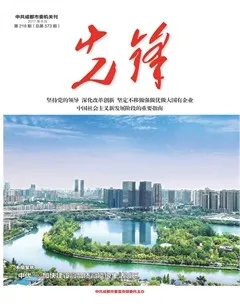創新政府監管 促進新經濟快速發展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成都作為地處西部的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應當積極推動要素市場改革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以抓住科技革命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切實增強“五中心一樞紐”支撐功能。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新經濟
理論研究表明,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供給側勞動力、土地與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五大要素之間的數量、質量、組合情況以及由此產生的綜合效益。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是否先進、效益是否明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吸引流入要素的數量與質量。
在《成都市產業發展白皮書》中,提出要加強要素市場建設,降低土地資源、能源、資金、技術轉化、物流運輸等要素交易成本,優化要素流動環境等加快促進資本、技術、人力、數據、管理等要素聚集。這是準確把握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與關鍵,扎實有力推動改革,為經濟轉型夯實基礎、創造條件的具體舉措。
在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人們常常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什么,成功與否的標志是什么?筆者認為,從要素運動規律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要落實到在通過改革破除了要素流動的重重約束之后,要素按市場規律自由流動、優化重組后所形成的新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之上。結合當前正日新月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判斷,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大力發展新經濟。
什么是新經濟?當下我國所稱的新經濟,主要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術(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術革命帶動的、以高新科技產業為龍頭的經濟,如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云計算、大數據應用、分享經濟等,還有在這一過程中,互聯網對原有國民經濟各個門類所進行的改革和升級,覆蓋一、二、三各個產業級次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
我國的互聯網經濟已經舉世矚目。目前,世界上十大互聯網企業中,我國占了四家。有國際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零售市場的線上滲透率將攀升至22%,市場規模總計將達10萬億元。再以當下正處于“成長的煩惱”中的分享經濟為例,其發展勢頭更是令人嘖嘖稱奇。據《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顯示,中國分享經濟發展迅猛,對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引領創新、擴大就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報告估算,2016年我國分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345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共有6億人參與,比上年增加1億人。預計未來幾年,我國分享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經濟交易規模占GDP比重將達到10%以上。
新經濟展示出的不可思議的潛力與空間,指明了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的大方向,當然也是未來財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放眼全球,當前世界正處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入口”上,我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能否抓住新經濟這一歷史機遇,是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重回世界之巔的關鍵一招。
成都在“產業新政50條”中,已經將創新信息要素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提升信息基礎設施能級、強化信息集成應用、推動信息與產業深度融合等方面都有明確要求與具體舉措。這正是準確認識到新經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所做出的前瞻性的布置與安排,必將為成都經濟發展培育出強勁的新動能,支持未來成都乃至整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創新政府監管,破除新經濟發展障礙
新經濟的廣泛興起和快速發展,一方面給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勢必觸動和影響既得利益格局而受到各種抵制。成都作為西部國家級中心城市,相對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完全有條件對新經濟持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積極創新政府監管方式,后來居上,后發制人,率先為新經濟的發展掃清路障。
其一,大道至簡、底線監管。對于新經濟,首先應當承認其“新”,承認其可能超出了政府已有的認知范圍,承認現有的監管規則可能是不適用的,在此基礎上再討論如何監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首先需要的是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因此,政府監管應當貫徹“大道至簡”“底線監管”的原則,守住法律法規的底線,只要在法律認可的范圍內,就宜將廣闊的空間留給各類市場主體,政府不要輕易出手。特別是對有些一時看不準的東西,可以先觀察一段時間。當然,那些經過實踐證明可能造成嚴重不良后果的,則要嚴格加強監管,果斷出手。總之,煩苛管制必然導致停滯與貧困,簡約治理則帶來繁榮與富裕,大道必然至簡,有權不可任性。
其二,從管理到治理,推動監管方式轉型升級。即使是那些看得準的新生事物,比如基于“互聯網+”和分享經濟的新業態,也要探索新的監管之道。新經濟不僅“新”,而且參與者眾多。在新經濟時代,政府監管要取得實效,除了要有傳統的、自下而上的政府層級結構的權力線之外,還必須與各類合作伙伴建立起橫向的行動線,原來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需要轉變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共治的扁平化治理。要十分重視平臺、行業協會的作用,主動與它們合作,將平臺、協會運行中一些具有普適性的規則上升到國家法律法規的層面,對于一時看不準的東西,則可以由平臺、協會為主,繼續在各方互動中逐漸探索清晰。
其三,創新政府監管的技術手段。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指出,大數據已成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徑”。在對新經濟的政府監管創新中,要十分重視大數據技術的應用,構建起一套“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新機制。一要爭取全面實現政務活動的網絡化、虛擬化。二要逐步實現計算機對數據的自動流程化管理,在數據匯集的基礎上發現規律,發現風險點和薄弱環節,增強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三是要努力打破各類“信息孤島”,實現數據按需、契約、有序、安全式開放,形成跨部門數據共享機制。總之,大數據既是政府監管所必須倚重的一種技術手段,更是激發政府創新監管制度的重大機遇,要善加利用。
其四,繼續深化政府監管體制改革。一是積極推進綜合監管,建立健全跨部門、跨區域執法聯動響應和協作機制。二是推廣“雙隨機、一公開”的新型監管方式。力爭實現全覆蓋。三是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更好地激發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的活力,對內資、外資、國資一視同仁,同時堅決維護公正、公開、公平的市場環境,為新經濟發展創造更加良好的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