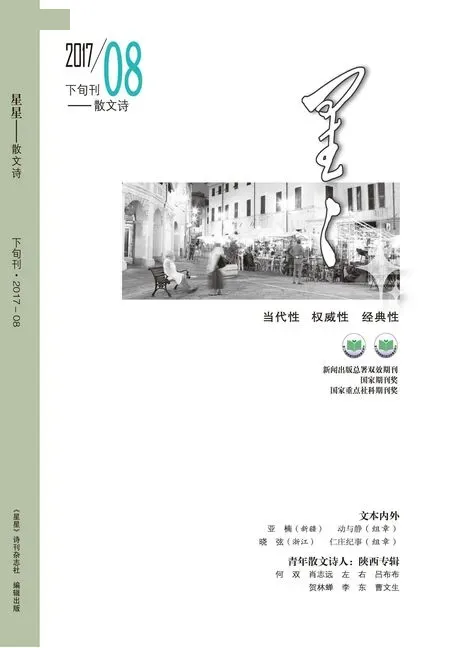非草即木(組章)
厲彥林(山東)
非草即木(組章)
厲彥林(山東)
山 草
山前,山后,田畦,房跟,路旁,河邊,溝底,石縫……自由地活著。
近看有形,遠看有影。
綠色的云。朦朧的霧。飄搖的夢。
潑潑辣辣,伸展青翠的手掌,從不奢求。有一把土、一滴水,就悄然扎根,就憋芽,就吐綠,就結籽,就繁衍后代。
生性纖細柔弱。雖然有骨、有筋、有肉,也有頭顱,卻風往哪邊吹就往哪邊倒。
老人可踏一腳,頑童可踏一腳,每一腳都很殘酷。
牛可以啃一口,羊可以啃一口,每一口都很新鮮。
鐮刀可以割頭,鋤頭可以斬根,依然頑強地活著。
一生貧窮、忍耐、善良,不說一句話。
山草,就是這一片片平凡的山草。
或為飼料,或為肥料,或為灶柴,聚集起來,就是燎原的熊熊烈火。
枯樹與長青藤
枯樹被長青藤纏繞著,相依為命。
蒼老的枯樹重新獲得生命,在風中抖動往日的雄風。
纖弱的長青藤爬在枯樹的背上,自由舒展著莖和葉,聆聽呼嘯的山風,凝視如織的游人,欣賞遠處的風景。
詩人說:長青藤生來沒有骨頭,依靠著枯樹,出人頭地,不值得稱頌。枯樹倒像一位長輩,為兒孫鞠躬盡瘁。
哲人說:枯樹雖然軀干已死,而靈魂依然站立。長青藤經過艱難的成長歷程,精神已經得到冶煉和升華。二者走向辯證統一。
佛人說:生就是死,死就是生。這沒有什么稀奇。
游人說:這是難得的風景,快舉照相機,留下一張凝重卻朝氣的倩影,存進記憶的永恒。
枯樹旁若無人,不動聲色。
長青藤依然爬在枯樹的背上,舉起生命的綠旗幟,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地活著。
叩問山頂的柏樹
樹木凋零的季節。我站在山頂上,迎著陣陣寒風,陡然發現兩塊巖石夾縫里被風斬斷頭顱的那棵老柏樹。
我輕輕蹲下來,仔細凝視著柏樹那白花花的傷口,還有傷口上忙著搬家的一群螞蟻。柏樹周圍是蒼老的石頭和衰敗的枯草。一種孤獨凄涼的感覺涌上心頭。
每一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秘密,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景觀。
這株老柏樹曾獨自站在山的背上,舒展,灑脫,自在。
站在山頂,伸出綠冠,就成為高山的峰。第一口品嘗太陽的光芒和春雨的溫馨。
山腰和山下所有挺拔的樹木,再高也站在腳下。
在眾多目光的仰望里,腰變粗,枝變密,漸漸成為多情風雨進攻的目標。陡然的一天,在雷霆的吶喊中丟失了生命。
生命,愛情,死亡,這是世間三樣最讓人驚心動魄的東西。
凋敗是殘酷的,卻是真實的。
我叩問這被折斷頭顱的老柏樹,漫長的生存之路,為何在最茂盛的時刻走短了?什么樣的生存狀態,能延長生命的軌跡?
站在老槐樹下
還是大雪紛飛的日子,還是故鄉這棵老槐樹下。
無奈的寒風,一頁頁翻動我的記憶。
我已與魂牽夢繞的故鄉相隔諸多的歲月。
在冬天的城里,身上很熱,心里很涼。
在冬天的鄉下,身上很涼,心里很熱。
樹枝已脫落所有葉子,伸開無數的顫動的手指,指向藍天。我的耳畔仿佛響起親人日思夜盼的呼喚。
雪地里的一行行腳印,被吹起的雪粒,悄悄覆蓋。漫長的時光,卻抹不平我的記憶。
我撫摸著老槐樹,望著白茫茫的曠野,滋生許多的孤獨。
我背負老槐樹的凝望,拄著探路用的樹枝,冒著雪走出了這寒冷的山坳。
走回故鄉,站在這棵老槐樹下,望著熟悉而陌生的一切,尋到許多寶貴的東西。
前方是茂密的山林,路從腳下隱隱約約地伸展到遠方。
我直直腰,拍打掉身上的雪花,憶起諸多停留的理由,卻又沿著鄉間的小路返回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