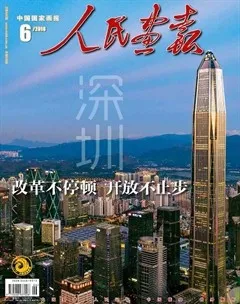曹文靜 深圳“第二代移民”成長記
曹文靜說自己是典型的深圳第二代移民。
2000年,文靜跟隨父母來到深圳。這之前,她的父母在湖北黃石擔任公職,但深圳的機會誘惑著這兩位年近40歲的人。
文靜在濱河中學初一年級作了插班生。全校的人都說廣東話,只有她一個人說普通話。下課時大家圍著她問你是哪來的呀?你為什么會來這里?“同學們好奇又友善。”
初夏的午后,文靜坐在她位于深圳大鵬新區較場尾的“巖嶼”民宿客廳中,講述著兒時經歷。
深圳對文靜最大的影響是眼界開闊,信息海量,且多數來自香港。她還記得小時候看過的風靡年輕人的香港時尚周刊《YES!!》(創刊于1990年,2014年停刊),所有的小女孩兒人手一本。當時還隨刊贈送謝霆鋒、容祖兒等香港明星的閃卡。
因為深圳和黃石教材差異大,第一次考英語,文靜只得了 50分,在黃石她曾考過120分。從此自暴自棄,“我就成了個學渣。”
文靜高考考上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習工業分析與檢驗。畢業后去了深圳市水務集團,在水質監測站作化驗員。父母對她這份工作很是滿意,覺得專業對口,又沒有太多社會交往,對女孩子很安全。
十年的光景,她離開時已經是辦公室主任。
曹文靜覺得,她父母年近40歲從體制內脫離出來,是一件很“牛”的事情。
雖然已經做到辦公室主任,但文靜認為已然看不到未來的自己,不如尋找一個未知。“創業是最不可知的,你并不知道明天是吃粥還是吃飯,就出來試試看吧。”
離職的事受到父母的影響。“他們也是覺得如果在老家一輩子就這樣了。我父母都是1960年出生的,他們來深圳的時候,差不多40歲,雙職工直接走,能夠下這么大的決心,這個事情很牛啊。我覺得他們選擇深圳很明智,因為深圳的機會太多了。影響我父母的大多是潮汕人,他們的那種創業精神、吃苦精神,都很驚人。”
文靜的父母有一位最要好的大哥,是潮汕人,她稱作陳伯伯。這位陳伯伯16歲的時候背著鍋碗瓢盆來到深圳闖蕩。“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事他都做過。”后來他自己開酒店做餐飲,最終做房地產。“這種榜樣在深圳比比皆是,大家都是那種吃苦耐勞型的,什么機會都不放過。”
走出體制,文靜并沒有想好做什么。做民宿純屬機緣巧合。當時房子的主人在尋找合作伙伴,跟文靜聊了以后,覺得這件事交給一個喜歡花花草草、貓貓狗狗的女孩兒應該靠譜,事情就這么定下來。
“巖嶼”所在的較場尾已有近400家民宿,競爭不小。文靜承受著很大的經營壓力,要把房東的投資賺回來至少得六七年。她目前期望能做到自負盈虧。
“巖嶼”有400多平方米,10間客房,黑白調子的裝飾,現代感極強。在一片斑斕的異域風情或陳舊古風裝潢的民宿中顯得自然、雅致、宜人。客人多為三四十歲拖家帶口或五十歲以上的職業人士。
“在深圳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行業的創業者,我是被尊重的。”客人跟她聊天,彬彬有禮。帶來的酒水沒喝完,盡管是很貴的紅酒也會留給她。遇到這些充滿善意的住客,文靜總是感嘆,“我是哪里來的福氣哦。”
曹文靜看好較場尾民宿的前景。“為什么不看好這里呢?這里整個灣全是民宿。”
接受我們采訪的那天下午,深圳市一位副市長到此地調研,文靜的“巖嶼”是其中之一。后來她告我們,副市長看了“巖嶼”后覺得她們做得挺好,但更希望當地商家多關注大的生態圈,對大環境有建設性的改良。諸如大鵬新區旅游生態圈如何打造、環大鵬半島水陸兩條線如何游覽之類。
文靜很看好大鵬區未來的發展,因為大鵬新區管委會成立,華僑城也進駐了,整個民宿所在的較場尾將會被打造成5A級景區。“我們這種靠著大樹的地方,自然會被福蔭到。”
民間組織是深圳的特色,較場尾成立了民宿協會。這讓文靜感覺不再是單槍匹馬打拼,作為同業,能交到不同店的老板作朋友“。我開業的時候,其他店的老板來幫我擺桌椅、拆包裝,真是擼著袖子幫你干活。后來有兩個‘90后’小姑娘新開了一家店,兩個人跑過來姐姐長姐姐短,然后又是一個輪回——別人幫我,我幫別人,人們都很友善。現在年輕人好多都是從國外回來,概念多,想法多,和她們聊天,我也有很多長進。”
提起深圳,曹文靜說:“很少聽說在深圳長大的小孩兒要離開深圳,去外面創業。如果創業,他們還是會選擇在深圳。”
深圳有創業需要的一切東西。只要有想法,就能把它付諸實踐。“比如說我現在開了這樣一家店,如果我要開第二個分店,就會有人給我投資。因為人家看到了這個店,知道你能夠做成。”
在文靜看來,深圳有諸般的好:沒有地域歧視,“來了都是深圳人”,包容極強;文明程度高,司機開車禮讓行人,遵守交通規則,市民坐公交車自覺排隊。
“在深圳,制定的規則,大家是會去遵守的。我覺得這很珍貴,因為規則這個東西,是人為制定的,你想遵守它,那你就去遵守它,不遵守,就當是空氣視而不見。還有一些是共識,你看不見,也不需要去說明,大家都會去做。比如媽媽帶著小學生等著過馬路,看到推垃圾車的師傅掉了東西,小學生會沖上去幫忙撿起來,這不是網上說的什么好人好事,這是日常可見的事情,我真心覺得很驕傲。深圳就是這么可愛。”
“我勝在能干點活,能吃點小苦。我真的沒什么文化,這是我內心的一個硬傷。”
“巖嶼”客廳中的書架上擺著些黑白攝影作品,還有《三體》《古船》《跟著馬克·呂布拍中國》《中國建筑史》《視覺》之類很“文化”的書。文靜說,那都是她看的書。

文靜朋友圈很廣。十年前,跟著年齡比她大十幾二十歲的朋友玩攝影,深受這些大朋友的影響。“在我心目當中,他們很神,一輩子就做一件事情——攝影。現在他們50多歲了,住在溪涌的農家院里,沖膠片、抽煙斗、養貓狗,自己給自己建立了一個烏托邦。我是有一點理想主義的,一定要有向往美的沖動,所以我就跟他們在一起。”
還有她父母的朋友陳伯伯,在文靜心目中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存在。“陳伯伯60歲的時候,把生意全部分給他的兄弟們,自己拿了一些錢去了西雙版納,包了幾座山頭,完成了他這一輩子的夢想,種茶葉,做出最好的老班章。他喝一杯茶,就能知道這個炒茶師傅的性格是什么。因為心急的人炒出來的茶是另外一種口味。”文靜很崇拜他。
文化程度也許跟學歷有關,但文化的涵養卻有多種方式和路徑。這一點,在文靜身上很是明顯。32歲的她談吐得體但不世故,性格開朗但不輕飄,善解人意卻不造作。僅憑讀大學得不來這般接人待物既脫俗又切近的氣質。
像許多父母創業成功的深圳第二代移民一樣,文靜更能感受到深圳的富足和文明,遵奉規則,自尊包容。父母和長輩雖艱難但終獲成功的創業經歷,使他們敢于選擇,務實上進。與不同來路、不同年齡但功成名就的朋友交往,使他們懂得放棄,隨遇而安。對文靜這樣的深圳第二代移民來說,懂得感恩、與人為善、珍惜生活,既是美德,更是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