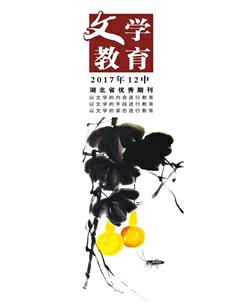近代商人心態例析
內容摘要:近些年來,晉商歷史小說的創作方興未艾。在這類小說中大多將時代背景定格在晚清時期,其中所暗含的共同創作旨趣值得探討。文章著眼于晚清時期晉商心態的巨大變化,具體可歸結為新四民觀的體現、愛國為民的情懷以及對皇權的蔑視心理。對晉商歷史小說中近代
新世紀以來,晉商歷史題材的電視劇收獲了巨大成功。誠然,電視劇能以直觀的影像將晉商的恢弘氣勢以及榮辱興衰的歷史變遷呈現在觀眾面前,但作為原始底本的小說,其藝術價值仍是不可忽略的。
在晉商歷史小說作家中,成一是創作上的先鋒,也是集大成者。新世紀初期的《白銀谷》可以稱得上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近代晉商風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由兼具作家和編劇身份的朱秀海創作的《喬家大院》,則把這一題材的創作推向了高峰,使“晉商文化”和“晉商精神”為世人所知。兩部作品都將時間定格在晚清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塑造了性格氣質不盡相同的晉商形象,但其中人物表現的心態卻是相似的,某些方面甚至是高度契合的,下面將從三方面進行探討。
一.新四民觀的體現
王陽明提出的“新四民論”,把士農工商置于“道”的層面上進行言說,認為他們只是存在社會分工上的差異,而并無尊卑貴賤之別。在《白銀谷》與《喬家大院》中,主要人物的言行時常帶有新四民觀的印記。《白銀谷》中雍正御批“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朕所悉知。習俗殊為可笑”[1]。青年時期的康笏南聽完父親的講述,令他吃驚的不是雍正皇帝對山西重商輕仕民風的評價,而是父親背誦御批時那種不屑的語氣。晉省流傳著的鄉諺“秀才入字號,改邪歸了正”,更加鮮明地表達出對由儒入仕、通過追求功名進而出人頭地的不屑了。作為傳統的讀書應仕、求取功名成了末路之選,“學而優則仕”演變為“學而優則商”,商人不再以自己的職業為恥,而將其看作自己大展宏圖、實現理想抱負的可行路徑。
《喬家大院》專門設計了喬致庸于貢院龍門前為山西商人正名的情節。當山西總督哈芬評價山西民風已敗壞,且將之歸咎于山西的重商之風時,喬致庸據理力爭:“圣人也沒說過重商之風敗壞民風……商人行商納稅,乃是強國固本的大事”[2]。喬在分析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在無形中將處于末位的商業、商人的地位抬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農業的重要性相提并論,這與新四民觀中“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論述不謀而合,體現出晚清商人的自我認知,即一種“良賈何負于閎儒”的心態。
二.愛國為民的情懷
在這兩部晉商歷史小說的代表作中,處處洋溢著晉商愛國為民的博大情懷。《白銀谷》中,康家“驚天動地賠得起”的情節描寫展現了晉商以國為家、家國一體的恢宏氣度。遭遇了庚子國變的巨大浩劫之后,京城里一片廢墟,西幫(晉商的別稱)各票號亟待復業,卻面臨重重困難。作為天成元財東的康老太爺顯示出了非凡的氣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擠兌再兇險,咱銀子也跟得上;窟窿再大,咱也賠得起”[3]!隨之進行的是開啟了家中的秘密銀窖,挖出六十萬兩白銀,源源不斷地運往京津兩地,解了擠兌風潮之圍。康老太爺的這一舉措,固然帶有愛惜自家票號名譽,維系生意的意圖,但更多的卻體現出一種博大的情懷,一股不失信于天下人的氣魄,一份心系蒼生福祉的赤誠。
同樣的心態在《喬家大院》中也有體現。縱觀喬致庸的一生,其一言一行都帶著胸懷天下、心系百姓的印記。喬致庸終生致力于“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為萬民謀天下那么大的財富”[4];遇到災年之時,毀家紓難,在家門口開設粥場賑濟了十萬災民。晚年的喬致庸,在自家票號生意蒸蒸日上之時,沒有喜悅和激動,而是看到了繁榮之后的悲涼。在作者的筆下,愛國為民的心態伴隨著喬致庸的一生。不論自己是富可敵國抑或傾家蕩產,喬致庸心里始終是先有“國”而后有“家”的概念,始終裝著為天下人,為黎明百姓謀福利的宏圖大志。
三.蔑視皇權的心理
在《白銀谷》中,年少時的康笏南曾聽父親背誦雍正皇帝的御批,那一份不屑令他吃驚;八國聯軍侵華,兩宮倉皇出逃去往西安,途經山西,在戴老幫安排好覲見之事后,康笏南一面贊揚其能力,另一面“在心里可是發冷笑了:哼,總算要親眼一睹天顏了,看一位如何無恥,另一位又如何無能”[5]!康笏南的話語與內心活動,體現了在那樣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晉商敢于蔑視皇權、不趨附于權力階層的心理。
作為《喬家大院》的核心人物,喬致庸更是敢于直接對抗朝廷。左宗棠帶兵西征勝利收復新疆,慈禧太后竟想以“賜匾”的方式賴掉欠下的銀子。剛烈的喬致庸敢于在眾多百姓與官員面前痛訴清廷的無恥,即使慈禧太后盛怒之下將他投入大獄,他也抱著慷慨赴死的決心,毫無畏懼。兩宮逃往西安時住進喬家,喬致庸并不曲意逢迎,而是目光之中“越來越多地現出厭惡”,并且大膽地將百姓每天吃的野菜團子端給慈禧食用。這一系列行為充分體現出了喬致庸鄙視權貴、敢于對抗朝廷的心理,反映出近代商人反叛封建腐朽勢力的心態。
四.結語
這三種似乎有悖于封建傳統社會階級觀的心理并不是毫無關聯的,相反,它們經常存在于同一個人身上,并且存在于不同作品中不同的主人公身上,恰恰豐富了小說的人物形象,也使歷史上晉商信義天下,匯通四海的形象更加豐富立體。同時,這三種思想所體現的家國大情懷也與歷代作品中商人重利輕義、因小失大的“負心人”與奸詐形象大相徑庭,對人們重新審視商人這個群體以及思考商人的社會價值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成一.白銀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朱秀海.喬家大院[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3]楊虹.當代歷史小說中商人精神的詩性張揚[J].中國文學研究,2003(4):82-86.
[4]李遇春.成一“晉商小說”論[J].小說評論,2012(6):132-138.
注 釋
[1]成一:《白銀谷》第32頁,作家出版社,2001
[2]朱秀海:《喬家大院》第24-25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3]成一:《白銀谷》第933頁,作家出版社,2001
[4]朱秀海:《喬家大院》第187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5]成一:《白銀谷》第566頁,作家出版社,2001
(作者介紹:于志彬,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2015級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