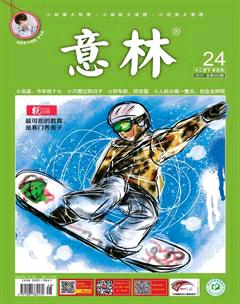請幫你的孩子選一個體育偶像
李稻葵
最近和一個哈佛畢業的年輕人討論,美國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輟學,輟學里的人不僅有終成大器的精英,更多是失去方向的孩子。
但為什么其中最有名的幾個人有兩個(比爾·蓋茨,馬克·扎克伯格)來自哈佛?
她說,哈佛錄取的學生非常重要的一關是面試。考官挑的都是一幫“自命不凡”之徒,而輟學的一般又是其中最狂妄的。
哈佛選人的能力恐怕遠遠超過它的教育能力,選的不僅是學習能力,更在于申請人的志向。教育最難的是如何激發一個學生的“志”。

我接觸過很多天資過人的孩子,但是上了大學就失去了學習動力和目標,變得迷茫,而且從本科階段越往上這種情況越多,十個哈佛博士生至少有三個退出了。
20世紀80年代末,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還專門舉辦了一個項目,幫助對本專業喪失興趣的博士生轉行,包括創業。對于教育工作者和家長,讀到博士了不想讀了,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失敗”結局。怎樣培養或激勵學生的志向?我不知道誰真的有答案。
但我覺得有個簡單的辦法,老師和家長必須盡量用好,那就是榜樣、偶像、明星——大多年輕人都會有偶像,常常不自覺模仿偶像的言行,自身的行為習慣隨之改變。但是現在的教育工作者遇到一個普遍問題:一時找不到當代學術界或政商界,對社會真正有突出貢獻的人物作為偶像。在我成長的年代,年輕人的偶像不是革命英雄就是華羅庚這樣的科學家,不過那個時代恐怕很難簡單重復了。
怎么辦?一個比較現實的辦法:與其任由孩子們追影視明星,不如柔性地引導他們去關注體育明星。首先,影視明星的工作就是“演”,有劇本有“人設”,展現給大眾的是一套嚴密的工業體系包裝推廣后的形象。
體育明星的成就則更真實有力,過的是沒有劇本的生活,他的“殊死搏斗”、心理上的失敗迷茫、成功的狂喜都能在賽場上一覽無余。體育是人類社會競爭與合作的縮影,尤其是直接競爭類的體育項目,如果一場比賽有你喜歡的明星,你不僅會看,而且整個過程跟他綁在一起,心情比他還跌宕起伏:看他是如何在被強敵壓制時逆襲翻身的,他是怎樣克服心理和生理障礙的?對我們有什么借鑒意義……競賽把人生的很多矛盾和解決方式,高度聚焦式地展現在你面前,對孩子而言是非常生動的高濃度的人生教育課。
而且如果你持續地熱愛一個項目或長時間關注一個明星,還會看到豐富的人生百態:比如李宗偉與林丹之間“既生瑜何生亮”的唏噓,比如中國女排如何團結一致,緊盯對手,拋開所有雜念后拼搏出的光芒,這就是體育的魅力!體育明星,這幫競技場的勝者,也正是像哈佛面試官最愛的那樣,是這個社會最自命不凡,最狂妄的志向遠大者。
這種斗志,是我們教育者在課堂上最難教給學生的,只能讓孩子們在現場近距離觀看體育明星的“ShowTime”,從中體悟,這恐怕是娛樂明星很難激發的。
更重要的是體育明星還會激發孩子多參加運動,孩子們會在球場上模仿NBA明星的經典酷炫動作。
很多人學羽毛球、學游泳,也會反復觀看林丹、菲爾普斯的比賽視頻……在一個娛樂為主的年代,追一個體育明星也是不錯的偶像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