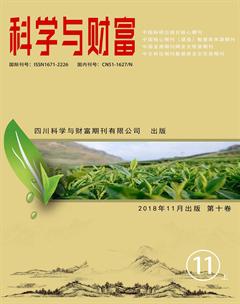社會治理工作中過度刑法化現象及對策分析
吳文意
摘 要:國家權利合法性是保障每一名公民自由與權利,公民犯錯,國家對其處罰要有正規化的根據。而過度刑法化是我國社會治理工作中的一種病態,反映在司法、立法多個層面上,如果我國在社會治理工作中,長期處于過度刑法化,會削弱了刑法的公眾認同性,進而阻礙了社會發展的創新。對此,本文著重分析過度刑法化的概述,論述社會治理工作中司法解釋與刑法過度化現象,提出社會治理工作中過度刑法化的對策。
關鍵詞:對此;現象;社會治理工作;過度刑法化
引言
我國刑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局限了人類的本性,為刑罰提供了道義與空間基礎。然而,任何與刑法相關的案例,都主張以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為主要內容,在此過程中存在“惡”的本質,故而,形成過度刑法化。過度刑法化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家權利與公民權利,削弱了刑法的公眾仍同性,進而阻礙了社會發展的創新。對此,在社會治理工作中,國家要減少對刑法的運用,只要是在不損壞國籍利益、公眾利益的前提下,部分民事糾紛案件,都要“寬容”態度進行審理,多給人一些自由,減少刑法過度化現象發生,進而才能夠發揮刑法學的根本效應。
一、過度刑法化的概述
社會發展需要秩序,人類生活需要自由。只因如此,每一個人都具有自由的權利。如果說自由是人類生來就應該具備的權利,那么任何人或者組織都不能夠對人進行懲罰與裁判,而懲罰也是我國刑法中的主要內容。因此,刑法學在教育學呈現時,要注重其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屬性,研究國家對公民強制力的正當性問題。法律雖然是社會制度化下的產物,但是其在社會治理工作中,不能夠過于制約人類的自由,那樣會形成過多刑法化。過度刑法化是指在社會治理工作中,刑法并沒有遵守與社會規范與其他法律的界限,越過刑法合理的功能。過度刑法化并不是我國特有的現象,其是國家在社會治理工作虹權力體系的越位體現。我國刑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局限了人類的本性,為刑罰提供了道義與空間基礎。然而,刑法主張以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為主要內容,在此過程中存在“惡”的本質,因此,國家在對人的處罰上很少、減少運用刑法。基于此,當前刑法被視為對人的處罰最后一道環節。而刑法過度化是對刑法觀念的背棄,會引起社會治理風險,使人們難以接受。可見,在社會治理工作中,刑法學的運用不易過度,要適合、適中,進而才能夠發揮刑法學的根本效應。
二、社會治理工作中司法解釋與刑法過度化現象
司法解釋與刑法過度現象。自我國刑法修訂以來,司法解釋頒布的“兩高”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取得良好的作用,進而統一了我國刑事案件辦案的標準。同時,我們也能夠看到,當前司法解釋的條文也超過了刑法學的條文,而眾多的司法解釋無疑增加了國民預測的的難度,還使司法辦案人員在案件辦理中無所適從,不能夠該運用那一種司法解釋去看待案件。在司法解釋中,較多的司法解釋低估了司法人員理解刑法的能力。比如:2000年時最高人民法院對《關于審理拐賣婦女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第一條與刑法第240條規定相一致,規定拐賣兒童、婦女罪中,對“婦女”的解釋。其指出:拐賣婦女罪中“婦女”,不僅包含中國籍的婦女,同時還包括無國籍、外國籍婦女。如果被拐賣的婦女沒有身份證明的,也不影響對罪犯的處罰。根據這一思維,刑法中的232條相關于故意殺人罪也要這么解釋嗎?在我國刑法中指出,人,既是中國人,同時也包含外國人、無國籍的人。
刑法過度化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律也在適當的調整與完善,指出:只有是在不損壞國籍利益、公眾利益的前提下,部分民事糾紛案件,都以“寬容”態度進行審理。例如: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立法認為:勞動者的報酬相關于其生存及社會穩定與基本人權。任何組織、機構拖欠勞動者報酬,就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有甚者會引發社會諸多矛盾。對于該罪的正當性,許多法學研究者都存在不同的見解,梁慧星指出:運用刑法打壓機構、組織、單位、企業欠款行為是不妥的,將老板判處幾年刑,之后企業會垮掉,很多勞動者會失去工作,這樣的處罰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應該站在立法的視角,去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幫助勞動者討回薪資。這種觀念并沒有被相關機構采納。由此能夠看出,刑法過度化的體現。
三、社會治理工作中過度刑法化對策
(一)貫徹刑法最小化原則
社會治理工作中,解決過度刑法化,要將最小化原則貫徹到刑法中,強調公民有不被犯罪化權利,國家權利與法治公民權利決定公民具有不犯罪權利,我國刑法上明確了“法益侵害原則”與“傷害原則”等基本犯罪化原則。傷害原則在我國刑法中被稱之為嚴重傷害危害性原則,也就是構成這項犯罪的基礎,是罪犯對社會發展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本文認為,刑理論與實踐持續保持傳統刑法犯罪本質上,在考查罪犯是否具有嚴重危害社會行為,要重視公民不被犯罪權利,國家要對犯罪化行為承擔證明責任。因此,在講解過度刑法化中,要尊重罪犯不被犯罪權利,將最小化刑法原則貫徹到其中,對罪犯從輕發落,尊重他們的合法權益。
(二)刑法治理最小化
社會治理工作中,要將刑法治理最小化滲透到刑法體系中,關注刑法對普通違法行為的處理情況。事實上,一個較為健全的立法者不可能為制定公眾不能夠完成的法律規定,同時有可能去制定司法機關不能夠實現的法律規章制度。例如:在經濟轉型期間出現的普遍性、規模性的犯罪行為,我們都能夠意識到這種犯罪對國家、社會發展具有危害性,但由于這些犯罪行為數量、規模較大,如果都處罰了會出現一些不平的聲音,會使大眾抵觸法律,削弱刑法的力度。然而,國家法律采取選擇性治理、打擊,運用殺一儆百的方法,就能夠震懾住其他民眾,會減少社會混亂現象,會使那些想要犯罪的人們收起自身違法行為,進而可以解決過度刑法化對社會發展、創新帶來的負面影響。
結語
綜上所述,當前刑法被視為對人的處罰最后一道環節,而刑法過度化是對刑法觀念的背棄,會引起社會治理風險,使人們難以接受。對此,新時期下,只要是在不損壞國籍利益、公眾利益的前提下,刑法學的運用不易過度,要適合、適中,進而才能夠發揮刑法學的根本效應。
參考文獻:
[1]何榮功.社會治理“過度刑法化”的法哲學批判[J].中外法學,2015,27(02):523-547.
[2]孫萬懷,盧恒飛.刑法應當理性應對網絡謠言——對網絡造謠司法解釋的實證評估[J].法學,2013(11):3-19.
[3]于志剛.“雙層社會”中傳統刑法的適用空間——以“兩高”《網絡誹謗解釋》的發布為背景[J].法學,2013(10):102-110.
[4]陳興良.刑法教義學與刑事政策的關系:從李斯特鴻溝到羅克辛貫通 中國語境下的展開[J].中外法學,2013,25(05):974-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