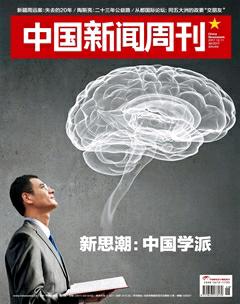人為什么會有同情心
徐賁
讓我們好好守護它,不要讓我們的心因為不再能敘述轉換而變得冰冷和僵硬
兩個人遇到一位正在驅趕和毆打路邊攤販的城管,一個說,“城管沒有必要這么冷酷無情”,另一個說,“城管在行使他的職責”。他們兩個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對事情的解釋卻大相徑庭。心理學將此稱為“看法構造社會現實”——你帶著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來解釋情境,你用認知和情緒來表述事件,這就是你構造社會現實的方式。問題是,我們是否能說清楚“真正發生的事情”?我們在試圖說清楚的時候是否會有偏誤?
有人認為,這類問題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是一種道德虛無主義。理性的社會生活,其基本秩序必須也只能建立在說清真相和辨別正誤的可能性之上。道德虛無主義本身就是錯誤的。試想,如果辨明是非曲直與你的切身利益相關,不辨明是非曲會讓你莫名其妙地深受其害,你還會認為辨明是非沒有意義嗎?
在構造社會現實時,一般人會產生“自利性偏差”:同一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就事關重大,發生在別人身上就可以理解。受自利性偏差影響,人的同情心容易產生遠近之分。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指出,“每個人對凡是直接關系到他自己的事,興趣都會比較強烈,而對關系到其他人的事,就比較沒有興趣。譬如,聽到某個與我們沒有特殊關系的人死了,我們感到心憂、沒有胃口或睡不著的程度,遠小于我們自己遇上一個很無足輕重的小小不幸。”
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當事人的敘述。心理學家梅拉妮·格林等人提出,故事有“敘述轉換作用”。故事敘述引起的想象和感情,讓人脫離自身現實,轉換視角,進入說故事人所構造的世界,然后便會按這個世界的角色和規則看待事物。
哈佛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里指出,對他人的同情和對人類生命的尊重,都是基于人類能轉移視角的同理心。他寫道:“當某某人的思想進入了你的頭腦,你就是站在他的立場觀察世界。你不僅去看見、去聽見那些你并未親身經歷過的場景,你還走進那個人的心靈,暫且分享了他或她對世界的態度和反應。”
通過媒體報道的社會弱勢群體和底層勞動者的故事,敘述轉換作用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我們感受到,他們生活在城市邊緣,干的是最累的活,換取的是低額的報酬,但他們仍以最大的努力頑強生活,并對未來懷有夢想和希望。互聯網時代的圖像和視頻傳媒,更加強了這種故事的敘述轉換效應,我們會對他們的夢想和希望因某種不公或不幸而破碎,感同身受。
平克還指出,“閱讀就是一種轉換視角的技巧”,具有人道教育作用。“閱讀他人文字的習慣能夠讓一個人養成代入別人觀點的習慣,從而感受別人的歡愉和痛苦,這樣說應該不算是很大的跳躍。在某一個瞬間,我們突然覺得自己就是絞架上窒息得臉色發青的人,或者就是那位絕望地推開燃燒著的柴束的女子,或者自己正顫抖地領受著第二百下鞭打。我們也許會問自己,是否應該在任何人的身上使用這樣的酷刑。”
18世紀的書信體小說,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20世紀的紙媒新聞報道,21世紀的網絡新聞和社交網站傳播,傳媒方式變了,但思想家對閱讀讓人有同情心的闡述沒有過時。
狄德羅是這樣描述這種同情心的:“盡管你知道這是小說,但一旦進入他的角色,你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他們的對話,然后,你同意,你譴責,你愛慕,你開始煩躁了,你感到憤怒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經不覺得奇怪了,我就像一位第一次被帶進劇院的兒童,哭喊著對故事中的人說:‘不要相信他,他是在騙你呀。????人物都是來自生活的普通人????描寫的激情,正是我自己內心的感受。”
社會底層人們的故事讓許多國人產生了強烈的同情心。讓我們好好守護它,不要讓我們的心因為不再能敘述轉換而變得冰冷和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