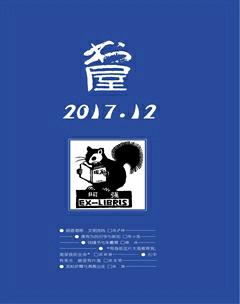心中有束光眼里有片海
張寶明
走進(jìn)同門(mén)師兄沈衛(wèi)威《民國(guó)大學(xué)的文脈》(以下簡(jiǎn)稱《文脈》)的領(lǐng)地,在作者移位變形、多維分說(shuō)的立意背后,一股擔(dān)綱的文氣首當(dāng)其沖:“學(xué)無(wú)新舊也,無(wú)中西也,無(wú)有用無(wú)用也。”這是王國(guó)維早在1911年就在《國(guó)學(xué)叢刊·序》中提出的“學(xué)術(shù)三無(wú)”名言。或許,這乃是對(duì)“學(xué)術(shù)乃天下之公器”之“價(jià)值無(wú)涉”、“價(jià)值中立”的概括和闡釋。
應(yīng)該看到,學(xué)風(fēng)的差異并非二十世紀(jì)民國(guó)的首開(kāi)。自古有之的孔孟、老莊之異,宋以后的尊德性、道問(wèn)學(xué)之別,清代學(xué)者的漢、宋之爭(zhēng)以及古文、今文學(xué)派的分歧都可以看作是“學(xué)分南北”的不同表現(xiàn)。試想,即使是儒學(xué)自家都會(huì)因地制宜,更何況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的因人而異?
1924年1月7日,胡適在日記中摘錄了毛奇齡一段關(guān)于話:“世每言,北人之學(xué)如顯處見(jiàn)月,雖大而未晰也;南人之學(xué)比之牖中之窺日,見(jiàn)其細(xì)而無(wú)不燭也。”饒有情趣的是主人加注的一段話:“此說(shuō)南、北之學(xué)之分,頗妙。北學(xué)多似大刀闊斧,而南學(xué)多似繡花針。”如果說(shuō)胡適是“站在橋上看風(fēng)景”的那個(gè)人,而他之被錢(qián)基博所看則進(jìn)一步將“身在此山中”的莫之能外一網(wǎng)打盡:“‘北大派,橫絕一世,莫與京也!……《學(xué)衡》雜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guò)重知識(shí)論之弊。一時(shí)之反北大派者歸望焉,號(hào)曰‘學(xué)衡派。世以其人皆東南大學(xué)教授,或亦稱之曰‘東大派。”在錢(qián)基博這番評(píng)論之后的1940年,一位長(zhǎng)期任教于中央大學(xué)也即是今天南京大學(xué)的歷史學(xué)教授金毓黼,為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門(mén)第二年編輯出版的《史學(xué)述林》撰寫(xiě)的題詞則寄希望于“南派”與“北派”之“收風(fēng)雨商量之雅”,與毛奇齡立意的“兼之”、錢(qián)基博著意的“相濟(jì)”可謂異曲同工。在這樣一個(gè)背景下,相對(duì)于桑兵、羅志田、陳平原、王汎森的關(guān)注,沈衛(wèi)威以更為確實(shí)的“史實(shí)和細(xì)節(jié)”將人為遮蔽的歷史本相打撈出來(lái),并以悲“學(xué)”憫“人”的文化情懷關(guān)注著這一應(yīng)然的方向和訴求:“雙方想要溝通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但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和學(xué)術(shù)觀念的差異所造成的學(xué)派分野,卻是一直存在的。”在作者那里,正是北方大學(xué)“新材料、新問(wèn)題”以及“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xué)人品行”為民國(guó)大學(xué)奠定了基本的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也正是“舊學(xué)的繼承與堅(jiān)守”為“東南學(xué)風(fēng)”種下了“眼里存不下沙子”的純正基因。
應(yīng)該看到,古往今來(lái)的學(xué)者不約而同地關(guān)心著這些因“地”而“宜”的“微言”或說(shuō)“學(xué)風(fēng)”,其中必有“大義”在。原來(lái),這是一個(gè)遠(yuǎn)遠(yuǎn)超出地理原因的命題:包括諸如沈衛(wèi)威在內(nèi)的一代又一代學(xué)人們還有著更為“應(yīng)然”的理想訴求。
在這一意義上,南、北的分屬尚可理解,但南、北人為地裂痕卻種下了很多不無(wú)遺憾的隱患。這乃是《文脈》的人文情懷之所在。
大學(xué)空間之大,為何容不得個(gè)性與特色鑄就的不同風(fēng)格?如果說(shuō)“學(xué)分南北”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流布,那么接下來(lái)《文脈》揭橥的又一具有一詠三嘆之旋律意義的“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由誰(shuí)來(lái)設(shè)定的實(shí)際問(wèn)題”就成為一個(gè)世紀(jì)之問(wèn):“民國(guó)時(shí)期的學(xué)界,在相當(dāng)自由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下,通常是誰(shuí)掌握了學(xué)術(shù)的話語(yǔ)權(quán),就由誰(shuí)來(lái)定學(xué)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衛(wèi)威兄在書(shū)中不止一次的追問(wèn)這個(gè)耿耿于懷的判斷,仿佛是一種現(xiàn)實(shí)的撩惹激起了他那積淀已久的千千心結(jié)。
《文脈》同樣讓我們看到,民國(guó)還有一抹亮色讓學(xué)人們?yōu)橹畱c幸:一些知識(shí)分子,盡管為數(shù)不多,但堅(jiān)守著萬(wàn)變不離其宗的學(xué)統(tǒng),尤其是把持住了守身如玉的道統(tǒng)底線。胡適,作為士人的表率,得到最大多數(shù)的肯定和贊譽(yù),在很大程度上來(lái)自于他以身作則的學(xué)術(shù)至上立場(chǎng)。《文脈》一書(shū)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舉展開(kāi)自己的敘述,既是對(duì)“由誰(shuí)來(lái)定學(xué)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這一論點(diǎn)的佐證,也是對(duì)這一“實(shí)際問(wèn)題”喜憂參半的腳注。事實(shí)上,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諸如學(xué)術(shù)至上的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守望者并不止胡適一人,只是在胡適身上體現(xiàn)得更為具體、生動(dòng)和完整。換言之,歷史讓胡適在院士選舉這個(gè)平臺(tái)上有了得以外化或說(shuō)施展自我忠厚之君子人格的機(jī)會(huì)。在國(guó)民黨搞出的“部聘教授、最優(yōu)秀教授黨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花樣繁多的名堂面前,有著生殺予奪話語(yǔ)權(quán)的胡適“并沒(méi)有因郭沫若此時(shí)的左傾而排斥他,相反,他看中的是郭沫若的學(xué)術(shù)研究本身”。為此,才有了作者的這樣的尷尬:“饒有意味的是,五年后的大規(guī)模批判胡適運(yùn)動(dòng),郭沫若最先站出來(lái),將自己1923年曾親吻過(guò)的胡適視為思想、學(xué)術(shù)上的最大敵人。”值得說(shuō)明的是,這里的“五年后”指的是五十年代的知識(shí)界清算胡適的運(yùn)動(dòng);“親吻過(guò)的胡適”師出有名,是指胡適1923年10月13日記中關(guān)于“沫若邀吃晚飯”間“我說(shuō)起我從前要評(píng)《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的記載。這也就難怪在郭沫若前后言行的不一致,讓作者流布出了這樣一段文字:“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不以政治立場(chǎng)評(píng)判,只以學(xué)術(shù)實(shí)力作為考量的標(biāo)準(zhǔn),郭沫若就能當(dāng)選。1955年中國(guó)科學(xué)院評(píng)選學(xué)部委員,以政治標(biāo)準(zhǔn)第一來(lái)考量,就有原來(lái)的老院士落選。”如果是換位思考,1948身為院長(zhǎng)的胡適和1955年身為院長(zhǎng)的郭沫若不知做何感想?不過(guò),在胡適這一抹亮色背后,作者的憂慮不無(wú)道理:胡適,一個(gè),兩個(gè),又三個(gè)固然可喜可賀,這也是知識(shí)分子的榮光。如果學(xué)術(shù)不能超越“黨爭(zhēng)”,那將是一輪又一輪的殘酷斗爭(zhēng)、無(wú)情打擊在前,因?yàn)椤芭笥逊茨浚瑫?huì)你死我活,政治斗爭(zhēng)就更可怕了”。從“學(xué)分南北”的“自然”流布到“學(xué)術(shù)話語(yǔ)權(quán)”的隱憂(因?yàn)樗橛凇白匀弧迸c“非自然”的人為操縱、模棱兩可之間),知識(shí)分子隨時(shí)可能陷身泥淖、在劫難逃。這一切,需要制度的保障。試想,胡適當(dāng)年為爭(zhēng)取學(xué)術(shù)話語(yǔ)權(quán)必須公然申明要做“學(xué)閥”嗎:“我想要做學(xué)閥,必須造成像軍閥、財(cái)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shì)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發(fā)生重大的影響;如其僅僅是做門(mén)徒是無(wú)用的。”有幸的是這個(gè)“學(xué)閥”是在“為文化開(kāi)新紀(jì)元”而上天入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豈非學(xué)界的罪人、民族的不幸、國(guó)家的災(zāi)難?說(shuō)白了,另一面相之“學(xué)閥”的登場(chǎng)則別有一番景象和滋味了。這也是沈衛(wèi)威之所以在文末奮筆疾書(shū)的根本所在:“學(xué)術(shù)超越黨爭(zhēng),彼此以學(xué)術(shù)的原則相互尊重、共生共存,當(dāng)是兩岸所有學(xué)人的共同期盼。”
在我們看到的條分縷析之《文脈》背后,既是一種說(shuō)不清、道不明的“從來(lái)如此”,也有一種欲說(shuō)還休的無(wú)奈與悲情。魯迅曾經(jīng)借“狂人”之口發(fā)出“從來(lái)如此,便對(duì)么?”的詰難,而這里卻只能以“從來(lái)如此有什么不對(duì)嗎”作罷。如果說(shuō)“學(xué)分南北”還無(wú)傷大雅,畢竟這只是一種學(xué)風(fēng)使然的話,那么當(dāng)走進(jìn)書(shū)中的另一層“學(xué)術(shù)話語(yǔ)權(quán)”則有一種莫名的痛楚與辛酸。如果說(shuō)《文脈》就此戛然而止的話,也就只能作壁上觀了。在對(duì)胡適、陳寅恪充滿由衷敬意之外,對(duì)未能例外的知識(shí)分子,作者更是平添了一份“同情之理解”的人文關(guān)懷。租賃作者援用的概念來(lái)支援本義的話即是“了解之同情”。
“同情之理解”或說(shuō)“了解之同情”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囊痪淙宋男g(shù)語(yǔ)。這一學(xué)術(shù)術(shù)語(yǔ)最早見(jiàn)諸1922年4月29日東南大學(xué)學(xué)生胡夢(mèng)華發(fā)表在《時(shí)事新報(bào)·學(xué)燈》的《評(píng)〈學(xué)衡〉》一文:“批評(píng)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1930年7月,陳寅恪在《馮友蘭著〈中國(guó)哲學(xué)史〉審查報(bào)告》中這樣議論道:“凡著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史者,其對(duì)于古人之學(xué)說(shuō),應(yīng)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從此,這個(gè)舶自德國(guó)啟蒙時(shí)代思想家赫爾德的著名論斷經(jīng)由大師之手不脛而走,成為人文學(xué)的當(dāng)紅學(xué)術(shù)術(shù)語(yǔ)。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但爬梳出了這一術(shù)語(yǔ)的“前世”,更重要的是在“今生”以靈魂附體的寫(xiě)作形式丈量著自我行文的腳步。面對(duì)在胡適、陳寅恪之外諸如朱光潛、馮友蘭、賀麟、華羅庚等等一批在“積極‘優(yōu)秀”,作者的筆墨沒(méi)有停滯于對(duì)其“自我檢討,洗心革面,大寫(xiě)頌詩(shī)”的簡(jiǎn)單批評(píng)和嘲弄上,而是從一個(gè)個(gè)“小細(xì)節(jié)”的敘述中回到歷史現(xiàn)場(chǎng),從而兌現(xiàn)了“大歷史的”人文承諾。除卻對(duì)“猶如黑暗中的一盞燭火”的陳寅恪肅然起敬、油然生愛(ài),全書(shū)散發(fā)出的那股一以貫之的文氣可謂字字珠璣般敲打著我們的無(wú)眠之夜,也許這就是我們所說(shuō)的“心中有束光,眼里有片海”之格局和境界吧。
(沈衛(wèi)威:《民國(guó)大學(xué)的文脈》,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