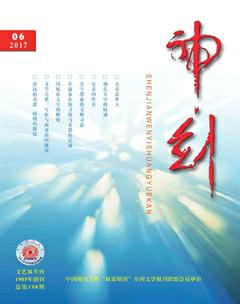軍旅詩(shī)是詩(shī)歌中的鹽和鈣
“軍旅生涯影響了我整個(gè)人生,這種影響是深入骨髓的,不可磨滅的。我的愛(ài)國(guó)情懷,民族情結(jié),使命感、責(zé)任感,直至生死觀,都是軍旅生涯鑄就的。”將軍詩(shī)人朱增泉說(shuō),“我把一生交給了軍隊(duì),軍隊(duì)給了我一切。”
1990年以后,朱增泉逐步轉(zhuǎn)向散文隨筆創(chuàng)作,2005年為集中精力寫(xiě)作《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基本停止了詩(shī)歌創(chuàng)作。
《朱增泉散文與隨筆》(4卷本)近日出版。之所以把書(shū)名定為《散文與隨筆》,朱增泉是希望讀者對(duì)他處理文體結(jié)構(gòu)的隨意性多一點(diǎn)諒解。
在一次次的梳理中,朱增泉對(duì)于歷史、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認(rèn)識(shí)在不斷深化。他認(rèn)為,歷史要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楚。這在《朱增泉散文與隨筆》中體現(xiàn)得尤其突出。
舒晉瑜:《朱增泉散文與隨筆》于您而言,有何獨(dú)特的價(jià)值或意義?
朱增泉:我是寫(xiě)什么學(xué)什么,通過(guò)寫(xiě)作這些文章,學(xué)到了不少知識(shí)。我說(shuō)過(guò),到中國(guó)歷史長(zhǎng)廊中去走過(guò)一趟和沒(méi)有走過(guò)時(shí)的感覺(jué)是不一樣的,不僅豐富了知識(shí),也提高了人生境界。有了寫(xiě)作的愛(ài)好,丟掉了諸多無(wú)謂的應(yīng)酬和累人的煩惱。
舒晉瑜:在編選的過(guò)程中,重新回顧梳理自己的作品,您對(duì)于這幾十年的創(chuàng)作有怎樣的總結(jié)和評(píng)價(jià)?
朱增泉:的確是對(duì)自己的業(yè)余寫(xiě)作做了一個(gè)總結(jié)。回顧這么多年的業(yè)余寫(xiě)作,我總結(jié)的第一條是“頂住壓力,堅(jiān)持不懈”。壓力來(lái)自閑言散語(yǔ),比如說(shuō)我“不務(wù)正業(yè)”之類(lèi)。我舉出兩條理由他們無(wú)法反駁:第一,官員寫(xiě)作是中國(guó)的文化傳統(tǒng)。歷史上那么多好文章、好詩(shī)詞,幾乎都是古代官員寫(xiě)出來(lái)的。第二,毛澤東寫(xiě)詩(shī),朱德寫(xiě)詩(shī),董必武寫(xiě)詩(shī),葉劍英寫(xiě)詩(shī),陳毅寫(xiě)詩(shī),我為什么不能寫(xiě)詩(shī)?寫(xiě),繼續(xù)寫(xiě)!理直氣壯,毫不退縮。我自己一直守住這條底線(xiàn):先把本職工作做好。我所有的詩(shī)歌散文作品都是熬夜熬出來(lái)的。
我總結(jié)的第二條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杜甫的詩(shī)句,我借來(lái)表達(dá)一下自己的感慨。我寫(xiě)歷史題材、政治題材的東西比較多,思考的問(wèn)題大多和我們中華民族興衰存亡有關(guān),與人民群眾的疾苦有關(guān)。我作為一名老軍人,這是肩負(fù)的使命所使然。從總體上說(shuō),我的散文隨筆比較厚重、大氣,有點(diǎn)歷史底蘊(yùn),語(yǔ)言比較簡(jiǎn)潔,有我自己的一些風(fēng)格特點(diǎn)。就這四本書(shū)而言,每一本書(shū)中都有幾篇好文章;但有不少篇目自己也并不滿(mǎn)意。孰優(yōu)孰劣,都交給讀者們?nèi)ピu(píng)說(shuō)吧。
舒晉瑜:您筆下的人物,每一個(gè)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有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軍嫂、士兵、詩(shī)人、航天員、元帥,也有帝王將相和二次大戰(zhàn)期間的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朱可夫等。我很想知道,您寫(xiě)的歷史人物,有沒(méi)有顛覆人們印象中的人物形象的?有一些被作家們反復(fù)書(shū)寫(xiě)過(guò)的人物,您如何寫(xiě)出自己獨(dú)特的發(fā)現(xiàn)?
朱增泉:我開(kāi)始寫(xiě)人物散文,是寫(xiě)自己接觸過(guò)的人,真實(shí),但缺乏深度。后來(lái)注意從多角度切入去寫(xiě)一個(gè)人,避免概念化、平面化,既寫(xiě)他的正面,也寫(xiě)他的側(cè)面,甚至反面,使人物形象更豐滿(mǎn)、更真實(shí),有血有肉,所以比較有深度。我寫(xiě)帝王將相,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人物卷中的《漢初三杰悲情錄》。漢初三杰是指張良、韓信和蕭何,寫(xiě)劉邦同這三位西漢開(kāi)國(guó)功臣間的微妙關(guān)系,我自己覺(jué)得把這四個(gè)人都寫(xiě)活了。劉邦自己指揮打仗本事不大,卻能將這三位杰出人物隨意掌控?cái)[布,為他所用,不能不說(shuō)他的馭人術(shù)在中國(guó)封建帝王中是一流的。在劉邦打天下的過(guò)程中,對(duì)這三位人物采取忍讓?xiě)B(tài)度換取他們的忠心。隨著天下到手,他與“三杰”的矛盾開(kāi)始增多、公開(kāi)。他對(duì)“三杰”采取分化瓦解、各個(gè)擊破的策略,將他們一個(gè)個(gè)收拾。而“三杰”各有各的性格,他們對(duì)劉邦的猜忌之心采取了不同的態(tài)度,因此結(jié)局也大不相同。韓信硬頂,終于招來(lái)殺身之禍;張良智避,放下一切功名利祿,隱退山林“辟谷”,抑郁而亡;蕭何對(duì)劉邦死心塌地,不僅任勞任怨,還當(dāng)眾忍受劉邦下令對(duì)他的鞭打和羞辱,又充當(dāng)呂后誅殺韓信的幫兇,總算保命終老。
戰(zhàn)爭(zhēng)卷中有一篇《從伊拉克戰(zhàn)爭(zhēng)說(shuō)到諾曼底登陸》,其中寫(xiě)到二次大戰(zhàn)中的三巨頭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通過(guò)對(duì)他們的重新研究,我對(duì)這三位歷史人物都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過(guò)去我們對(duì)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是否定的,因?yàn)樗麄兌际堑蹏?guó)主義頭子,都反共。但我從歷史角度去重新認(rèn)識(shí)他們,對(duì)羅斯福和丘吉爾都產(chǎn)生了一定好感。我認(rèn)為這兩人都是世界級(jí)政治家,對(duì)二次大戰(zhàn)勝利都有歷史性貢獻(xiàn)。羅斯福另一個(gè)貢獻(xiàn)是二戰(zhàn)結(jié)束前就為建立戰(zhàn)后秩序做安排,提議創(chuàng)建了聯(lián)合國(guó),為戰(zhàn)后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基本框架。還有一條,我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寫(xiě),羅斯福對(duì)中國(guó)是很重視的。他提議中國(guó)擔(dān)任聯(lián)合國(guó)“四強(qiáng)”之一(美、英、蘇、中)。羅斯福看不起法國(guó),反對(duì)法國(guó)進(jìn)入聯(lián)合國(guó)領(lǐng)導(dǎo)層。后來(lái)法國(guó)力爭(zhēng),經(jīng)各國(guó)協(xié)調(diào),補(bǔ)充法國(guó)為聯(lián)合國(guó)“五常”之一。1943年,羅斯福邀請(qǐng)蔣介石出席開(kāi)羅會(huì)議,決定戰(zhàn)后重大事宜。羅斯福的本意是戰(zhàn)后要把日本侵占的中國(guó)領(lǐng)土臺(tái)灣、澎湖和琉球群島一并歸還中國(guó)。他一再問(wèn)蔣介石,中國(guó)是否想要琉球群島?蔣介石卻說(shuō)該島由美、中兩國(guó)“共管”。戰(zhàn)后美軍駐扎了一段時(shí)間,又把琉球交回給了日本,中國(guó)失去了收回琉球群島的歷史性機(jī)遇。羅斯福還提出由中國(guó)派兵占領(lǐng)日本,蔣介石說(shuō)這件事只能由美國(guó)來(lái)干。這是蔣介石的歷史性過(guò)錯(cuò)。蔣介石的心胸太狹隘了,他的“心腹大患”是共產(chǎn)黨,抗日戰(zhàn)爭(zhēng)一旦結(jié)束,他要集中力量“消滅”共產(chǎn)黨,所以不愿過(guò)分“得罪”日本。他這種心態(tài),在《蔣介石日記》1943年這一章中反映得很充分。如果蔣介石不那么狹隘,能夠站在民族大義立場(chǎng)上思考問(wèn)題,在羅斯福的支持下,臺(tái)灣、澎湖、琉球、香港問(wèn)題當(dāng)時(shí)有可能一攬子得到解決,要是那樣現(xiàn)在也不會(huì)留下釣魚(yú)島爭(zhēng)端之類(lèi)的后遺癥了。丘吉爾是反共急先鋒,但二次大戰(zhàn)德軍大舉進(jìn)攻蘇聯(lián)當(dāng)天,他就在倫敦發(fā)表廣播講話(huà),公開(kāi)支持蘇聯(lián)反擊德國(guó)法西斯。
什么叫世界級(jí)政治家?就是能夠順應(yīng)世界進(jìn)步正義潮流而動(dòng)。斯大林功過(guò)對(duì)半開(kāi),我一向崇拜他領(lǐng)導(dǎo)蘇聯(lián)人民頑強(qiáng)抗擊并最終打敗德國(guó)法西斯軍隊(duì)的鋼鐵意志。對(duì)蘇聯(lián)衛(wèi)國(guó)戰(zhàn)爭(zhēng)研究越深,這種感覺(jué)越牢固。盡管蘇聯(lián)政治局面經(jīng)歷了天翻地覆的巨變直至土崩瓦解,我對(duì)斯大林的基本評(píng)價(jià)一直沒(méi)有變。斯大林搞肅反擴(kuò)大化是完全錯(cuò)誤的,蘇聯(lián)崩潰的國(guó)內(nèi)根源要從這里找起。歷史要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前不久,媒體上有一則消息,俄羅斯搞了一次民意測(cè)驗(yàn),評(píng)選一百年來(lái)俄羅斯最受尊敬的人。評(píng)選結(jié)果出乎人們預(yù)料,第一名居然是斯大林,普京位居第三,這是發(fā)人深思的。
舒晉瑜:您寫(xiě)的游記,并非純粹的游山玩水,而是帶有深厚的問(wèn)題意識(shí),這使您的游記增加了厚重感和憂(yōu)患思考;而且游記中多寫(xiě)西北景色,這又使作品更開(kāi)闊,為什么?
朱增泉:我的國(guó)內(nèi)游記大部分是寫(xiě)大西北的,這同我調(diào)入原國(guó)防科工委工作有關(guān)。我們的馬蘭核試驗(yàn)基地、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都在大西北,每當(dāng)有大型試驗(yàn)任務(wù)我都去。每次試驗(yàn)任務(wù)結(jié)束后,我都會(huì)留下多待幾天,走一些地方,熟悉大西北,包括新疆、甘肅、內(nèi)蒙古西部。要了解中國(guó)歷史,尤其了解中國(guó)古代戰(zhàn)爭(zhēng)史,不了解大西北不行。漢武帝抗匈奴、通西域,中央政權(quán)與匈奴、西夏、吐谷渾爭(zhēng)奪河西走廊,明清兩代與北元?dú)堄鄤?shì)力(西蒙古、東蒙古)的反復(fù)交戰(zhàn),這些歷史陳?ài)E大多在新疆、甘肅、內(nèi)蒙古西部這片廣闊地域內(nèi)。我以濃厚的興趣一次次、一處處去尋訪(fǎng),增長(zhǎng)了不少歷史知識(shí)、軍事知識(shí),每次回來(lái)都能寫(xiě)出一點(diǎn)東西。通過(guò)這些實(shí)地考察,更激發(fā)了我熱愛(ài)這片遼闊疆域的情懷。文章的厚重和開(kāi)闊,都來(lái)源于此。古人認(rèn)為寫(xiě)文章的基本素質(zhì)要求就是兩條:行萬(wàn)里路,讀萬(wàn)卷書(shū)。這是千真萬(wàn)確的至理名言。如果我不去大西北走那么多地方,我這些文章根本寫(xiě)不出來(lái)。
舒晉瑜:戰(zhàn)爭(zhēng)卷的散文和隨筆,以您當(dāng)年跟蹤觀察伊拉克戰(zhàn)爭(zhēng)所寫(xiě)成的《觀戰(zhàn)筆記》一書(shū)為主,還有6年前您寫(xiě)的一批觀察分析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guó)通過(guò)低烈度戰(zhàn)爭(zhēng)(以網(wǎng)絡(luò)推手和街頭事件為主)發(fā)生政權(quán)更迭的文章。現(xiàn)在收錄進(jìn)來(lái),卻并不過(guò)時(shí)。因?yàn)闀?shū)中對(duì)美軍打信息化戰(zhàn)爭(zhēng)新的作戰(zhàn)理念、新的作戰(zhàn)樣式和新的作戰(zhàn)手段的概要介紹,對(duì)21世紀(jì)美國(guó)戰(zhàn)略思維及其戰(zhàn)略走向的分析和預(yù)判,對(duì)21世紀(jì)亞洲國(guó)家群體性崛起的歷史機(jī)遇及必將面臨美國(guó)戰(zhàn)略遏制的分析和預(yù)判,正在“不出所料”地一步步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為什么您會(huì)有這樣的前瞻性和預(yù)判能力?
朱增泉:戰(zhàn)爭(zhēng)卷中的文章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寫(xiě)伊拉克戰(zhàn)爭(zhēng)的,第二部分是寫(xiě)中東、北非風(fēng)波的。對(duì)21世紀(jì)美國(guó)戰(zhàn)略思維及其戰(zhàn)略走向的分析和預(yù)判,以及對(duì)21世紀(jì)亞洲國(guó)家群體性崛起的歷史機(jī)遇,這種群體性崛起必將面臨美國(guó)戰(zhàn)略遏制的分析和預(yù)判,集中在《伊拉克戰(zhàn)爭(zhēng)后的亞洲命運(yùn)》這篇文章中。這樣的前瞻性和預(yù)判能力,是我對(duì)世界局勢(shì)走向分析的結(jié)果。從宏觀層面做戰(zhàn)略性分析判斷,不像對(duì)某些突發(fā)性事件的預(yù)測(cè)那樣難以捉摸,它是有跡可循的。就像觀察一條河流,只要找到它的源頭,弄清它的流向,再根據(jù)季節(jié)變化,是可以預(yù)見(jiàn)它的水流大小變化的。
舒晉瑜:朱可夫是真正的軍事家,在蘇聯(lián)衛(wèi)國(guó)戰(zhàn)爭(zhēng)期間當(dāng)過(guò)八個(gè)主要作戰(zhàn)方向的方面軍司令員,料敵如神。我注意到您寫(xiě)過(guò)《朱可夫雕像》。能談?wù)勚炜煞騿幔繌哪切┖?nèi)外的軍事巨頭身上,您是否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
朱增泉:朱可夫是我崇拜的世界級(jí)軍事家。我對(duì)他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幾點(diǎn):第一,他有打大仗、打惡仗的非凡膽魄,有洞察戰(zhàn)場(chǎng)局勢(shì)變化的敏銳感覺(jué),有扭轉(zhuǎn)戰(zhàn)場(chǎng)危局轉(zhuǎn)敗為勝的鐵腕。第二,他有堅(jiān)持正確判斷敢于頂撞斯大林的錚錚骨氣。第三,他有豐富的軍旅生涯經(jīng)驗(yàn)積累。他是從士兵一步步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先后參加過(guò)兩次世界大戰(zhàn)。第四,他出生于農(nóng)村貧苦家庭,熱愛(ài)親人,同情窮人。第五,他進(jìn)入和平年代后屢遭挫折,以至被赫魯曉夫利用,名聲受到很大影響。戰(zhàn)爭(zhēng)卷中的《朱可夫雕像》一文,是我2002年率團(tuán)訪(fǎng)問(wèn)俄羅斯期間,一處處尋訪(fǎng)了朱可夫的許多遺跡后寫(xiě)出來(lái)的。其間還發(fā)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這在文章中都有。我既然從軍一生,身為將軍,自然要以國(guó)內(nèi)外的許多名將作為參照系,時(shí)時(shí)激勵(lì)自己,不能活得庸碌不堪。
朱增泉就讀過(guò)的小學(xué),錢(qián)穆先生曾擔(dān)任過(guò)校長(zhǎng)。朱增泉表示,錢(qián)穆自學(xué)成才的成長(zhǎng)道路,影響了自己的一生,為自己長(zhǎng)期堅(jiān)持自學(xué)產(chǎn)生了很大的激勵(lì)作用。
舒晉瑜:詩(shī)歌創(chuàng)作是您當(dāng)了集團(tuán)政治部主任以后才開(kāi)始的,曾出版過(guò)《朱增泉詩(shī)歌三卷集》:政治抒情詩(shī)《中國(guó)船》、軍旅詩(shī)《生命穿越死亡》、抒情詩(shī)《憂(yōu)郁的科爾沁草原》。能否談?wù)勀脑?shī)歌創(chuàng)作,具有怎樣的特點(diǎn)?
朱增泉:我開(kāi)始寫(xiě)詩(shī)是在戰(zhàn)場(chǎng)上開(kāi)始的,寫(xiě)出第一首詩(shī)的時(shí)間是1987年1月31日。我通過(guò)長(zhǎng)期自學(xué),對(duì)文學(xué)產(chǎn)生了興趣,但我參戰(zhàn)前從未想過(guò)要當(dāng)什么詩(shī)人,參戰(zhàn)給我提供了契機(jī),使我突發(fā)性地寫(xiě)起詩(shī)來(lái)。《山脈,我的父親》就是在戰(zhàn)區(qū)寫(xiě)出的第一首詩(shī)。大意是:人們都說(shuō)大地是母親,我說(shuō)山脈是我的父親,我踏著山脊去約會(huì)死神。寫(xiě)完已是午夜,我?guī)е?shī)稿到山坡下的戰(zhàn)地小報(bào)編輯部去審閱小報(bào)清樣。我進(jìn)了屋先給大家念了一遍這首詩(shī)稿,問(wèn)大家這算不算詩(shī)?大家都說(shuō):“這就是詩(shī)啊,很好的詩(shī)。馬上發(fā),馬上發(fā)!”我就是這樣開(kāi)始寫(xiě)起詩(shī)來(lái)。后來(lái)通過(guò)去前線(xiàn)采訪(fǎng)的記者、作家,把我登在小報(bào)上的詩(shī)歌帶回后方,有些報(bào)紙雜志進(jìn)行了轉(zhuǎn)載,引起了人們注意。既然大家承認(rèn)我寫(xiě)的這些分行文字是詩(shī),我就“一發(fā)不可收”地寫(xiě)了起來(lái)。
一直寫(xiě)到2005年,我把詩(shī)停了。集中精力開(kāi)始寫(xiě)作5卷本的《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我寫(xiě)的是自由體白話(huà)詩(shī),有兩個(gè)特點(diǎn)比較明顯:一是我的軍旅生涯比較長(zhǎng),軍旅生活積累比年輕詩(shī)人多;二是我當(dāng)了多年領(lǐng)導(dǎo)干部,站在宏觀角度分析問(wèn)題的能力比年輕詩(shī)人要強(qiáng)一點(diǎn)。這兩條優(yōu)勢(shì)反映在我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生活氣息比較濃,視野比較開(kāi)闊。所以,不少人說(shuō)我的詩(shī)歌比較大氣,而且有不少詩(shī)篇真切感人。但我的詩(shī)歌作品水平不整齊,有些作品我自己也不滿(mǎn)意。尤其是我的長(zhǎng)詩(shī),敘述的成分比較多,而詩(shī)歌是拒絕敘述的,即使寫(xiě)敘事詩(shī),也不能用寫(xiě)敘述文的句子去寫(xiě),這是我不再寫(xiě)詩(shī)以后才徹底明白過(guò)來(lái)的。
舒晉瑜:寫(xiě)散文隨筆,也是碩果累累。2011年出版的《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5卷本)貫通中國(guó)古代戰(zhàn)爭(zhēng)史5000年,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主席鐵凝稱(chēng)贊說(shuō),這部書(shū)是史學(xué)的也是文學(xué)的,是軍人的也是詩(shī)人的。您寫(xiě)詩(shī)關(guān)注的是貓耳洞和局部的戰(zhàn)場(chǎng),寫(xiě)這部書(shū)是關(guān)注中國(guó)古代戰(zhàn)爭(zhēng)史,以及戰(zhàn)爭(zhēng)給人類(lèi)帶來(lái)的深刻思考。這種思考的深刻,是一般人不能抵達(dá)的。您覺(jué)得呢?6年過(guò)去,您如何評(píng)價(jià)《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
朱增泉:鐵凝主席概括的這兩句話(huà)很精辟,我感謝她對(duì)我的鼓勵(lì)和支持。何鎮(zhèn)邦說(shuō):“《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是老朱的代表作。”他是從作品的分量和產(chǎn)生的影響來(lái)評(píng)價(jià)的。我接受并珍惜他們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的評(píng)價(jià)。我為這部書(shū)的確付出了相當(dāng)大的心血,動(dòng)筆時(shí)我已65歲,寫(xiě)完時(shí)已70歲,沒(méi)有一點(diǎn)毅力是拿不下來(lái)的。我寫(xiě)作《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是嚴(yán)肅認(rèn)真的,因?yàn)檫@是寫(xiě)歷史,不能誤傳子弟,所以我不搞任何“演義”“戲說(shuō)”之類(lèi),對(duì)每一條史料都查得很認(rèn)真。當(dāng)然,即便小心再小心,也難免仍有某些差錯(cuò)。所以,今后幾年如果我身體條件還允許,我想再修訂一遍。
舒晉瑜:能談?wù)勀恼Z(yǔ)言嗎?軍史專(zhuān)家糜振玉曾指出,《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題材鮮明,是一部散文化的戰(zhàn)爭(zhēng)史。您的語(yǔ)言詩(shī)意且凝練,用文學(xué)的筆法來(lái)描述中國(guó)古代戰(zhàn)爭(zhēng)史,生動(dòng)豐富,拉近了普通讀者和戰(zhàn)爭(zhēng)史的距離。
朱增泉:用散文筆調(diào)來(lái)寫(xiě)《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是我有意為之,這也許是這部書(shū)的價(jià)值之一吧。糜振玉是軍事科學(xué)院老副院長(zhǎng),軍事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我的《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能得到他的肯定也不容易。我在長(zhǎng)期讀書(shū)自學(xué)中體會(huì)到,凡歷史,讀起來(lái)都是比較枯燥的。我想為年輕讀者們寫(xiě)一部讀得進(jìn)、有吸引力的歷史讀物。我語(yǔ)言中的“詩(shī)意”,那是因?yàn)槲耶吘故俏辉?shī)人嘛。說(shuō)到“凝練”,這來(lái)自?xún)蓚€(gè)方面。首先,我受到過(guò)魯迅語(yǔ)言的滋養(yǎng)。我年輕時(shí)喜歡讀魯迅的作品,魯迅的語(yǔ)言很凝練,句子都不長(zhǎng),對(duì)我影響較大。寫(xiě)詩(shī)之前我曾模仿魯迅筆法寫(xiě)過(guò)幾篇雜文,有一篇被收入《中國(guó)雜文鑒賞辭典》,說(shuō)明寫(xiě)得還不錯(cuò)。其次,得益于我對(duì)公文寫(xiě)作的深入研究。我在各級(jí)機(jī)關(guān)都工作過(guò),對(duì)公文寫(xiě)作曾做過(guò)深入研究。我討嫌空話(huà)、套話(huà)、八股調(diào),專(zhuān)門(mén)研究如何把公文語(yǔ)言寫(xiě)得實(shí)在、活潑。我概括出公文語(yǔ)言的三條要求:正確、準(zhǔn)確、明確。“正確”是相對(duì)“錯(cuò)誤”而言,“準(zhǔn)確”是相對(duì)“分寸”而言,“明確”是相對(duì)“含糊”而言。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摸索和實(shí)踐,我的語(yǔ)言比較干凈、活潑,沒(méi)有空話(huà)、套話(huà),沒(méi)有含糊其詞、模棱兩可的話(huà),也從來(lái)不去編一串一串的順口溜,句子都比較短,讀起來(lái)比較順。
評(píng)論家雷達(dá)認(rèn)為,“朱增泉有天生的歷史感”,具有通過(guò)歷史看人或通過(guò)人物看歷史的特點(diǎn)。朱增泉笑言所謂“融會(huì)貫通”,是同一個(gè)問(wèn)題的兩面,切入點(diǎn)不同而已。好比一個(gè)深宅大院,從前門(mén)或從后門(mén)進(jìn)去看個(gè)究竟,兩頭都走得通。
舒晉瑜:您的詩(shī)集《地球是一只淚眼》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能談?wù)勥@部作品嗎?是在什么情況下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
朱增泉:《地球是一只淚眼》是我的第7本詩(shī)集,出版于1999年8月。我前面的6本詩(shī)集,都是階段性詩(shī)作的結(jié)集,這第7本帶有一點(diǎn)選集的味道。以前6本詩(shī)集之后寫(xiě)的新作為基礎(chǔ),把前6本詩(shī)集中比較好的作品也編了進(jìn)來(lái)。我于1987年1月寫(xiě)出第一首詩(shī),到編《地球是一只淚眼》這本詩(shī)集剛好十年多一點(diǎn)時(shí)間,是一個(gè)階段性總結(jié)。《地球是一只淚眼》這本詩(shī)集共分5輯,第1輯《地球是一只淚眼》是寫(xiě)國(guó)際題材的作品。《地球是一只淚眼》是一首短詩(shī),一問(wèn)一答兩句:“地球是漂在水里嗎?/為什么每一塊大陸的周?chē)?全都是汪洋大海/哦!地球滿(mǎn)腹憂(yōu)煩/她睜圓了望不斷天涯的淚眼/何時(shí)能哭干/這么多苦澀的海水?”這是我對(duì)充滿(mǎn)矛盾的世界前途的憂(yōu)思,也是對(duì)人類(lèi)命運(yùn)的終極思考。我用這首詩(shī)的題目做了書(shū)名,也用它做了第1輯的欄目標(biāo)題。第2輯《對(duì)手之間》是寫(xiě)戰(zhàn)爭(zhēng)題材的作品,主要部分是寫(xiě)戰(zhàn)斗生活的;第3輯《我生命的河流》是寫(xiě)我自己生命體驗(yàn)的作品;第4輯《放牧靈魂》是寫(xiě)我游歷祖國(guó)南北各地的作品;第5輯《出奔》是幾首長(zhǎng)詩(shī)的選章。綜合起來(lái),可以反映出我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全貌,的確是我的一本重要詩(shī)集,我的詩(shī)歌代表作都集中在這本詩(shī)集里。
舒晉瑜:您是詩(shī)人,是作家,但您當(dāng)領(lǐng)導(dǎo)的時(shí)候,講話(huà)從來(lái)不用一句詩(shī)。您對(duì)自己是怎樣的要求?
朱增泉:這同前面說(shuō)到的閑言散語(yǔ)有關(guān)。不是有人說(shuō)我寫(xiě)詩(shī)是“不務(wù)正業(yè)”嗎?那好,我用實(shí)際行動(dòng)做給你看,我是如何對(duì)待我的正業(yè)的。我把履行職責(zé)同業(yè)余寫(xiě)作徹底切割開(kāi),開(kāi)會(huì)講話(huà)從來(lái)不用一句詩(shī)。另外,有些人講話(huà)時(shí)非要生拉硬扯引用幾句詩(shī),我聽(tīng)了身上起雞皮疙瘩。
朱增泉說(shuō),他期待軍旅詩(shī)歌有朝一日能重新振興。軍旅詩(shī)是詩(shī)歌中的鹽和鈣,愛(ài)國(guó)主義、英雄主義永遠(yuǎn)是軍旅詩(shī)的基調(diào)。一個(gè)正在迅速崛起的偉大民族,不能缺少這些精神元素。
舒晉瑜:在創(chuàng)作上,您秉持怎樣的文學(xué)理念?
朱增泉:我是現(xiàn)實(shí)主義派,是寫(xiě)實(shí)派,寫(xiě)詩(shī)、寫(xiě)散文隨筆都是這樣。我堅(jiān)信生活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唯一源泉。我的詩(shī)歌都來(lái)源于生活。寫(xiě)散文隨筆把真實(shí)性放在第一位,這更不用說(shuō)了。我寫(xiě)歷史散文,對(duì)史料的引用是很?chē)?yán)謹(jǐn)?shù)摹S袝r(shí)也會(huì)出現(xiàn)一些差錯(cuò),那是由于自己沒(méi)有把史料完全查清、吃透,有時(shí)是一知半解,有時(shí)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時(shí)是粗心大意。
說(shuō)到文學(xué)理念,正確對(duì)待文學(xué)批評(píng)也很重要,我對(duì)此一直保持平靜心態(tài)。讀者或評(píng)論家發(fā)現(xiàn)我作品中的差錯(cuò),我只要看到這些意見(jiàn)都照單全收,從不辯解。有位評(píng)論家曾在《文學(xué)報(bào)》上以一整版篇幅挑我散文作品中的差錯(cuò),題目是《名家筆下的硬傷和不足》。前面先有一段插曲,他寫(xiě)了一篇評(píng)論,通過(guò)別人轉(zhuǎn)給我看,文章結(jié)尾處有一小段是指出我散文中的差錯(cuò)的,他做了個(gè)記號(hào)征求我的意見(jiàn)。我在旁邊批了一句話(huà):“這些內(nèi)容可以照登。”這是他對(duì)我的一次試探,回去就來(lái)了這么一大篇。沿海某市有位刊物主編給我打電話(huà)說(shuō):“他是借你的名字炒他自己,有些地方挑得完全沒(méi)有道理。”我聽(tīng)了笑著對(duì)這位朋友說(shuō):“不必生氣。”我后來(lái)主動(dòng)托人帶給這位評(píng)論家一套《戰(zhàn)爭(zhēng)史筆記》,還可以做朋友嘛。有一次,某地有位人士在博客上鮮血淋淋挑出我散文中的一處硬傷,口氣還不太友好。我在博客上寫(xiě)了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向讀者致歉。后來(lái),我又把這篇博文發(fā)表在《美文》雜志上,再次向讀者致歉。我覺(jué)得這樣做光明磊落,沒(méi)有什么不光彩的。
舒晉瑜:您如何評(píng)價(jià)軍旅作家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在當(dāng)前詩(shī)壇中有怎樣的獨(dú)特價(jià)值?
朱增泉:目前的軍旅詩(shī)創(chuàng)作,和中國(guó)詩(shī)壇的總體情況一樣,處在一個(gè)低潮期。老一代軍旅詩(shī)人李瑛是大家,他的詩(shī)歌影響了幾代人。中年一代像周濤,他的詩(shī)歌是出類(lèi)拔萃的,現(xiàn)在他不寫(xiě)了。年輕一代的軍旅詩(shī)人劉立云是代表,他不斷探索,堅(jiān)持不懈,取得了不小的成績(jī),但他一個(gè)人也顯得“勢(shì)單力薄”。和劉立云同時(shí)代的還有武警的王久辛。更年輕的一批軍旅詩(shī)人我都不認(rèn)識(shí)了。軍旅詩(shī)的低潮期,和我們當(dāng)前的時(shí)代背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有關(guān)。人們的生活觀念過(guò)度物質(zhì)化了,文藝圈過(guò)度娛樂(lè)化、低俗化了。我期待軍旅詩(shī)有朝一日能重新振興。軍旅詩(shī)是詩(shī)歌中的鹽和鈣,愛(ài)國(guó)主義、英雄主義永遠(yuǎn)是軍旅詩(shī)的基調(diào)。一個(gè)正在迅速崛起的偉大民族,不能缺少這些精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