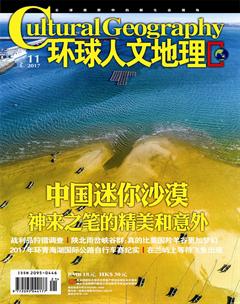“世界遺產”的標簽是一把雙刃劍
萊格妮·巴倫
馬來西亞喬治城的“姓氏橋”,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客。這里一度是居民的家園,如今成了商業小攤扎堆的地方,曾經的漁民現在卻在兜售T恤和明信片一類的東西。每天從早到晚,一輛輛旅游大巴運來一群群游客。
這種接連不斷的騷擾早已讓當地居民不勝其煩:他們只要一見到游客就馬上躲進屋里,“不準拍照”的告示也比比皆是。
“我想提醒大家,這里不是動物園,我們也不是猴子”,一名經營紀念品商店的當地人憤憤地說道。雖然這名商戶也承認來訪的游客越多,店里的生意越好,但同時也希望游客能夠尊重她的隱私,尤其是不要未經允許就擅自進入她的家里。
從前,位于馬來西亞檳城島喬治城郊外的姓氏橋是一座沿海成片建成的木屋村。這些用木樁架起的高腳屋,由一條長長的木板道串起,道旁依次分布著寫有中國人不同姓氏的屋子,它們是馬來西亞華人最后保存完好的老社區之一。僅存的7個姓氏橋躲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日軍的侵占,但海水數十年來的腐蝕,以及虎視眈眈的開發商,迫使當地人無數次地向外界求助——他們最終還找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并在2008年成功地獲得了“世界遺產”的稱號。
不過,隨之而來的事情讓當地居民更加苦惱。原本是漁民、生蠔捕手和算命先生進行買賣交易的姓氏橋,轉而被紀念品商店和小吃店占領了。當地人都表示,他們的小漁村不知不覺就被旅游浪朝吞沒了,令人措手不及。
類似的抱怨聲,同樣也發生在歐洲的巴塞羅那、威尼斯等地方,這些城市都為了在旅游業和商業化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而絞盡腦汁,而這也是1052個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標志的景點正在面臨的抉擇:究竟是迎合游客而獲取經濟利益,還是保護好為其帶來世界名聲的歷史文化?
始于1972年的“世界遺產”稱號,旨在鑒定和保護具有“杰出的普世價值”的地點。然而,在提高某個地方的國際知名度的同時,這個名號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而且為商業化打開了大門,從而損害了當地的原始性。2002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場會議上,世界遺產中心前主任弗蘭西斯科·班達蘭說道:“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這些景點被記錄在《世界遺產名錄》上的理由,恰恰也是吸引成千上萬游客的原因。”
比如,“世界遺產”——老撾的瑯勃拉邦,是一座擁有大約5萬人的小城,但預計在2018年,這里將會迎來超過70萬名游客。同樣,巴拿馬老城才被評上“世界遺產”后不久,當地政府就把老城的居民遷到了城郊,而老城的中心卻充滿了游客。還有人提到過拉美的伯利茲堡礁:開發商從四處涌來,利用該區域的“世界遺產”的名號,通過互聯網來出售當地的沼澤地資源……
對此,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喬·科思認為,“世界遺產”的標簽是一把雙刃劍,很多地方政府會把這種身份當做搖錢樹,雖然轉向旅游業能夠使社區得到復興,但若缺少有效的管理計劃,這些地方最終將會毀于旅游業。“歐洲受到影響的社區,許多居民正在努力地反抗失控的旅游業,而第三世界所受到的影響會更加嚴重。”喬·科思說道,“取得和開發這一稱號,這背后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么?賺更多的錢,還是保護文化遺產?”
面對日益惡化的形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可持續性旅游”的概念,甚至還將2017年定為“國際可持續性旅游年”,但有關專家認為這個目標比較虛幻,不切實際。
“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控制世界遺產商業化還沒有明確、有效的指導方案和行動綱領,他們在討論可持續性,但只停留在口頭上,并沒有實際上的操作性。”檳城古跡信托會的一名工作人員說道。
讓我們回到姓氏橋,這里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發。當地的一位居民提議提高門票價格,然后把募集到的錢款用在維護和修復高腳屋上,以便吸引更多年輕人回流。他還補充道,雖說他們一族的姓氏橋已經不可逆地商業化了,但人們還是要聯合起來保護好姓氏橋,因為這里是本地人生活的家園。他說:“只有我們能保護好這個地方,我們現在要決定如何管理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