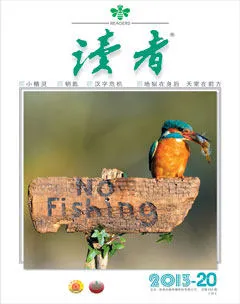嗚嗚地哭了
2013-12-21 07:11:58張煒
讀者 2013年20期
張煒
高爾基是當(dāng)年蘇聯(lián)的文學(xué)泰斗,跨越新舊時(shí)代的傳奇人物,走到哪兒都被簇?fù)碇K鞴芴K聯(lián)作家協(xié)會(huì),又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第一人,威望高得不得了。他主要寫小說,但也深愛詩歌。我們可能沒有看到過高爾基的詩,只看過一個(gè)與詩有關(guān)的他的故事。原來這個(gè)老頭子在家里寫了好多詩,只是不好意思拿給人看。有一次他沒忍住,就交給當(dāng)年正在詩壇走紅的馬雅可夫斯基,就是那個(gè)寫階梯詩的、很狂妄的無產(chǎn)階級(jí)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看著看著,就忘了面前是一個(gè)多么偉大的人物,竟然氣不打一處來,斥責(zé)說,這個(gè)句子怎么能這樣寫?這寫的是什么東西!不行不行!話說得不留余地,批評(píng)得毫不留情。
馬雅可夫斯基說著,對(duì)方一點(diǎn)聲音都沒有,抬頭一看,這才發(fā)現(xiàn)高爾基正抹著眼淚。老人嗚嗚地哭了,絕望了。這是羞愧的眼淚,絕望的眼淚,是“命里八尺,難求一丈”的眼淚。
我覺得高爾基哭得那么可愛,可以感受到一個(gè)大師在文學(xué)和藝術(shù)面前的那種謙卑,對(duì)詩的那種熱愛。這樣的老人可以不向強(qiáng)權(quán)低頭,但在詩的面前,在文學(xué)面前,卻非常謙卑。年輕的馬雅可夫斯基也很了不起,在詩面前他可以忘記一切,可以訓(xùn)斥泰斗。而高爾基像小孩子一樣嗚嗚地哭泣,多么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