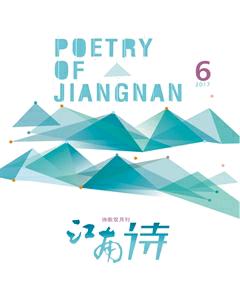《燃燒的麥穗》:“偏遠詩人”的精神群像
主持人語:
《燃燒的麥穗》出版時,我寫過這么一段話:“《燃燒的麥穗》無疑是繼2000年的《飛石》之后,維吾爾青年詩歌的一個重大收獲,也是向漢語世界的一次精彩亮相。無論是原創翻譯作品還是雙語寫作,呈現了一個古老‘詩性民族置身當下的情感節奏和心靈脈動,其現代意識、探索精神以及個人化寫作的差異性和豐富性,幾乎與國內新詩發展是同步的、相呼應的。……”與此同時,張清華、敬文東、張光昕等對這部詩集都有過高度評介。女詩人江媛的這篇評論,是一次深入細致的解讀,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這部優秀詩集。(沈葦)
《燃燒的麥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11月版)是對新疆近100多位詩人的千余首詩篩選后編譯出版的33人的詩歌合集,也是新疆維吾爾詩人首次在全國結集出版詩集,合力展示現代維吾爾詩歌成就,是推動維吾爾語詩歌從邊緣走向中心、抵抗遺忘的一次努力。這部詩集由314首詩塑造的新疆維吾爾族詩人的精神群像充滿了勇氣和真誠,也充滿了思想的珍珠。雖然我無法把握這塊遼闊地域上的詩人所經歷的具體命運,但由一個民族構成的合唱不僅超越了地域和語言、超越了民族和國界,也是自造詩歌的方舟向精神的大海出發的標志。《燃燒的麥穗》因其繼承了世界性多元文化融合的悠久民族傳統而顯得極為寶貴和獨特,因而具備了超越地域及民族的重要研究價值。
回望傳統,面對自我之未來,已是必然選擇。《燃燒的麥穗》中,大多數詩人在民間詩與藝術詩的繼承與發展方面經過長期努力,寫出了代表這個時代的精神特質及靈魂訴求的詩,這些詩篇不僅帶有維吾爾古典詩的影響,同時也帶有中西方現代詩的影響,甚至還帶有中國古代哲人的影響。其中絕大部分的詩歌展現出詩人將對個人體驗的生活通過詩歌內容向著哲學性的方向提升的努力,表現出維吾爾族詩人對古典維吾爾詩歌注重哲學思想的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兩條水在他的手杖
正在畫大地的中心
在他的手杖沒有他的夜
……
他的名字被風擦除
他只有像巖石的淚
他沒有名字……
阿不都外力·艾爾西丁的《他沒有名字》將手杖與夜、肚臍與橄欖樹、巖石與淚這些毫不相關的意象通過感官的覺知融合起來,讓眾多毫無關聯的事物通過思想的網編織在詩中,充滿哲思。哲理性是維吾爾古典詩歌的傳統,在當代表現為詩人將個人生活經驗通過詩向哲學性方向提升的努力:
淡黑色的路流入思想
……
可南方不一樣,
它以模糊的臉迎接客人,
然后送走。
——塔依爾·哈木提:《南方行》
維吾爾詩歌融合了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原的詩歌元素,不僅將哲學內容帶進詩歌創造出富有獨特韻律的格律詩,還以唱詩的方式保留了本民族的史詩。多數維吾爾詩人繼承這一傳統并與現代詩融合,展現出詩的哲學深度:
而黑夜的鬼魂
從墳墓中逃出
向世界索要詩。
……
將秘密說給大海
而大海指給我一片
傲慢的海浪。
艾買提庫·爾班的《斷續的夢囈》以重復定義的方式賦予天空以人性,將空無一物的天空做擬人化描寫:
一個有顆小小的心的少女
我稱之為天空
……
充滿淚水的眼眶
我稱之為天空。
詩歌一旦回望傳統,就會穿過記憶,召喚那消逝了的文化鄉愁,帶領人們在文明的廢墟和堆砌的浮華大廈里,揭示人類失去的和已經建造的同樣多的真理。為此,詩人以童年生活表現對消逝的文化家園的眷戀:
如果你不出來,我就向你的房頂扔土塊,
……
我騎著柳條駿馬來了,
……
麻雀將會在我的胸毛里筑巢,
孩子們將會在我的胡須上擺置土塊打 游戲,
我的手杖將會在你的門旁生根長成一 棵巨大的梧桐。
吾吉麥麥提·麥麥提在《當當當……》中通過幽默的表白刻畫了戀愛中的男女主人公,令人想起木卡姆中對舞男女風趣的情態,揭示出光陰轉瞬即逝,我從生命的我將會慢慢轉化成物質的我,此外,該詩還透露出賦予傳統意象以新意的意圖。
古典維吾爾詩歌有著說唱的傳統,因此民歌與詩人情同手足:
你的四十條小辮子是四十把梯子
貼靠在心之墻上。
四十個男人已爬了四十年
支撐著倒塌的蒼天。
——開賽爾·吐爾遜:《啊,哈麗丹》
《燃燒的麥穗》中出現了很多富有民歌情趣的詩:
長發蓬亂的帕媞瑪
連衣裙上有八十個補丁
走呀走在我的前面。
突然變成一河水
急湍地流向我的心。
艾海提·柯坪的《干渴的水》的前兩句引自“流浪的戀人”的詩:披頭散發、衣身簡陋、手持沙巴依,流離在各城市街道或戈壁沙灘的特殊的、神秘的群體吟唱的維吾爾民歌。把女人想象成河水也許源自人類集體無意識中將女性與水聯系在一起的基本思維模式。包括帕爾哈提·吐爾遜的《女人》中水的意象,都能讓人聯想到世界各地的創世神話。古代突厥人的創世神話中也認為神吩咐第一人從水的深處撈出泥土,要用泥土創造世界。當代精神分析學說認為,古代創世神話中水的意象來自人類共同的經驗即潛意識當中對母體或羊水的記憶。當然,水的意象有更深層的文化含義,悖論式的題目運用恰到好處,讓水的意象脫離它的原意,暗示了人類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始思維模式。
神秘性和想象力一直是維吾爾古典詩歌的特質,比如《詛咒》:
或者使太陽的風暴
星星的云降落的詞語
……endprint
那無風吹而動的樹的搖動
在沉默的黃昏中
——木拉提·買合木提:《詛咒》
視傳統為舊物和敵人的年代因現實的精神頹廢及道德墮落而瓦解,回望傳統其實是對現實喪失詩意及公正的抗議。當然,這不是期望用傳統扭轉現實,而是以傳統對照現實的文化鄉愁,期望傳統中優秀的精神遺產警告現實的錯誤混亂。然而現實總是試圖以荒謬推動荒謬,妄圖摘取荒謬到極致的桂冠,并為實用主義的輪子加足貪欲之油,令瘋狂的現實一路在荒謬中狂奔,不僅如此,它還要碾碎一切阻礙其瘋狂前進的精神力量,于是傳統再一次被傷害了。現實與傳統的關系因現實的價值混亂而被加上實用主義的華而不實的多余飾物而變得面目全非。為此,詩人重溫傳統,以反抗功利性推動一切并摧毀精神遺產的現實:
我們將泥土肉體留給傳統
久久地坐在靈魂的岸上
然后
將泥肉體與靈魂互換
我們走進夜之鐵籠,星轉斗移……
《塵世何時才來迎接我們》這首詩揭示了將靈魂與肉體亦即現實與傳統互換之后,人們的命運。傳統被消失之后,人們困于現實的禁錮,以實用價值作為衡量個人的標準,致使個體淪為物質及權貴的奴隸。
文字對精神、語言對詩歌的背叛加之暴力對肉體和精神的摧毀時常發生在以生活為鏡子的詩歌創作中。為減輕這種背叛和摧毀,詩人借助哲學和科學解決這一痛苦,亦即以科學的理性調和難以自控的感性。這一消除心理傷痕的努力,在《燃燒的麥穗》中顯得極為普遍:
凍死在雪山的逃難者尸體隊伍中你能認出 我嗎?因為我們尋求庇護的
同胞拿走了我們的衣服。現在你依然能看 到我們赤裸裸
的尸體。惡人將屠殺當成一種愛強加給我時
你可知道我與你同在?
……
惡人在大街小巷無法搜到我無影無蹤的軀 體時
你可知道我與你同在
……
腦子被擊穿的人轉去拉長的臉,尋找被擊 斃的原因
在他的視線中劊子手身影變得越來越模糊 并最終消失時
他那因子彈擊入而發熱的頭腦里映出的是 我的倒影。此時此刻
你可知道我與你同在
帕爾哈提·吐爾遜在《頌歌》中面對暴力和死亡表現出驚人的冷靜和清醒,并提出萬物同體、人類同根同源的哲學思想,為沉重的死亡現場注入了信仰的安慰。《頌歌》是極具控制力的一首詩,也是詩人以理性對抗血腥尋求精神和解的努力。在詩中,詩人譴責了盜用愛的名義逼迫同胞行惡的惡,譴責了手足相煎的悲劇。
詩人寫詩的目標,無非是使物質世界得到精神的純化,并使得到純化的精神穿越物質和黑暗,歸屬到精神的光明溫暖中,以精神之光召喚并溫暖真知之伙伴。詩人不盲目仇恨也不盲目愛慕的品質得到了詩之慧眼,并用此眼看世界,為精神和解尋找哲學性答案。
精神和解勝過其它,且總是以愛和美為基調。遠離了愛和美,一切藝術和信仰都是具有實用功能和教化意味的服務性的偽藝術、偽信仰。《燃燒的麥穗》的詩無一不展現出個體的痛苦所帶來的割裂及隔膜感造成的靈魂孤獨,這其實是渴望向和解邁進,又被思想的不自主或被綁架而被迫趨于毀滅的痛苦所阻礙:
我猛烈搖晃被強加的思想
將覆蓋著你明亮的黑暗的空白
從流放地掏出,并使之面對你
在面對中
在你滴落大海的黑奶中
……
我們的黑暗是我們的詞語
我們的黑暗是我們的眼睛
夏依甫·沙拉木的這首《正穿過你黑夜的》是對喪失自我的生活及被強加的抗議,但抗議失敗了,我變成黑暗的發言者,我用黑暗的眼睛觀察世界。這種思想及強加使我變成了黑暗、被迫流放。詩人表現了被強加的喪失的自我發展成消失的自我和轉變為黑暗的妥協的自我的人格及精神的異化過程。為此,詩人運用了將痛苦推向極致的表現手法:
兇兆在浴室里赤裸裸地游蕩。
拖曳著那燦爛的尾巴而遠去,
……
永遠在巨輪上孤零零地舉著一只手,
是什么使我如此苦苦等待?
當我的路在死亡的無限中呈現……
在《致諾查丹·瑪斯》中,帕爾哈提·吐爾遜在個人生活細節、人類宏大象征以及神話間轉換,在個人感受和集體無意識之間反復。
被顛覆的傳統價值觀念引起思想的混亂、靈魂的迷路,將個體置于文化和精神的鄉愁中,導致精神和靈魂的雙重痛苦。被極端物化的人成為被榨取價值的對象,這一現實進入詩人的精神,分泌出遭遇異化的詩歌意象,出現了被物化的女性形象:
女人啊,女人!
你就是創世之前在黑暗中蕩漾的那個 原始水。
……
你那處處圓形的肉體就像一個永恒的 迷宮,
廢除了所有的哲理和邏輯
《女人》表現了錯綜復雜的矛盾的兩性體驗。在禁錮的生活中,愛情的對象被異化成被征服者:從精神層面體現出喪失及否定個體價值的年代,男性在占有女性方面所取得的具有悲劇意味的異化的勝利。這首關于女性的詩,延伸了現實對精神桎梏的強烈程度,展現了在戀愛關系中男性對女性的物化:圓形的肉體、原始水、迷宮和火種。同時,這首詩似乎還隱喻了女人以感性拆解偽秩序對慣于秩序生活者所造成的驚恐。
我的心上,除了你別無畫像
你的心上,除了我別無畫像
來吧,我愛,讓我們死……
……
詞語會在唇上變成經文。
……
作為死尸的我們多么幸福!
在阿依努爾·買提吐爾遜的《來吧,我愛,讓我們死》中,愛成為死的宣言:愛遭到各種阻撓,也許是偽道德,但詩人并不向毀滅的力量妥協。endprint
禁忌表現出信仰和世俗、偽信仰與信仰及保持民族性與喪失民族性的矛盾中的禁忌和束縛。在禁忌中寫詩留有明顯的禁忌的痕跡,亦即心靈的活動處于極端矛盾中:渴望被理解又懼怕被理解,渴望和解又對和解因禁忌而退步,因而,詩中似乎隱藏著一種綁架的力量并借助某種神圣之力的綁架,迫使神圣越發遙遠。禁忌包圍下的舞蹈,以黑暗或反人性的意象表述黑暗,無一例外。雖然對光明的召喚始終是詩的主題,但在《燃燒的麥穗》中,黑暗似乎總能吞噬光明,詩人亦成為黑暗的一部分去吞噬一切發光的事物:愛、紅唇、太陽,代之以陰郁的事物:黑血、解渴的血、蛇。這都展現出在暴力和喪失自我的生活中,其他形象均已消失,只有受虐者成為唯一留存的形象。
不愿意在黑暗中永遠消失
也不愿意在火焰中永遠燃燒
流浪在黑暗與火焰之間
——帕爾哈提·吐爾遜:《木乃伊》
詩人對外部世界的不公正的審判,先從自身開始,展現出勇氣和真誠:
我們的黑暗是我們的詞語
我們的黑暗是我們的眼睛
——夏依甫·沙拉木:《正穿過你黑夜的》
政治藩籬對詩歌文本的影響無處不在,詩人跨越或墜落,都會對詩歌的精神深層發生影響:既渴望自由光明又絕望地將自身變成黑暗或捆綁自由的組成部分,形成這種非此即彼的思想根源便是現實對自由的禁錮。在兩難的選擇中,詩人回答:我無法選擇自由便要選擇喪失自由的痛苦:
黃昏之樹在無祖國的乳房上飛
在你被囚禁的永恒之洞中
我通過他們
——木拉提·買合木提:《無聲的蘆笛》
當個人喪失自由與尊嚴,一切皆淪為囚徒。既然現實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我便請歷史回答我;現實不能給予我心靈的安慰,我就不回答現實,而去回答歷史,找出那條歷史上毀滅過的道路,對照現實即將毀滅的道路,形成對古典傳統的模仿:
我從痛苦的深洞中出來,黑暗一片,
在白晝,我閃著黑光。我不憂慮,
我是唯一的漫游者。
……
以我的靈魂充滿空間的你
以空間充滿肉體的你
通過充滿而使我空虛的你
麥麥提敏·阿卜力孜在《手》中借用策蘭的手進行引申:手從痛苦的深洞出來,帶著隱喻性的黑充滿你。具備創造力的手,如雕塑家用手賦予無行之物以有形的靈魂。手的來處那深洞意味著黑暗、神秘和未知。
現實給予詩人什么樣的生活,詩人就會運用轉移法,借助詩藝及意象將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禁錮等轉移到詩中,向人們再現靈魂受捆綁的景象,以自身的痛苦或毀滅進行勸諫。而超常規的意象,源于畸變的生活。艾爾肯·努爾在《蛇頌》中為蛇正名,蛇因而具備了顛覆性的意義:被抹黑的一切我們不再信任,于是通過給蛇正名以抵抗被強勢抹黑的困境,還真實以真實。這種以黑暗的意象解釋黑暗,以惡解釋惡的手法,是維吾爾詩人具備的獨特詩性:通過蛇的意象重新闡釋黑暗與真理的關系,并以反邏輯的方式達到合乎邏輯的詩意。
蛇是海市蜃樓
領我們進入生命——
進入真理的黑洞,真理的邪惡
為進一步了解極端意象互文的精神內核,再引一首詩:
面朝海灘的失明
我吻我的黑戀人,在停落在夜晚的田野里
在她的紅唇上,我聞到夜晚
在她的乳房,開了石頭花
在她的懷抱,我鳴乎黑戀人
——夏依甫·沙拉木:《正穿過你黑夜的》
習慣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不知不覺已經變成黑暗的一部分:詩人給我們展現出主人公在愛人身上尋找黑暗,以黑暗吞噬鮮活的愛的特性,揭示了我之黑暗對任何事物包括愛情的無情吞噬,變現出黑暗將一切變成黑暗的不可阻擋的力量,以及我帶著光明的名義行黑暗之事的我的非。
詩人常會對自身的存在發生懷疑:放棄生命獲得自由,或放棄自由與那強大的黑暗融為一體增強黑暗,用黑暗解釋光明,寫出極端意象的詩,形成詩的悖論,讓兩種水火不相容的存在以極端的方式相處,展現出個體精神和生存的困境:
你是誰的墓碑在空中?
……
在被困于風中的夜的火鏡上
我看見光的微笑
……
我仍然不會拋棄搖籃;
而你讓大海
流入它的縫隙
……
當我的尸體揮動翅膀
風從坍塌的屋頂升起
……
溢向白夜
溢向母親白夜
——巴圖爾·肉孜:《無明月的白夜》
巴圖爾·肉孜的這首134行的長詩原名為《無月的月光》,譯者在翻譯時做了出色加工。原詩是一堆意義相反、互相對立的反義詞的堆積。用反義詞制造假悖論試的詩歌語言是維吾爾古典文學中常用的技巧。在多疑、嫉恨、撒謊成性的社會,這種假悖論試的語言模式是一種語言自慰的方式。
對不能言喻且對自身造成極大困境的事,詩人通過對大量意象的想象力粘合使它們對現實形成隱喻。當現實阻礙了詩性的表達,精神便拓展了詩歌的異質之路:通過對意象的高度變形及扭曲展現現實對個人的扭曲和限制,使詩歌帶有高度晦澀及抽象意味。由此,情感附著在黑暗而極端的意象上,展現毀滅和喪失的沉重;古代物我兩忘的詩歌境界已經失去的同時人類也喪失了物我兩忘的生活環境并不斷被迫轉換成物的價值的可悲宿命。一方面,維吾爾古老而開放的文化傳統凝聚成本民族的精神家園,另一方面以物質及權力決定人的價值的現實又讓現實直接拆散了傳統的意義,在大局難改的情況下,受傷害的文化鄉愁一方面需要傳統的撫慰,另一方面又被現實狠狠地踢開,致使一個個精神孤兒流浪在被拆散的傳統的廢墟上歌吟:
我欲沿著溪流走,endprint
重返童年。
在童年的岸上,
世界是一條溪流。
……
兩棵彼此喜歡的青草
為沐浴而啜飲溪水。
它們全身都長著眼睛
卻找不到自己的眼睛。
開賽爾·吐爾遜回顧童年并悼念喪失童貞的人類迷失于自建的龐大欲望迷宮中的命運。
去除詩的贅物,亦即去除精神的贅物。包括過渡定義、修飾、用主流文化權威規范少數民族文化、精神習慣、評價的桎梏對詩形成的傷害,避免政治化的語言、物欲化的定義及喪失鄉愁的自言自語的精神貧乏癥。我相信,破壞已經無法為創造提供任何益處和契機,再也不用遮遮掩掩地繼承和窮兇極惡地破壞,真正的鄉愁時代已經到來,在拆除家園和精神信仰之后,人人懷抱破碎的鄉愁,渴望回家而又無家可回,這便是當代人陷入的文化和精神的鄉愁。
《燃燒的麥穗》中,詩人真實地表現了內在的心靈,拋棄了純粹靠技術寫出的僵硬而充滿機械感的詩,力求詩歌簡潔、準確、樸素、具有思想深度。這在情感日趨枯竭的年代,維吾爾詩人去除了強加在情感領域的裝飾物,為權錢決定一切的物欲化世界注入了勇氣和愛:
我把我的手砍下來
丟給正把手伸向黑夜的一棵樹
然后,我試著從各個方向抓住你
麥麥提敏·阿卜力孜在《下沉的云》中為愛獻祭,甚至不惜毀掉身體的每一個充滿力量的部分去偎依愛人,揭示了愛是存在的意義。
此外,詩人書寫了很多思考禁錮與自由的關系的詩,從現實和精神兩難的困境中細致地觀察自我的角色及處境,以大量意象為媒介,推動詩歌的鏟子向精神的縱深處挖掘:
廢墟忙著做夢
憂傷閱讀我
——阿力木江·哈斯木:《天空》
他們把房子帶進房子里
把外面視為一杯熱茶,然后
倒掉,
——阿卜杜熱西提·艾力:《這是發生一些瑣 事的夜》
上兩首詩運用了擬物及夸張的手法,從日常生活入手,表現出人類思想和現實渴望走出自我卻又走不出自我對自我的限制。
拆除功利性文化權威預設的枷鎖,不為定義和圈定的概念寫作,是一個優秀詩人必備的品質。有形的枷鎖固然可怕,無形的枷鎖更加可怕;前者是被迫的被禁錮,后者則是自己畫地為牢。對傳統和不同民族文化的遺忘和埋沒,致使古老而優秀的傳統被埋入所謂的現代經濟廢墟,造成人們生活的迷惘及精神能源的枯竭。《燃燒的麥穗》中的詩人跨過了這一障礙,喚醒了傳統對人類靈魂塑造的同時加入了現代性的思考,為當代的靈魂物化癥及精神淺薄癥注入了一劑良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燃燒的麥穗》回到了精神領域,展現出個體對現實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對生命價值的重新定義,合力將維吾爾現代詩推進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亦即靈魂和精神的探索層面。
母語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故鄉,是一個民族繼承的秘密血緣。維吾爾詩人大多用母語寫作(詩集中還有幾位雙語詩人),保證了在精神內涵及韻律和節奏上不喪失自我之民族性,留存了富有尊嚴的民族密語更留存了一個民族靈魂的聲音。
我是被誤創造的一個
……
風吹過我的臉去親吻青草
我融入血紅色新物
我們對彼此才存在
——依合散·依司馬義力:《七次墮落》
母語就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標志。維吾爾詩人在用母語寫詩的同時,保持了向不同文化學習并將其融入自身的文化基因中,如買爾旦·艾海提艾力的《魯米老子辭典》:
我們就是不小心親吻了那些死了也不會失去酒香的嘴唇。
老子曰:“存在即非存在。”
開放性的文化傳統使古典維吾爾文化取得過輝煌的成就,雖然文革以后這種文化傳統變得封閉了,但在《燃燒的麥穗》中我依然能夠感受到。這條由維吾爾詩歌構成的精神的河流,從古代流到今天,保留了可貴的詩意和深邃的哲理及古老而優美的韻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維吾爾詩人均肩負著思考本民族精神歷程及推動維吾爾詩歌走向世界的使命。這部由314首詩構成的合集,不僅記錄了一個民族源源不竭的詩意,還在古典的傳承與現代的表現力方面展現出驚人的天賦。《燃燒的麥穗》是當代維吾爾詩人獻給世界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研究新疆維吾爾先鋒詩歌最具鑒賞性的文本。
作者簡介
江媛,女,1974年生,曾用名阿月渾子,喀什莎車人。主要從事詩歌、散文、小說創作和文學批評。19歲發表第一首詩《遺憾》,之后回到內地,在北京讀書,獲碩士學位,現今生活在中原。在《莽原》《時代文學》《綠洲》《山花》《南方文壇》等刊物發表詩歌百余首,著有詩集《喀什詩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