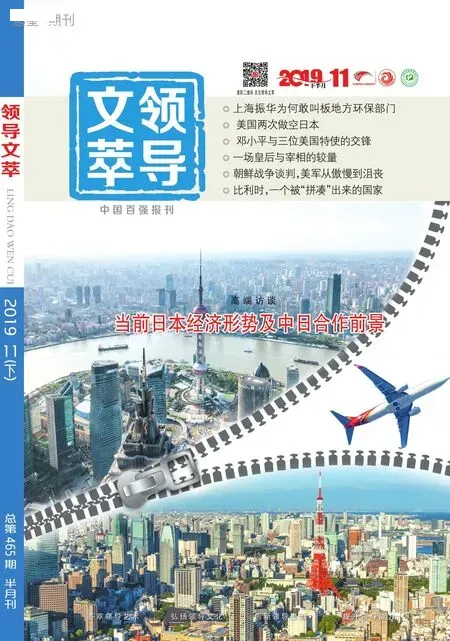中國“好故事”該怎么講?
環球時報
如何把握大勢、區分對象、精準施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文中的三位外國學者從不同地域、不同角度,論述他們所認知和期待的“中國故事”,對于有針對性地完成好此項任務具有參考價值。
【美】包道格:西方社會的疑慮
在40年的時間里,中國以高速的經濟增長,實現了這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巨大改變。作為一位很多年前就來往于中美之間的美國學者,我認為中國取得的成功不可否認。但是,要把中國的成功變成一個“好故事”,這并不容易,因為首先你要做到被中國之外的國家接受。
我認為,大多數人都認同以下這一點——一般來說,有關于中國對全世界所做的貢獻,如果是一個不帶有威脅意味的故事,那會是一個好故事。外界(西方國家)對于非西式民主國家所提出的方案,即便看上去心懷善意,但還是對行為背后的真實目的存在根本性的猜忌,如中國與其他國家合作發展經濟的計劃。所以,講述故事的人應理解這一點,要通過自己的故事令外界對其安心放心。
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點?首先,要坦誠地說明,中國從這些合作發展計劃中能夠得到哪些收益。其次,中國也應直面外界對其潛在戰略計劃的疑慮,例如擴大中國軍事影響力的海外基地。
不少中國學者、官員和媒體人都曾對我說,著眼于目前中國的一些成功經驗和經歷,他們認為這些內容很精彩,但是在國外、在西方似乎吸引人們的程度不如他們的預想,問題出在哪里?
我認為,當中共十九大報告說,可以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發展模式時,很多西方觀察家卻更愿意解讀其中對現有國際秩序推倒重來的意圖。換一種方式,如果能把中國模式稱作是“現有秩序和規則的補充”,則會讓國外聆聽者感覺不那么具有威脅意味。
眾所周知,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很多國家并不相同,而且中西方之間也有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最近一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越來越多地開始談論“中國影響力滲透”,一些學者將此定義為“銳實力”,那么他們到底擔心什么?我認為,如果在一些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協約上缺乏透明度,就會帶來不必要的副作用,就會對這些機構的宗旨和運營心生猜疑。此外,在海外地區堅持中國法律也會讓外界猜疑。當然,美國的海外機構也這樣做,只是會注意遵守美國法律和所在國法律,兩者相互不排斥。
一個怎樣的腳本才是講述“中國故事”的好腳本?我的建議是,坦誠地探討中國如今正在做的事情,這符合中國的內在需求,同時也不會給其他國家帶來不利。保持透明度,這將有助于中國投資者、發展者在更多國家受到賓至如歸的對待。
人們常說,在中西方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認識中存在“難以融化的堅冰”,我認為新晉的強大國家的確通常會招致猜忌。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國是這樣,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現在則輪到中國。
在人文領域,中國必須努力培養精通各國文化的人才。美國和日本在走出國門的早期也缺乏此類儲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逐漸重視并培養了此類人才。此外,在近代歷史上盡管中國曾經有過苦難的經歷,但今天仍要努力放下這些怨恨,相互間的報復難以有一個盡頭。(本文作者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
【日】天兒慧:日本的經驗
要想更多國家的民眾真正對中國懷有“親近之情”,中國在“講好故事”方面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第一,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一舉一動都會給國際社會帶來巨大影響,給各國留下強烈印象。中國對外國人講述的“中國故事”,應該與國外民眾在中國看到的,或者在本國看到的基本一致,這樣才具有更強的真實性,可信度也會大大提高。
第二,中國在海外設立了一些文化傳播和教學機構,希望以此提升“軟實力”。但有些機構和宣傳片給人“不自然”的感覺,感覺傳遞國家政治目的更多,有一種戰略意圖。這種宣傳會造成反效果,無法達到提升中國形象的目的。
第三,所謂“軟實力”,前提條件是這種文化由國家的土地、民眾自然孕育,“宣傳”只是為了讓外國人欣賞到本國文化。比如日本的漫畫、動畫片、清潔的街道和自然環境,這些自然產生的無形文化能給人帶來好感,從而塑造日本的良好形象。就目前而言,中國真正自然的、來自民間的文化傳播還遠遠不夠。
回顧日本過去的經歷,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期時,曾被嘲為“經濟動物”。當時,日本備受韓國和東南亞各國的指責,稱日本的發展是“由軍國主義的政治侵略”,改為了“由企業戰士的經濟侵略”。20世紀70年代后,日本開始努力將國家形象從戰前的“大國日本”,轉變為“和平國家日本”“為世界做貢獻的日本”。剛開始,這一努力并不被亞洲各國接受。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義”,這不僅是口號,也付諸了行動。日本不僅給東盟各國提供貸款,還為他們的經濟建設制定規劃,予以技術支持。
同時,東盟國家與日本還積極地就文化和社會問題展開學術交流,一方面讓日本專家學者和在當地的工作人員更深入地了解東南亞國家,也讓這些國家更清楚地了解日本的意圖,從而化解了相互誤會,增進了互信。20世紀90年代后期,東盟各國對日本的印象迅速改善,良好印象持續至今。
我認為,中國想要提高自己的“軟實力”,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但也不能照搬日本的例子。
第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留下了“負面遺產”。中國沒有這樣的“負面遺產”,中國要著眼如何改變當前的形象,而非歷史問題。對比來看,二戰后美國也提出“美國夢”,這個理念當時成為全世界人憧憬的象征。因此我認為,應該把“中國夢”的內涵擴充為全世界人們能夠共有的夢想。
第二,中國要活用民間的力量和創造力,要關注國際社會對這些民間力量的評價(包括負面評價),并幫助他們發展、改善。
第三,在以上兩點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展現出與國際社會協調協作的姿態。當前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等“國際公共產品”,絕大部分由西方國家設計,但已被世界其他國家接受,這也說明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找到同“國際公共產品”的價值聯結點,能夠讓其他國家更容易接受中國,認為中國是自己的朋友。(本文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學榮譽教授)
【索馬里】和丹:非洲的期待
自從非洲各個國家獨立并與中國建交以來,中國都是以一種平等的眼光看待跟非洲各個國家的關系。不管別人怎么說,非洲國家的領導、學者以及民眾,都將這些事實看在眼里。中國在非洲是一種友善的存在。
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都不同,但是,哪怕是處在同一文化和政治環境的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有些西方國家看待中國的視角是片面的,并且將中國的發展定義為“銳實力”,也是沒有真憑實據的。非洲的國家民眾親眼目睹了,中國在非洲到底是在以“銳實力”的形式影響他們國家,還是以實際改善民眾生活條件的方式,推行互惠互利的政策。
要讓中國的“成功故事”被更多非洲民眾所接受,甚至被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所接受,就需要讓這個“好故事”有更多符合他們文化習慣的元素和思維。
每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總伴有不好的一面,而這一面也應讓世人看到。有時候,塑造得太完美,很容易被人認為是虛假的。外界對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后來如何糾正錯誤,可能更感興趣。廣大發展中國家和非洲國家都需要中國的經驗。講故事時可以實事求是地從問題開始,逐漸過渡到中國的收獲和成績,這能讓人覺得更真實。
此外,要被非洲國家或者中國以外的國家接受,就需要站在各個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同時,要加入這個國家的專屬元素,用這個國家的語言習俗和表達方式去講述,這樣對象國的民眾才更容易懂得中國的“好故事”,明白能夠從這個故事中學到什么。這個故事還應從小事件、小細節、小人物開始說起,如果拿數據來講大道理,很多人可能缺乏傾聽的意愿。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認為中國的“好故事”在對外傳播中最大的問題存在于形式上。故事得脫離傳統宣傳的思路,對外傳播不要簡單強調以提高中國“軟實力”為目的,而應以表達“真誠希望改變世界上因為欠發達而造成的問題”為目的。除了對中國成功經驗的驕傲外,還要以真正地為世界上處于貧困狀態的人民著想,真正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來促進傳播。目的和態度的改變,將帶來接受度的改善。
如果讓我來設計一個講述中國故事的腳本,我會選擇講述小村莊的一戶家庭近40年的故事。首先從他們長輩的生活狀態開始,到父母前往北上廣打工的故事,再到他們自己創業打拼的故事,再到他們的孩子受到高等教育成為高新技術人員的故事。一個普通家庭的命運在40年里發生根本性改變,同時這個村子慢慢地發展成發達的城市規模,以及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方面的改變。
一個普通的故事能夠讓人懂得,其實這個改變的過程很痛苦很漫長,但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本文作者系浙師大非洲研究院東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