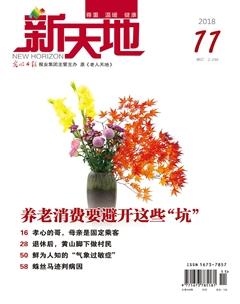票證·信物
李祝英
如果對老一輩人來說,改革開放如同“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話,那么對我而言,這40 年的變化好似“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有人把此前的年代稱作計劃經濟年代,而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便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票證。計劃經濟時期幾乎一切都需要票證;沒有票證,即使是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也寸步難行、無法生存。
這些票證包羅萬象,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像糧票、油票、酒票、糖票、布票、棉花票、自行車票、縫紉機票、煙票等不一而足。如我輩人恰恰經歷了票證的歷史變遷。
在孩提時代,經濟才剛剛放開,百廢待興,物質也不充裕,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需要沿用這些票證。家里買米買面買油都需要各種特定的票證。就糧票而言,得按照戶口根據年齡、性別、工種等按月發放。因為年紀小,我從來沒有弄清楚過這些糧票的使用范圍或者數量概念,只知道沒有這些小花紙什么也吃不到。多少次眼饞著油條店大叔炸的香噴噴的油馓子,可是老爸說身上沒帶糧票,有錢也只能作罷。
對于我們姐妹倆而言,每月的必修功課之一,就是一起長途跋涉走到外婆家,把屬于我們兩個的糧票給取回來。因為戶口在那里,我們的口糧也發到那里。隨著我們年齡漸長,分到的糧食越來越多。到了姐姐讀初中的時候,大概屬于一個人生命周期中最長身體最能吃的時候,她一個人就能有二十多斤糧食,是我們全家“收入”最多的富裕戶,比爸媽都多,把她得意壞了。當然我也有過此等輝煌,不過等我漲到二十多斤沒多久,糧票就取消了,大人們也極少提到黑市之類的字眼了。
過年是孩子們最開心的時候,大人們會從單位發到很多雞鴨魚肉,當然也意味著孩子們最忙碌的時候到來了。我和姐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按照老爸老媽給的票證上的日期去趕各種場子。今天在水產公司排隊領胖頭魚,明天去農副產品店排隊領肉。大冬天在橋頭排了整整一個下午,站到小腳麻木才領到一只鴨子。鴨子嘎嘎地伴著我們姐妹的歡笑終于回到了家,我們正打算向媽媽邀功請賞,鴨子生下一個熱乎乎的蛋,令大人們一陣惋惜,要知道鴨子可比鴨蛋緊俏多了。鴨子是餐桌上稀有的美味,鴨舌更是我們姐妹倆白熱化爭搶的目標,以至于老媽最后定下規矩,每次姐妹兩個輪流分得鴨舌。當然這些故事已經成為笑談,現在山珍海味也稀松平常,每次家里吃鴨子我和姐姐還象征性地把鴨舌讓給對方。這個時候全家相視大笑,一切盡在不言中啊。
小時候父母親的單位就是家,家也像安營于單位。從開水到夏天的冰水綠豆湯, 再到冷飲棒冰都是單位發票統一供應。從國家到省到市最后到單位,大大小小都有計劃,貫穿于老百姓的生活。現在呢,這些有關生活物資的票證都可以進博物館,而我們手里也多了一些新的票證,只是發證單位不同了。有各家蛋糕店的消費券、速食連鎖的優惠券、賣場商店的現金抵用券、零售鋪子的集齊可以兌獎的小卡片……無不印刷精美,個性鮮明。發票證不是東西不夠大家買的,而純粹是為了吸引顧客,刺激消費。
(責編: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