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梯上的少年
郎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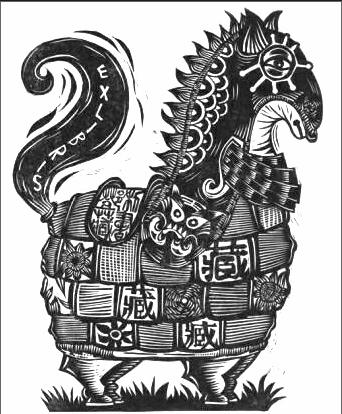
格桑多杰在村頭高處的路邊下了鄉村中巴車,他從公路邊往下看去,第一眼看到的是處于河邊的自家舊居遺址。那里現在只剩下兩米高左右的墻作為園地的圍墻,墻內種了一些農作物。那個地方原來是個不錯的地盤,可他的家遷到縣城之后房屋也被拆了,但無論他走到天涯海角,那里的房屋讓人難以忘懷。他的記憶和夢里再也沒有比這棟屋子的原貌使他想起童年的深刻記憶。然后他看了看那條村莊旁邊從北往南流淌的瑪依河,童年時是他和伙伴們探險的地方,曾經給他無比的快樂,也同時給了他無窮的遐想,甚至恐懼。緊接著,他想起了一些親戚的面孔,要看的景象應接不暇,熟悉的山峰和森林,曾經和父母并肩耕作過的田地,和伙伴們放過牛的草地等等。很快,有一個人的名字,卓瑪拉姆,閃現在他的頭腦。雖然她的臉龐是那么的模糊不清了,但她的名字保存在這個村子里,只要他踏上那里一步,卓瑪拉姆這個名字就自動彈了出來。他費了很大的勁兒,也實在記不起她少年時的面容,畢竟相隔也有二十年了,但那些故事記憶猶新,無論他走到哪里都時不時地回憶起來。他朝著卓瑪拉姆曾經的家望去,看見的是一棟新藏房,與他記憶中的完全不一樣。
那棟房子面朝西南,偏黃的土墻上有很多大窗戶,木窗上的彩雕顏色絢麗,圍著窗子的絡腮胡形的黑色框飾也顯得格外肅穆,能看出是新修的大概35根柱子那么大面積的房屋。他記憶中原先的房子是面朝東山的,房子大小應該只有24根柱子那么大,樓層高度也比現在的低很多。當時的房子門窗上一律刷的是朱紅,窗邊框飾刷得黑油油的,紅黑兩種顏色的搭配象征一個家庭的威信。這棟新房子不能讓他想起兒時舊屋的印象,反而干擾他惦記起過去的景象,因此他發覺到舊屋除了故事,其余都早已跟隨歲月而逝。
他把背包放在一棵小柏樹旁,坐在地上望去整個村莊。那棟房子里曾經住著一位姑娘,關于她的故事也許太多,但每個人心里的記憶都是一部秘密的自拍自演的電影。他心里的她也是獨一無二的,雖然二十年沒有見過面,但發生過的故事是那么的記憶猶新。
她叫卓瑪拉姆,乳白色的臉,整潔發光的牙齒,個子高,動作輕快,能干能玩……,當時格桑多杰大概十二歲的時候她比他大兩三歲。這個幽靜的村莊當時來的外地人比較少,四面環山,白色藏房像珍珠一樣撒落在大河的兩邊。村民都在山里或者田間忙碌著,偶爾有人走出家門去到河邊挑水,或者你在寬闊的青稞麥浪中看到一位婦女伸直腰桿把手里的雜草小捆扔到田埂上。她又開始彎下了腰撿地里的雜草,而離田地不遠的河流在陽光的強照下閃光凌凌,河水隨著自己自由的步伐流淌著,多么地平靜自如,時間與自然的節奏是同一個步伐。每一個童年時段都有新的景象和發覺,孩子們心里也有了自己喜歡的和討厭的村民。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卓瑪拉姆就成為了這個村莊里被喻為龍女的小名人。除了她美麗的容貌,人們從小就在她身上發現一種獨有的賢惠,都說她很活潑可愛。當時,格桑多杰看遠處的青山好像卓瑪拉姆在那里呼喚著他的名字,那清脆的叫聲遙遠而深刻,隨高空刮來的清風而至;到河流旁邊,他從木橋上看到她在水里像魚兒游來游去,時而回過頭露出純潔美麗的笑容;他在田地里追趕蜻蜓時,注意力被一只蝴蝶吸引住,那也是卓瑪拉姆的化身在牽引他的好奇心;睡夢中的月兒彎彎掛在碧空,她卻坐在彎月之上笑著看他在打盹……。
在格桑多杰接近十三歲的時候,她臉上青春賦予的微紅和處處散發的活力色澤更是讓他的心進入無窮的想象。他從小是一個在自己熟悉的小環境里尋找豐富樂趣的男孩,但十分羞于在眾人面前展現自己的才能,何況去找卓瑪拉姆一起玩耍。在別人家里,看到愛吃的東西,他客氣半天才吃一點點。對于卓瑪拉姆的那種強烈感覺,是對美的一種純凈的樂趣,是他成為少年時找到的一種無瑕的友誼。覺得在她的孩童時代,她就是一道美麗的風景,允許他的想象去點化她的每個角落。對于她的那種單純的感覺走過了幾個年頭,當時他絲毫沒有想擁有她或者獨占她的那種感覺,只是認為她是自己的世界里盛開的一朵美麗的格桑花,她的清香催化著他的成長。
不久,他成為了一名寄宿制學生,挎著他媽縫制的勞動布書包,里面裝著裹得像卷心菜的書和斷了頭的鉛筆。他皮膚曬得黑黝黝的,但五官端正,鼻子高,眼睛大。除了周末都住在離村莊有六公里遠的學校。雖然學校里看到了一些新的面孔,但那時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去學校。除了覺得學校剝奪了自己自然生存的環境,也覺得老師些特別嚴厲,同學們矛盾重重。他們因為沒有背誦完漢語拼音,被老師關在教室里不放學,透過窗戶遙望著美麗的村莊,餓壞的肚子叫得咕嚕咕嚕響。對于他們來說,不知道拼音是用來干嘛的。當時所有的家鄉人都說藏語,拼音這個東西對于他們來說比老鄉們念誦的咒語還要難。有一年的暑假開始了,解脫真的來臨,他和他的好友扎西收拾好了東西。他們激動得不知道怎么選擇返回村莊的路,有一條是順著公路走,還有一條是大河與田地之間那片蔥郁的草地上的小路。最后,他們踏上翠綠的草地,清凈與美麗能把他們的憂愁都消除干凈。本來只需要一個小時不到的路程,他們就走到天黑才進入村莊。草地上的泉眼和旁邊的水草,好像是上天準備好給孩子們的禮物。花朵的清香和迅速在空中互相追趕的蜻蜓,是神山賦予這片土地的恩賜。青稞麥浪和土豆花,還有河邊開滿清秀白花的賁穗樹,都是那么的美麗,是村民們求佛所得到的恩賜。
暑假的第一天早晨,格桑多杰在他母親上下樓梯給家畜喂東西時的咚咚聲和嘴里不停念誦經文的嗡嗡聲中慢慢醒來。是個很興奮的早晨,心里充滿了太多的計劃而猶豫不決。要去水磨房的小溪里看魚,還是去對面山上撿蘑菇;到村頭柳樹林里找喜鵲蛋,還是到村尾草地上找馬兒騎;到寺廟去看看壁畫,還是找牛童們一起去野外玩游戲。他的思慮被他媽媽的叫聲打斷了,只好起床吃早飯。
“快吃早飯,然后把牛放到孔大崗山頭去。”他的媽媽斯朗翁姆說。
“媽媽,晚上可以吃牛肉土豆包子嗎?”他問。
“可以,一定要把牛放到山頂草壩上,別放在山面松林間就跑下來。”
格桑多杰把鍋魁捏斷后一小塊地放進大碗里,上面放些奶酪,然后把滾燙的酥油茶倒在上面。他用小瓢攪勻了酥油茶泡饃后呼嚕呼嚕吃了起來。吃完飯后,他媽媽在底層牛棚里把一頭頭牛從柱子上解開了栓繩。牛群很快走出了大門,格桑多杰跟著牛群也跑了出去。因為山頭的小路太多,想把牛趕到父母指定的地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些牛最喜歡順著它們想走的小路溜走。格桑多杰時刻盯著引路的那頭牛,摔石頭來趕它走上山頂的草壩。就這樣,他花了一個半小時才把牛趕到山頂平坦青翠的草地上。他仰臥在長滿野花的草地上,看著清空中的白云朵朵,滿頭大汗。他坐起來時看到山麓的村莊像一幅唐卡畫,清晰而美麗。他能看到每一個家庭的房屋和條條小道。他回頭看了看牛群在吃草,然后順著松林間繞來繞去的小路下山了,不到半個小時他就到了村頭。他在木橋上看見一個人影,很快認出是扎西。
格桑多杰一口氣沖下村頭公路的邊坡,穿過村舍間的小路,順時針方向繞過村頭的白塔和轉經房到了橋頭。那是一座傳統木橋,兩岸的橋臺是大小均勻的圓木疊加搭建的立方形結構,里面填滿了大小石頭。河水中央有個用粗大均勻的圓木疊加搭建的橋墩,高兩米左右,由上游一側的立體三角形,中間略高的立方形和下游一側的立方形構成,里面都塞滿了堅硬光滑的大石頭,再猛的水流也沖不掉橋墩。接近十米長的五條整塊木頭制作的橋梁分別從兩岸的橋臺伸出來剛好在大河中央的橋墩上接觸,并緊緊相扣在一起。那座木橋雖然不大,但給人們的生活不僅提供了方便,也成了他們交往的橋梁。有坐在暖暖的橋面上聊天的老人,有橋頂上跳下河里游泳的大男孩,也有光著身在橋墩的圓石上曬太陽的兒童,甚至有的婦女在橋梁或者橋臺上洗刷衣服。
扎西坐在橋梁邊沿上,雙腿從橋梁外側伸下,很認真地朝下看著水里的魚兒。格桑多杰輕輕走過去,嗨一聲就抓住扎西的肩背輕輕推了一下,這讓扎西驚慌失措,掙扎著把兩腿縮了上來,滾到橋梁中間。
“求你了,別開這種玩笑,你讓我失魂的。”扎西道。
“失魂有啥擔心的,我給你請來古絨村的巫師為你招魂。”格桑多杰說。
“叫你給村子里的姑娘們開玩笑,你就像個膽小的老鼠,對于我你啥樣的玩笑都能開。”
“對姑娘們有啥開玩笑的,她們只會哭鬧。”
“你算了吧! 看到卓瑪拉姆,你靦腆得呼吸的勇氣都沒有。”
“這是我根本不想理她們,難道我還怕她們嗎?”
“不是不想理,誰都知道你喜歡卓瑪拉姆。”
“我的媽喲,你這話是怎么瞎編的,我媽媽知道了我連回家都不好意思。”
格桑多杰逮住扎西的兩只手,狠狠地把他壓在橋梁上。
“你再敢說我喜歡卓瑪拉姆,我就把你丟進河里。”
“求你了,我知道你對男孩些最兇,若你想壓住任何人,你就去壓卓瑪拉姆,別在橋上壓我。”
雖然格桑多杰比扎西大一歲,但他確實也認識到扎西比他懂一些關于女孩子方面的事情。說的也是,格桑多杰確實受到了卓瑪拉姆很大的影響,他對這個山谷里充滿的好奇心越來越被卓瑪拉姆占上風。以前他覺得花兒里最美的是格桑花,但卓瑪拉姆的笑容漸漸替代著格桑花的妍麗。他覺得最純潔的是村尾草地上剛剛冒出地面的清泉,但卓瑪拉姆的眼睛有一股清澈的眼神總是沐浴著他童年的煩惱;他總是相信放牧時分聽到的布谷鳥之聲是最悅耳的聲音,但有一次撿松茸時聽到卓瑪拉姆的歌聲后,他的腦海成了她歌聲繚繞的秘境;他認為村頭溫泉里游來游去的魚兒是最活潑動人的神奇物種,但看到卓瑪拉姆和村民們跳起鍋莊時,她優雅別致的舞姿才能展現孩童們成長的姿態;以前阿爸講過格薩爾王的王妃卓姆姑娘是三界最美的女人,但格桑多杰堅信如果讓卓瑪拉姆穿上卓姆的盛裝,那么天底下誰都不會勝過她……。
“嗨,輪到你走神了吧?”扎西說道。
“我才不走神,我在想怎么度過這個美麗的暑假。”格桑多杰回答道。
“你只知道怎么樣去打游擊戰或者怎么樣去抓野兔子。”扎西說。
“那么你知道些啥?”
“比你想到的多,比你想到的有意義。”
“說吧,只要不去偷那位五保戶老人煮的洋芋,我都可以考慮。”
“你知道卓瑪拉姆的父母去轉神山了嗎?家里這些天只有她一個人。”
“這有啥大驚小怪的?”
“誒,這你就不懂了,天黑了我們可以去找她。”
“找她干嘛?”
“可以跟她睡覺覺。”
扎西邊說邊伸出雙手準備擁抱格桑多杰。
“去去,我最討厭你的這些怪模怪樣的動作。”
“哎,說你笨你就不高興,我們不去找她,早晚被其它村子的兒子些占用的。”
“我的媽喲,你這些是怎么想出來的,難怪你每次考試得的是雞蛋。”
“村里從老人到小孩,只要是男的,都喜歡卓瑪拉姆,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喜歡啊?”
“你這個小兔崽子,我從來沒有說過喜歡她。”
格桑多杰站起身子準備抓扎西時,扎西很快跑到了橋的另一邊。
“別跑,我不打你,我們去看看你爸爸那里能要一根香煙不。”
這時,巴登尼瑪叔叔走了過來。他是一位長期放牧的人,喜歡開玩笑。
“你們倆在橋上等哪個家的大姑娘?”
格桑多杰感到很靦腆,對那樣的話不知道如何去回答。扎西笑瞇瞇的,好像他發現了什么重要的線索。
“你們倆,看上去就沒有膽子,我在你們那么大的時候,村里的所有美女都睡過了。”
格桑多杰感到很尷尬,不知道巴登尼瑪叔叔為什么那樣說他們。他倆走回了村子,往扎西父親做鐵匠的地方跑去。
“我說過,所有男人都在想村里的姑娘些,巴登尼瑪叔叔也是。”
“你怎么學到了這些東西,別管大人的事。”
“你比牦牛還犟,我在很多地方佩服你,就對姑娘們害羞這個,我真看不起你。”
“不要你看得起我,也別胡思亂想,我們是小孩。”
“你聽聽大人們講的話,他們十幾歲,也就是我們這么大的時候就開始盯上自己的對象。”
“我才不要,我們是學生。”
“好吧,反正能說服你的人還沒有誕生。”
格桑多杰和扎西偷偷去了扎西父親的工作棚里,他父親是個鐵匠,名叫羅絨稱勒。他是個脾氣很好的人,一般扎西偷偷拿走他的幾根香煙他都不怎么生氣。格桑多杰和扎西蹲在一邊,眼睛盯著羅絨稱勒在打鐵,他用鉗子把燒紅發亮的一塊鐵從炭火中取出,舉起錘頭在上面均勻地打了一節,然后就把那個鐵塊放入了盛有冷水的木槽里。淬火時冒出很大的霧氣,小小的鐵匠棚里變成了一個蒸鍋,彌漫了霧氣。
“格桑多杰,你爸爸最近在忙啥?”
“他去縣城辦事了。”
羅絨稱勒站了起來,他身上穿著一件棕色布料做的藏袍,很薄很輕。他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同樣的藏袍,說脫掉藏袍是個很困難的事情,脫下后感覺失去了一種古老的優雅和風度。但村子里越來越多的人都習慣了穿現代服,堅持穿藏袍的女性占多數,男性越來越少。他頭上還戴著一頂撮箕帽,確實像個藏族版的上世紀工人。他是個瘦高的人,皮膚黝黑,笑起來時兩眼邊到嘴邊縱向的笑紋構成了一個葫蘆形,他很喜歡開玩笑。他走出棚子上了廁所,剩下了格桑多杰和扎西兩人。扎西迅速跑到他父親坐的位置,在皮坐墊一側找到了一包煙。他問格桑多杰要幾根,格桑多杰豎起了四個手指。 格桑多杰和扎西等羅絨稱勒回來后離開了鐵匠棚,他們去河邊坐著抽了那四根煙。下午時分,格桑多杰回家幫他的母親喂牲口,扎西平時都比較悠閑。
格桑多杰幫母親拴好了每一頭牛,也幫母親把秸稈粉放入一桶桶木桶,上面倒些煮好的元根湯,然后一桶桶放在每頭牛的前面作為它們的晚餐。他媽媽擠完奶之后叫他從牛犢圈里放出那頭牛媽媽的牛犢,小牛猛拉著他,沖到牛媽媽身下吃留給它的奶子。格桑多杰幫媽媽挑水,還要把當晚要燒的木柴從大院里摟著放到二樓大灶旁邊。還要用小斧頭劈一些松枝作為松燈。差不多要完成家務時,格桑多杰聽到大門外有人輕輕叫了他的名字,一聽就知道是扎西的聲音。
“大忙人,需要幫忙嗎?”
“快完了,不需要幫忙。”
“那就出來玩嘛。”
“我還要喂狗,還要去經堂里下掉供奉的凈水。”
“快點,我在木橋那邊等你。”
等格桑多杰忙完之后,太陽早已落入西山背后。他給媽媽說好之后終于出了家門。他兜里還有一塊錢,他想著同扎西一起去看電影。順時針轉過白塔和轉經房后來到了木橋邊。那邊有幾個婦女在河邊挑水,也有幾頭晚歸的牛在木橋上匆匆趕來。
“扎西,走開,擔心牛把你撞下河里。”巴登尼瑪叔叔大聲喊了起來。扎西匆匆忙忙跑到橋臺的一側,巴登尼瑪叔叔就滿頭大汗地吆著牛走了,只聽見牛脖子上的鈴鐺鐺鐺響著消失在村子里。除了在轉經房里轉經的幾個老人和一些小孩之外,橋邊越來越安靜了下來。格桑多杰邀扎西去看電影,但扎西說他有更好的主意。 等橋邊和轉經房里都沒有人影之后,扎西說他看到卓瑪拉姆一人在家里。
“今晚不把握時機,以后再也沒有了。”
“啥機會?”格桑多杰不可思議地問扎西。
“要去和卓瑪拉姆睡覺咯。”
扎西張開他的大嘴巴,露出參差不齊的牙齒笑,得意地點著他圓圓的頭。
“我不敢去,也別給我提‘睡這個字,惡心。人家天黑就會關掉門的,而且她家的狗夠兇的了。”
“你放心吧,我已經有了所有的安排。”
扎西對他要做的事情充滿了樂趣和信心,格桑多杰忐忑不安,不知道將要發生的故事會對他有多大的影響。 天色已黑,村里除了在一些敞開的窗戶里看到幾點弱光,有狗在某個角落叫了幾聲之外,其余都回歸到黑夜的寧靜之中。
“走,跟著我來。”
“算了吧?我有點害怕。”
“不用怕,一切后果我來承擔。”
扎西帶格桑多杰來到了一座曬床[ 曬床:也稱曬架,藏語稱之擁尺或者雜尺,意為曬元根和野草的臺架。]旁,離卓瑪拉姆家很近。
“我們的計劃是背著這個曬床上的木梯,從卓瑪拉姆家側面的曲繞窗戶[ 曲繞窗戶:曲繞為大水缸,藏族人家放大水缸在大灶后的墻角,并用水缸柜子裝飾出來,在側墻上修一戶窗子為水缸取光。]里爬進去。”
“我的媽喲,你這是著了魔吧?怎么敢背阿巴秋美家的木梯? 他會割掉我們的耳朵。”
“哎呀,你別緊張,我都想好了主意。晚上放回原處不就對了嗎?”
“我的媽喲,扎西,你這是怎么學會的。”
“大人們不是經常講這種故事嗎?”
“我沒有聽說過。”
“你放心吧,我們又不是去偷東西,你甭怕,一切后果由我來承擔。去看看她有啥不好。”
扎西取出一包煙,遞給了格桑多杰一根。他們點上火,開始抽了起來。黑夜中,村頭他倆的煙頭組成了一對移動的火花。抽完之后扎西站了起來,說要開始最精彩的故事。格桑多杰勉勉強強地配合了扎西,他們倆背著一條三米左右長的木梯一步一步地向卓瑪拉姆家側面的小窗戶走去。
“輕點,你抬起梯子的頂部,站在梯子下往上舉起。”扎西在黑暗中說。
“你抱住梯子低端,我往上抬起的時候你也跟著往上推。”格桑多杰說。
“噓噓! 用力別太大。”
“狗在叫,別動。”
他們倆一下子停了下來,格桑多杰的心跳越來越加快,好像無數個眼睛在黑夜里監視著他,嘲笑著他。 扎西反而趴在地上咯咯地笑了起來,格桑多杰踢了他一腳。
“你這傻子,笑個屁。”格桑多杰說。
“我在想卓瑪拉姆稍后會不會在睡覺之前讓我們洗腳。”
“你想得美吧,我的腳好幾天沒洗,我不好意思脫鞋子。”
“哈哈,所以我想她也許給我們端來溫水,讓我們泡腳。”
“不會的,她讓我們喝點茶就夠給面子的。”
“也許她會煮肉,下面條給我們吃,絕對是最好吃的。”
“哎,你別說了,我最喜歡吃面。”
“我們請她唱山歌,你也準備一首哦。你就這樣唱吧:‘我是絨毛大藏袍,只缺沒人來穿著;我是精巧竹笛子,只等有人把我吹……。”
“我,不,我最怕在她面前唱歌。”
“說明你喜歡她,她征服了你這匹小駿馬。”
“別亂說。我還是很緊張,我覺得我們算了吧?”
“絕對不能放棄,你放心,一切由我來承擔。”
格桑多杰感到自己從來沒有如此緊張過,但說不出為什么不拒絕扎西的鬼主意。他看了看天空中出現的幾顆星星,其中最亮的那顆就像卓瑪拉姆的眼睛,如此的明亮有神。但村子里大部分男孩都喜歡她,聽說其它村子的有些男孩也很喜歡她,但她心中到底有沒有一位她最喜歡的男孩呢?
“你覺得卓瑪拉姆會喜歡哪個男孩?”格桑多杰問。
“這個很難說,她平常對誰都好,像個大人似的。”
“對了,她確實比我倆大幾歲,我們還是放棄吧?”
“放棄?你瘋了吧!就算不能跟她睡一晚,就吃點她做的東西都算個勝利。”
“也許她只喜歡大男孩,那些打架很兇的男孩。”
“我們也不小了,要學會大男孩們做的事情。”
“要是我們都十六歲了就好,村里的男孩些不敢取笑我們。”
“別管那么多,先來抽個煙,做到了才算男人。”扎西說。
扎西給了格桑多杰一根煙,他們在卓瑪拉姆家的墻角里抽了起來。雖然有一彎月亮在云間忽隱忽現,但整個村子沉睡在黑夜的籠罩中。
“出發了,誰先上?”扎西問。
“當然你先上啊!”格桑多杰說。
扎西兩手握著梯子的兩邊,慢慢攀登了上去。
“輕點。”
扎西接近了小小的窗戶,他從窗門縫隙中仔細窺覷了一眼。
“只有她一個人。”
扎西輕輕回頭,給地面的格桑多杰說。
“真的嗎?”格桑多杰微微的聲音恐怕扎西才能聽得出來。
“不信你來看看。”
扎西從梯子爬了下來,讓格桑多杰登上去看。格桑多杰爬到梯子高出,從窗門縫隙看了看,確實看到卓瑪拉姆一個人坐在大灶邊織毛衣,火光下她的臉顯得那么的溫和而美麗。
“確實是她一個人。”
“那么你就推開窗戶啊。”扎西說。
“我才不推,你自己來。”
“哎,除了你年齡比我大,其它什么都比我小。”
“你的主意你來干。”
“快下來,看我的。”
格桑多杰慢慢下了梯子,扎西又爬了上去。扎西從窗戶縫隙里看看了,然后給格桑多杰說卓瑪拉姆是落在梯子之頂的小星星,為了她,我們值得攀登梯子。格桑多杰叫他住嘴,但也感到扎西是個不可思議的家伙。扎西輕輕推開了窗門,卓瑪拉姆在窗口上看到他黑黑的小臉蛋,除了羞澀的笑容,再也沒有什么有滋味的部分,中分的頭發,眼睛里充滿了猶豫。
“嬉皮笑臉的,你在干嘛?”
“嘿嘿,我,我,我前來向你說一聲,有空的時候我也愿意和你們去放牛。”扎西吞吞吐吐地說。
“那么進來啊,從窗口掉下去我可負不起責任。”卓瑪拉姆笑著說。扎西想,她總是一位喜歡笑的姑娘,純樸而美麗。
“我還有一位朋友。”
“是哪個?”卓瑪拉姆問。
“格桑多杰。”
卓瑪拉姆哈哈大笑,說格桑多杰居然也敢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兩個都進來吧。”卓瑪拉姆溫柔地說。
“你不會打我們吧?”
“打?如果想打,我早就把你從窗口推下去弄死。”
“好吧,那么我倆要進來了哦?”
“別待在黑糊糊的窗頭,快點進來喝點茶。”
扎西輕輕地把他的一條腿放進了窗戶的內臺上,鞋子上有兩個補丁,沒穿襪子,腳桿上都是灰塵和泥巴。卓瑪拉姆保持著她的微笑,點頭讓扎西進來。扎西回頭叫了一聲格桑多杰。
“快登上來,卓瑪拉姆邀請我們進來,別怕。”扎西說。
“我算了吧,你去吧。”
“別啰嗦,快點,她叫我們進來喝茶。”
格桑多杰勉勉強強也爬了上去,扎西把身子轉入窗門,從窗戶上跳到木地板上。格桑多杰的臉出現在窗門口,幾乎是失色的臉,中分的頭發,上身穿著一件灰白色南美服西裝。她看到卓瑪拉姆時幾乎像個掛在蜘蛛網上的飛蛾,不知道下一步要做的什么,他滿頭大汗。
“哈哈,你那么害羞還來。快快,進來吧。”卓瑪拉姆叫了一聲。
“就是嘛,快點進來吧。”扎西鼓勵格桑多杰。
“別站在窗口像個小偷,外面有人看到你就會用石頭把你打下去的。”卓瑪拉姆補了一句。
格桑多杰把他的一條腿放進了窗戶的內臺上,是一只穿破了的回力鞋子。然后他把身子伸進窗門,把另一條腿也放在窗戶的內臺,輕輕跳到房間里。
“哈哈……兩個賊都落網了,收拾吧!”
卓瑪拉姆把窗門緊緊關上,突然,她家柱子的背后出現了兩位阿姨。她們笑不成聲,一位阿姨拍打著她自己的膝蓋笑,另一位邊笑邊敲打著腰部。卓瑪拉姆同他們一起笑得眼睛都變得濕漉漉的,好像他們在看漢族人耍的猴戲。
“好吧,這下子要好好收拾你們兩個小屁娃。”其中的一位阿姨叫次仁卓瑪,另一個阿姨叫斯朗曲措,她們都是村子里的親人。她們倆迅猛跑過來把扎西和格桑多杰壓倒在地板上,開始用她們的手掌狠狠地打了起來。格桑多杰格外緊張和羞澀,屁股被打得疼痛不算什么,就是羞愧讓他麻木得好像要靈魂脫了殼。他抱著頭在地板上蜷縮了起來,身體好像在燃燒。
“求你們了,以后再不敢了,哎呦呦,啊呲呲…”。扎西不停地在地板上打滾,次仁卓瑪阿姨很興奮,咬著牙齒,一邊擦著嘴邊的口水一邊壓著扎西狠狠地打屁股。次仁卓瑪是一位喜歡開玩笑的女人,平常在村里做游戲,她積極參加,有的時候甚至敢迎接男人們的挑戰。她冷笑著,扎西越是求她,她越感到興奮。她把普玫長裙的一個邊角撩起來夾在腰帶間,然后舉起右手掌邊打扎西的屁股,邊問以后還敢不敢犯類似的錯誤。
“不敢,再也不敢,我向阿克瑟徹護法神[阿克瑟徹:一位格魯派的護法神。]發誓,以后絕不犯這樣的錯誤。”
“是誰叫你們來這里的?”斯朗曲措阿姨壓著格桑多杰問道。她用右手揪了一下格桑多杰的耳朵。
“是扎西的主意。”格桑多杰泣不成聲。
“不,我也是無意中聽到我爸爸他們大男人在聊這些事情。”
“你倆是大人嗎?是大人都不能爬窗戶的,小屁孩,要好好教訓。”
兩位阿姨繼續打了幾下,她倆都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她們豎起腰桿,兩手叉腰,笑不成聲。卓瑪拉姆趴在地板上笑,眼睛濕漉漉的,她看著扎西和格桑多杰好像已經掌握了以后嘲弄他倆的最佳武器。
“倆小兔崽子,以后還敢不敢?”
“不敢,不敢。”扎西淚眼汪汪,格桑多杰低頭抽泣。
“你倆哪個先提出的主意?”
“是我提的,嗚嗚……”扎西張開大嘴,涕泗滂沱。
“我就知道是你,你爸爸那個色鬼最喜歡在村里聚會時講怪模怪樣的男女事情。”次仁卓瑪說。
“好了好了,別哭,再哭就用皮鞭子狠狠收拾你們倆。”斯朗曲措阿姨說。
“就是,這個算最輕的了,我們準備把你們的小雞雞割下來。”次仁卓瑪說。
她們三個女的都笑了起來,她們很享受發生的一切事情,又說要嚴肅以待。
“你們倆過來坐在灶邊。”斯朗曲措給了他們倆一張架登坐墊[ 架登坐墊:一種東藏康區等地的藏式坐墊,用皮革做外套,里面裝特殊干草,可以折疊。]。
次仁卓瑪用很大的銅瓢從灶上的大鍋里舀了開水,然后加了一點冷水后叫格桑多杰和扎西到客廳門口洗手。
“把臉也洗了,你們上學了還不知道洗臉嗎?”
“好哦,好哦。”他們倆異口同聲說道。
格桑多杰和扎西用溫水洗了他們小小的手和圓圓的臉蛋。然后跟著次仁卓瑪阿姨走進客廳,坐在墊子上烤火。卓瑪拉姆在灶的背后偷偷看著扎西和格桑多杰笑,她在幫斯朗曲措阿姨蒸包子。
“看這兩個男孩,洗了臉以后多可愛。”斯朗曲措阿姨說。
“是的,是大人些亂教,把他們給教壞了。”次仁卓瑪阿姨說道。
格桑多杰的羞澀漸漸也清淡了一點,他能感覺到灶邊的溫暖,也能聞到鍋里正在蒸的包子。扎西很快恢復了他的嬉皮笑臉,不停地看著三位女士。
“扎西,你還看我們三個干嘛?”次仁卓瑪狠狠盯著扎西問。
“不不,沒啥意思,就是覺得你們對我們太好了。”
次仁卓瑪,斯朗曲措,卓瑪拉姆都笑了起來。她們在做蘸水,打酥油茶,還有當地吃包子時不可或缺的奶酪酸水。包子從蒸鍋里取了下來,他們倆的碗里裝滿了酥油茶。整天沒有好好吃飯的扎西和格桑多杰開始咬著牛肉松茸包子,大口大口吃了起來。三位女士能看到扎西脖子上上下移動的喉嚨時又笑了起來。
“現在你們兩個都是學生了,要聽老師的話。”次仁卓瑪說道。
“嗯嗯。”
“村里男人們說的怪話聽不得,他們沒有上過學校。”
“嗯嗯。”
“等你們考上學校,拿到工資時來娶卓瑪拉姆。”次仁卓瑪說。
她們三個都笑了起來,卓瑪拉姆感到很羞愧。
“其實他們以后有了好的前途,就會把我們這些鄉下阿姨忘掉的。”斯朗曲措說。
“不會的,絕對記住。”扎西說道。
三位女士又笑了起來,格桑多杰也笑了起來。在微弱的燈光和火焰的照射下,五個人進入了融洽的氣氛中,雖然有些羞澀,但兩個孩子也放松了許多。
“你們倆剛來到窗戶底下時我們就發現了,還抽煙。”次仁卓瑪說。
“你們再聰明都超不過我們的,好好學習。”斯朗曲措說道。
“好的,吃完了走吧。”次仁卓瑪說。
“記住,以后不要聽男人們的壞話,尤其是扎西的爸爸、巴登尼瑪和索朗仁青說的話。”斯朗曲措說道。
“好的,再也不聽我爸爸說的那些怪話。”
扎西一說,三位女士又笑了起來。
她們拿著電筒把格桑多杰和扎西送到了門口,星星多了起來,月光下能看到隱隱約約的村間小路。
“快點回去,好好做家務,好好寫作業。”斯朗曲措說了一句。
格桑多杰和扎西回頭看時,卓瑪拉姆手里拿著手電筒站在中間,能看出她在不停地笑。兩位阿姨站在她的兩側,她們看著倆孩子背著梯子離開,咯咯笑個不停。平常在黑夜中最怕的是遇見鬼,但那天晚上扎西和格桑多杰都忘掉了鬼,擔心第二天他們的故事會成為村子里的熱門話題,想著想著他們跑回了各自的家。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了,卓瑪拉姆家母親去世,只剩下父親一個人。她家家境不好,他爸爸也沒有很好的名聲。她小的時候本來有很多人愿意上門做女婿,就算很多富有家庭的兒子也愿意上門,也聽說有干部也愿意娶她。但不知為什么,最后上她家門做女婿的是一位很普通不過的人,是她一個親戚介紹過來的。她的老公長相一般,不懂什么手藝,但命運就那樣安排了她的婚事。
格桑多杰結束了他的回憶,立身背上背包,他順著小路進了村子。他在一家新修的房子前面停了下來,看到院子里有一位阿姨在洗衣服。她背著一個三歲左右的小孩,旁邊還有一個十來歲的姑娘在看書。
“你們在忙嗎?這應該是誰的家?”格桑多杰問道。
“喇嘛拉保佑我,我以為你是一位外地來的游客,你還會說藏話。”
“肯定啊,我是這個村子里長大的,你是嫁到這里來的嗎?”
“怎么會呢?我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那位阿姨說道。
“那么讓我好好再想一想你是哪位。”格桑多杰摸了摸頭開始回憶。
“你不可能是格桑多杰吧?”
“正是,你是?”
“我老了,孩子都這么大了。”
格桑多吉看到旁邊十歲左右的姑娘時,突然想起兒時的卓瑪拉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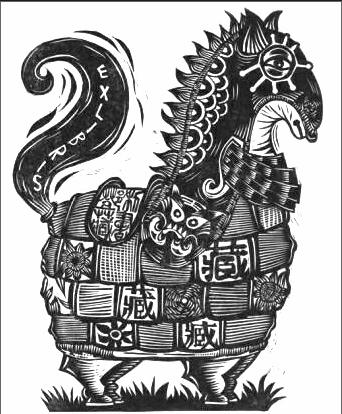
“我的天,卓瑪拉姆。你家以前不是在那邊嗎?村里變化太大了。”
“是的,變得連咱們互相都認不出來了。”
格桑多杰給了卓瑪拉姆的小孩一些糖果,想多說些話,但看到卓瑪拉姆使勁兒在洗衣服,他就向他們告別了。她眼睛周圍堆滿了皺紋,個子也沒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高,在她身上實在找不出當年卓瑪拉姆的一絲特點。他感到自己無法還原兒時的那些美好印象,只剩下零零碎碎的故事,甚至在這個山谷里才有的那種純樸的笑容也幾乎不見蹤影。聽說村里這些年變化很大,最大的變化是事情越來越多,忙碌中村民們被迫應接外部世界的迅速變化和沖擊。格桑多杰進入了村子,繼續帶著他的印象來探索眼前的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