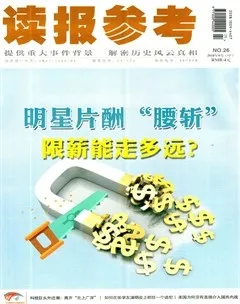“學校恐懼癥”在日本蔓延
袁野
在推特網上,日語標簽“不上學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話題。標簽的說明寫道:8月19日,一場“不登校”學生聚會將在日本100個地點舉行。活動發起人是24歲的小幡和輝,他希望此舉能讓社會對不愿上學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殺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寫道:“你不必到學校赴死。”
“我只在夜里一個人出門”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了2018年度《問題行為/拒絕上學研究報告》,這份報告顯示,該國每年缺課30天以上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達13.3萬人,占在籍學生總人數的1%。按一個班級30人計算,這意味著超過4300個班級空無一人。
近20年來,日本中小學就學人數持續下降,“不登校”情況以每年增加近1萬人的速度連年惡化,小學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過初中生(4.9%)一倍;13萬逃學者中,超過一半是長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個獨特的概念。根據文科省的定義,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每年缺勤達到30天,就被記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貧困或傷病等被動缺席,“不登校”是學生主動地長期逃學。
早在1941年,教育學家就提出了“學校恐懼癥”概念。1950年代早期,“拒絕上學”現象開始頻繁見諸報端。彼時“不登校”背后是“中產階級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問題”。
教育網站“東京家學”總結了7種類型的“不登校”:母子分離造成不安型、情緒混亂型(情緒低落,頭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對學習提不起興致)、人際關系型(恐懼校園霸凌而拒絕上學)、應激性精神障礙型、發育障礙伴有學習障礙型。過去,“不登校”只發生在小學和初中,現在高中和大學生也會“不登校”。
不上學的孩子們在干什么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頭于動漫和游戲。“那個時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覺。”30歲的山口真央回憶道:“我看電視劇,看深夜動畫,在網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里一個人出門,白天就在房間里呆著。”
相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穩。不少孩子淪為“隱蔽少年”,流落街頭、無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于嚴重的心理問題,最終走上了自殺的末路。
校園霸凌與“黑色校規”
面對這一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社會起初的反應并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學?打一頓就好了。那時,家長和老師都相信不上學是因為懶散或者不夠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壓力,結果適得其反。1990年代,幾乎每年開學季都有學生自殺的新聞傳出。
日本政府和社會開始痛定思痛。他們發現,很多孩子不愿上學并非是厭惡學習,而是受制于種種外部因素,其中校園霸凌首當其沖。文科省的報告顯示,近80%的“不登校”學生有遭遇校園霸凌的經歷。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處理不好與教職員工的關系;33%的孩子無法適應學校的社團活動;少部分人因為在讀期間懷孕而被學校勸退。
與校園霸凌不相上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太過嚴苛的校規。在日本,“黑色校規”已成為社會問題。一些學校禁止學生吃午餐時交頭接耳。廣島縣一所初中規定,午餐剩飯的人要被全校廣播點名批評。2016年,巖手縣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師欺負而自殺,而該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一些學校甚至對學生內衣的顏色進行規定,并且由教職員工監督檢查,結果導致了不少性騷擾案例。據“不登校新聞”網站報道,今年3月8日的一項調查顯示,1/6的日本初中對內衣顏色有要求,其中相當一部分學校會進行檢查;曾受到教職員工性騷擾的學生比例為1.9%,這意味著每兩個班級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師動手動腳。
試圖獲得父母更多關愛,也是孩子們“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壓力下,很多父母既無時間也無精力照顧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獲取關注。
還有些人純粹反感上學。“學校就如此重要嗎?”有人在“不登校新聞”上匿名寫道:“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我總是很痛苦……為什么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個奴隸一樣被困在學校里?”
討論“不登校”問題的同時,日本社會積極探討解決之策。教師家訪、單獨輔導等措施是“標配”。櫪木縣宇都宮市從2007年開始實施“缺勤一天就打電話,連續兩天就家訪”政策;名古屋市在網上公布了詳細的“不登校對策基本構想”,目標是在追蹤孩子心理狀態的同時,減少父母的焦慮并給予支持。
很多人呼吁社會給予更多的寬容。東京地方議員海津敦子在美國《赫芬頓郵報》日本版上發表《逃學不是問題行為》一文,她寫道:“我們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開開心心的嗎?誰都有沮喪的時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樣……讓他們返回學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們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路。”
在日本,“無法適應集體生活”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不登校”的孩子在升學和求職中都會遭遇重重歧視。
(摘自《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