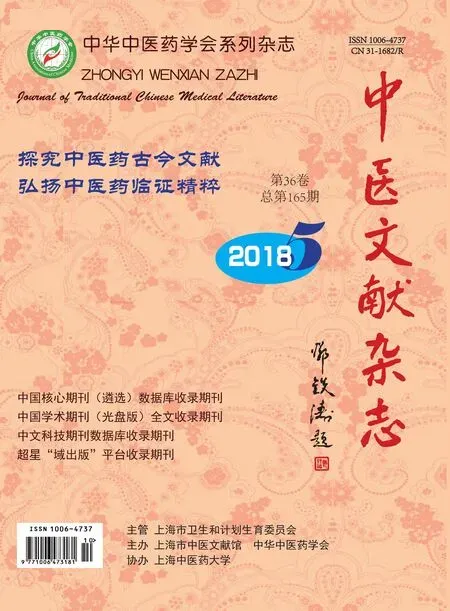肖曉亭《瘋門全書》與麻風病的因機論治
廣州中醫藥大學(廣州,510006)
陳天紅 吳培靈1 劉孝忠 劉 晟2△
麻風病是一種慢性傳染性疾患,自古以來長期影響國人的健康,斯疾為病尤甚,殘害尤烈,特別是其中的疣型,頑固不愈,可致嚴重的皮膚損壞和肢體殘廢[1]。歷代醫家針對本病的病因病機和防治曾有大量論述,但直到明代嘉靖時期之后,才有麻風病專書陸續出現,肖曉亭所撰《瘋門全書》便是其中重要一種[2]。肖曉亭,祖籍江西省分宜縣(今屬新余市),生卒年不詳,約生活于嘉慶、道光年間。曾為廩膳生,后以醫濟人,有記載其“醫人神效”,“于治癘一門,尤屬專家”。《瘋門全書》是其廣搜博采,悉心救治麻風患者數百余人,集其多年經驗,“彈心竭力,三易寒暑”而成,其于治癘,百不失一,匯集了其對惡癘(即麻風)病因、病機、辨證、防治等多方面的認識。
《瘋門全書》成書經過及版本流傳
《瘋門全書》寫于乾隆嘉慶年間瘟疫大流行后,成書于嘉慶元年。乾隆嘉慶年間瘟疫大流行,此次流行范圍極廣,狀況慘烈[3],如書中記敘:“村落中十里九里,處處咸有。”當時少有麻風病專書,缺少治驗良方,肖曉亭憐憫麻風患者的悲慘境遇,廣搜博采,尋求各種方法全力救治麻風患者數百余人,后為求治癘之法能傳于后世,集其多年經驗,“彈心竭力,三易寒暑”,分列綱目,簡潔而清晰地論述了麻風病的成因辨證及防治之法,于嘉慶元年(1796年)撰成《病疾輯要》、《病瘍備要》各一卷,但無力刊印,病故前托付于友人劉全石,然亦因種種原因未能成事。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始由袁春臺注而付梓,定其書名為《麻瘋全書》(見袁春臺按語)。道光二十三年、二十五年曾由敬業堂重刻刊行,光緒初亦有刻本。1936年裘吉生先生主編之《珍本醫書集成》將該書編入刊印。1959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曾校印出版。現所見版本為道光二十三年敬業堂刊本,現通行書名為《瘋門全書》[4]。
麻風病的病名及癥狀表現
麻風病,在醫史文獻記載中,或以病因命名,或以典型癥狀命名,常有“癘”或“厲”,“大風”或“惡疾大風”、“癩”或“風癩”、“天刑”、“癘瘍”等多種不同名稱[5]。關于書中麻風病的病名,雖然肖曉亭已了解其發病與空氣中一種“濁氣穢氣毒瓦斯”(即麻風桿菌)相關,但囿于時代局限,書中仍以“癘風”名之。“癘”言其惡疾,纏綿難愈,并會使患者有極大的身心痛苦;所謂的“風”,從蟲從風,一言與空氣中由風攜帶的毒氣有關,二言與不正之風有關。即如《素問·脈要精微論》篇所言的“風寒客于脈而不去,名曰癘風”[6]。
麻風病的癥狀多表現為麻木性皮膚損傷、神經粗大、毛發脫落、感覺障礙、運動障礙、畸形、深在性浸潤、腹股溝、腋窩等處淋巴結腫脹,涉及皮膚、骨骼、內臟等多種組織和器官損害。《瘋門全書》對于麻風患者癥狀的觀察極為準確。書中記載的“面紫發泡”,“遍身生瘡,上損眼目”,“眉毛先脫,重則鼻梁崩塌”,“四肢浮腫”等全身癥狀,以及“虎口肉珠必焦”和特征性癥狀,及“皮死麻木不仁”、“血死潰爛,膿水淋漓”等局部癥狀,均與現代醫學對麻風病的認識相吻合。
對麻風病病因病機的認識
麻風病的病因,《瘋門全書》中認為其與東南地勢低而近水有關,再加上氣候的異常,故而造成此病的流行,且認為其發病與五風生五蟲密切相關。肖曉亭在書中寫道:“嘉慶元年(1796年)孟夏,蓋東南地卑近水之處,此疾尤甚。天地較炎,地氣卑濕”,“濕熱相搏,乘人之虛,入于營衛……故此病血熱居多。又臥于濕地,受其熏蒸……皆能受病。初則血滯不行,漸生麻痹。”其觀點與《脈要精微》中“癘風者,營衛熱,其氣不清”的觀點無二。近年由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導的一項研究證實,瘟疫的爆發大部分是突如其來的嚴重氣候變化而引起,此研究結果與《瘋門全書》氣候變化引發瘟疫流行的觀點不謀而合。至于“五風生五蟲”的觀點,作者囿于當時有限的醫學知識,不可能從現代病原學的角度去認識麻風病。事實上西醫亦直到1873年才發現麻風病的病原體——麻風桿菌,證實了麻風是麻風桿菌導致的一種慢性傳染病。而在今天看來,肖曉亭提出空氣中由風攜帶的微小蟲體加上氣候異常導致麻風病流行的觀點不但不荒謬,且有一定的先進性。對于蟲與該病的關系,書中寫道“黃風生黃蟲,青風生青蟲……黑風生黑蟲”,“此五種蟲食人五臟……鼠食人肝,眉睫墮落,食人心,遍身生瘡……”,說明肖曉亭當時已經意識到有一種特殊的生命體的入侵,才使得人的五臟長期被消磨。但是肖曉亭并未認識到“無形”的蟲才是該病的傳染體,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有形的必須殺滅的寄生蟲,以諸如苦參、大黃等“利出瘀惡蟲物”入方中,作者以此等缺乏實證的理論來詮釋麻風病的病因,是該書的局限之處。
肖氏認為,麻風病的直接病機在于營衛不和。相較于其他時行疫證,麻風最典型的癥狀即是“肌膚麻痹”,至于此癥狀出現的原因,肖氏認為“衛氣不行則為麻木……營氣虛則不仁”,亦由“衛氣內伏,濕熱日久,血隨火化而致”。麻風病的根本病機為“陽明一經”氣血不和。陽明經多血多氣,氣血敗壞,則“食人五臟骨髓皮肉筋節”,如薛己所言,“瘡瘍所患,非止一臟,然其氣血,無有不傷”。麻風病雖是時行疫證,但肖曉亭傾向于從六經辨證認識此病。《瘋門全書》“麻瘋三十六種辨癥圖說”一節所列的“唇翻齒露,手足指脫”的大麻瘋,或是“手足麻木,身有死肉,皮肉常似蟲行”的暑濕瘋,或身有紅塊手拳足吊的拔發瘋,或發泡生瘡且多痹肉的血熱瘋等多種麻風證型,確與陽明病密切相關。如“脾主口主唇主四肢主肌肉”、“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196條)、“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190條)。結合對本病常見癥狀的綜合分析,可以將麻風病的病機歸納為營衛不和,氣血乖錯,惡血稽留不去,血隨火化而生此病。
針對麻風病的防治特點
1.治法多樣,涉及病程各個階段
作為一本麻風病防治專著,《瘋門全書》所載麻風病的治療方法極為豐富,大致可分為內治法與外治法。內治法載方126首,先是統治方,以古方為主,特別是上古方;其次分治,分五臟經絡的不同,酌加引經藥,以疏其流;當病情穩定時,投以緩治、補治,以治本氣不足的病人;如果受病既久,投緩劑不效,則以峻治;氣血凝滯,濕熱相搏,則以瀉治;如果遇到先患麻風而有并發癥者,或由于本病而引起麻風者,則兼治之;最后斷根時,重視麻風病人的善后,即“補其血氣壯其筋骨”,此為余治。外治法載方49首,涉及針法、灸法、燒法、蒸法、熏洗法、淋浴法、涂抹法、熨法等,甚至有專門去腐爛之肉的“瘰爛法”。全書共計列方175首,劑型包括丸劑、散劑、膏劑、丹劑、飲劑、油劑、飯劑、水劑、漿劑、酒劑、粉劑等,涉及預防、治療、調護等各個方面[7]。
2.緊抓病因病機,和營衛調氣血
關于本病的治療原則,肖氏緊抓外邪入侵的病因以及營衛不和、氣血不調的病機,提出“以涼血和血為主,驅風驅濕為佐,審元氣之虛實,按六經以分治,斯治厲之要道也”。治療上立足皮膚之疾為營衛之氣不仁不用,重視調和營衛,調治之余不忘使用五臟引經藥,解毒之中涼血和血,驅風除濕,融入血藥,散結化瘀。難得的是,肖曉亭并不拘于血熱涼血之說,更主張因機論治、方證相印,雖桂附亦可用之。如針對危重病癥,書中有錄“癘疾回陽起痿方”一首,專門針對麻風病人由于后期彌漫性浸潤,損害遍及全身出現的陽虛重癥,方中用了附子、肉桂以引火歸原、回陽救逆,以破故紙和枸杞溫養肝腎,在治疫病多用清熱解毒之法的明清時期,顯得極為可貴。
3.抓住典型癥狀,提出以針砭刺絡放血
與其他麻風病防治專著相比,《瘋門全書》的最大特色是緊緊抓住麻風病人肌膚不仁這一典型癥狀,標本兼顧,虛實并重。既能從外感病的角度認識麻風病,在治療中貫徹祛邪的原則,又能認識到麻風病內有“惡血”、“死血”的病因病機,提出“若惡血凝滯在肌表經絡者,宜刺宜汗”的治療法則。這與《長刺節論》“病大風,骨節重,須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的做法不謀而合。其做法或刺十指甲并臂腕以去肌表毒血,或針足指縫并腿腕以去下肢毒血。其將解決“痹”的問題,當作治療的要務,防其“有一二點痹肉未活,或痹肉活而皮色未撤消,以致復作”。
4.反對濫用毒藥、戧伐正氣
肖曉亭在記述麻風病治療方法時,提出不能過度使用攻毒之藥,“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而后治其瘡可也”。他認為,“丹溪止用醉仙散、再造散二方,但服輕粉,多生輕粉毒,恐一疾未愈,又添一疾。又有大黃皂刺牽牛之類,然惟實者可用,氣血虛者,反耗元氣”。肖氏提出,非病之極重、不得已而用之,主張用平和之藥亦可去病,而重藥以蛇蝎即可,不可過用毒藥,以致過于伐正而病情愈重。
5.提倡戒“食”,顧護脾胃
肖曉亭在對麻風病人的治療過程中極其重視日常飲食調護。他認為“發毒之物助毒,生冷之物凝血”,“凝滯之物固毒,煎炒之物助火”,故其立足病人體質及疾病特點,對于營衛不和、氣血乖錯的麻風病患者,囑其冷食煎炒“皆宜切戒二三年”,特別是“若自死禽獸之肉,終身宜戒”。對于治愈的病人,亦強調不能輕忽善后,要固本祛邪,培補脾胃。
6.重視疾病預防,提出防傳染措施
書中有載“瘋疾傳染,事故常有”,“患病疾者父子離散、夫妻睽違、親友避之、行道叱之”,明確指出麻風是一種具有強烈傳染性的疾病。是故肖曉亭針對麻風病的傳染性也提出了相應的預防措施:“但回避可也,不共用器,不同飲食,各房各床,盡力求治……調停處置,令衣食不缺,若夫妻離棄,切莫勸解”,又云“大小便不同器,人皆知之,外此病人吸煙,亦宜避之……病人之尿,不可淋煙草,淋則吃者必生瘋病,此則人所不知。”在作者生活的年代,這些方法的提出極具前瞻性,亦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是很難能可貴的。
綜上所述,肖曉亭所著《瘋門全書》為麻風病學專著,書中作者基于自己治愈多例麻風病的實踐經驗,述其對于麻風病因、機、論治及預防等多方面的認識。肖曉亭治療麻風病,辨證精微,用藥獨到,方法多樣,其所撰《瘋門全書》對清末麻風病的治療作出了卓越貢獻。雖然由于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加強了麻風病的社會性防治措施[8],麻風病例在上世紀末已經顯著減少,但這并不意味著麻風病得到了徹底的根治,報刊雜志仍時有麻風病例的報道[9- 11],《瘋門全書》所載的麻風病治療經驗在當今社會仍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