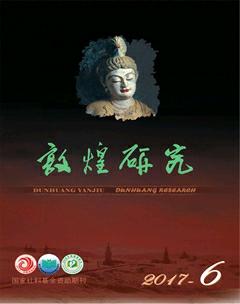敦煌“守護眾神”與絲路之魂
內容摘要:本文從段文杰先生在敦煌文化藝術保護、研究、弘揚上重視人才培養的杰出貢獻出發,以簡要的文字說明七十年來一批又一批富有犧牲精神的“莫高窟人”,堪稱“敦煌守護眾神”,有了他們,才能夠將“交流互鑒、交融創新”的絲路之魂演化成有強大生命力的、為當代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營養與物質財富。
關鍵詞:敦煌;“守護眾神”;段文杰;誕辰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7)06-0009-05
The Guardian Patrons of Dunhuang and
the Spirits of the Silk Roa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 Duan Wenjies Birth
CHAI Jianh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00073)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made by Mr. Duanwenjie to personnel training for the conservation,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Dunhuang culture and ar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several generations of“Mogao patrons”who have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Dunhuang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who deserve to be regarded as the guardian saints of Dunhuang. It is because of them that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represented by“communication, mutual learning, assimilation, and innovation”has been developed into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enjoy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even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Keywords: Dunhuang; guardian patrons; Duan Wenjie; birth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自1982年夏天第一次觀瞻莫高窟始,35年間,我有幸與敦煌研究院結緣,有幸結識院里的眾多專家學者,也有幸得到歷任院長的殷切指教。眾所周知,敦煌文物研究所老所長(或稱研究院老院長)常書鴻先生被譽為“敦煌守護神”;第二任所長(建院后第一任院長)段文杰先生,我曾在文章中稱之為“敦煌圣徒”、敦煌研究“杰出的領軍人”;第二任院長樊錦詩女士被稱為“敦煌的女兒”;而第三任院長王旭東先生,履新之初,則已經帶領院領導集體在繼往開來的道路上,為進一步擴大敦煌文化、學術的國際影響邁出了扎扎實實的步伐。
段文杰先生從1946年9月到莫高窟進敦煌藝術研究所至2007年出版《敦煌石窟藝術研究》論文集,堅守敦煌研究六十余年,期間擔任所長、院長十六年。他在洞窟保護、壁畫臨摹、藝術研究、文化普及方面的杰出貢獻,學界公認,杜琪、趙聲良研究員在《隴上學人文存·段文杰卷·編選前言》(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趙聲良還在《莫高窟的守望者》一書(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有精要敘述,我也曾在《論段文杰》《敦煌圣徒,時代功臣》及段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三篇文章中作了評述(請參考拙著《敦煌學人與書叢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茲不再贅敘。為紀念段文杰先生百年誕辰,我擬就這篇短文,僅就他重視人才培養、領軍學術研究方面再做一些補充,并由此述及對“敦煌守護眾神”與“絲路之魂”的粗淺認識。
段文杰先生重視培養人才,不僅做到了不拘一格,而且是全方位地積極施行落實。據我所知,80年代初,為填補敦煌文物研究所內文獻研究人才的匱乏,段文杰所長力主將在“反右”等政治運動中蒙冤受屈的李正宇、譚蟬雪、汪泛舟等征聘入院,并為這幾位有真才實學的老大學生提供各種條件,引導他們結合洞窟圖像資料開展文獻研究,不但使得研究院的敦煌文獻研究工作風生水起,成果迭出,而這幾位沉寂多年的中年研究者也煥發了青春,迅速成為國際敦煌研究領域中有影響的學者。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從全國征聘的人員還有鄭念祖、梁尉英、楊漢章、趙崇敏、張德明、譚真、林家平、黃家全、樸寬哲等,都各有所長,為敦煌研究作出了貢獻。1983年夏,重慶師院歷史系羅華慶、四川大學歷史系寧強大學畢業后主動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段先生抓住典型,予以鼓勵,進行宣傳,擴大影響;第二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生趙聲良、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生王惠民、陜西師大歷史系畢業生楊森也進所工作。80年代中后期進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以及招聘或調入的專業人員還有李崇峰、邰惠莉、莊壯、李聚寶、謝成水、胡同慶、高山、楊雄等人。此外,研究院堅持選拔一些優秀員工送到國內外高校學習、深造,如劉永增、段修業、趙秀榮、盧秀文、杜永衛、吳榮鑒、馬強等,為敦煌研究院工作開創新局面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礎(這項培養要才的工作至今仍在持續)。更可喜的,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院內工作多年(包括60年代初進所工作)的許多老專家,如史葦湘、李其瓊、關友惠、孫儒僩、孫紀元、孫修身、賀世哲、施萍婷等亦迎來了他們的“學術之春”,分別在壁畫臨摹、彩塑復制、石窟保護、學術研究中擔當了重任。自那時至今的二三十年間,李最雄、王旭東、張元林、張先堂、婁婕、楊富學、楊秀清、沙武田、侯黎明、王志鵬、陳菊霞、張小剛等一批中青年研究人才紛紛先后進入敦煌研究院,以段文杰為院長的領導班子則特別注意為他們的迅速成長創造各種條件,尤其是讓他們陸續讀研及出國進修培養,到一些文物遺址進行學術考察和承擔文物保護項目,鼓勵他們撰寫論文參加國內外各種學術研討會,為他們出版學術論著提供必要資助,其顯著成效令國內學界欽羨。endprint
上世紀70年代末,史學界曾盛傳有人在國內高校講堂上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引發我國敦煌學研究人員都鉚足勁頭,要改變落后狀況。1980年剛擔任第一副所長不久的段文杰先生,為了提升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水平,期望研究所能夠成為我國敦煌研究的一個中心,不僅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擠時間帶頭撰寫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的論文,而且組織所內同仁紛紛動筆寫文章。從1978年到1982年段先生擔任所長前的四年間,他已經在《文物》《蘭州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了《敦煌早期壁畫的民族傳統和外來影響》《形象的歷史——談敦煌壁畫的歷史價值》等15篇文章,可見他的寫作之勤與成果之豐,為激勵和帶領研究院同仁開展敦煌學研究作出了榜樣。
1982年,他主編的編集所內研究人員13篇論文的《敦煌研究文集》正式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段先生的“前言”撰寫于1980年8月1日)。12位作者中,既有長期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專家,也有迅速成長的中年研究人員。他又耗費大量心血籌辦并于1983年舉辦了全國第一次敦煌學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大會。作為與會代表,我親身感受到,這次全國性的會議,規模大,規格高,不僅會上的學術交流氣氛空前熱烈,而且會后還出版了高質量的多分冊的分類論文集,對團結與協調敦煌學所涉多學科學者專家的研究,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在我國敦煌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1983年學術會的前奏,是1982年夏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發起并組織在蘭州舉辦的全國性的敦煌文學座談會。會議也得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支持。會后,因交通不便,我們部分代表分散到莫高窟參觀。段先生不僅不憚煩勞地多次親自為大家講解洞窟藝術,而且仔細了解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具體論題,為第二年全國學術會議邀請文獻研究方面的代表摸清情況;第二年全國敦煌學學術會結束后,他又特別邀請與會學者參觀莫高窟,并開始著手實施聘請兼職研究人員的計劃。到1985年初,敦煌研究院聘請的兼職研究人員已達13人:姜伯勤、項楚、張鴻勛、高國藩、柴劍虹、馬世長、肖默、鄭汝中、黃瑞云、何鄂、郎紹君、黃文昆、耿昇,涉及文獻學、語言文學、石窟考古、古建、藝術、民俗等多個專業方向。其中馬世長、肖默、何鄂曾在研究所工作,鄭汝中后來與其夫人臺建群一起正式調入研究院。
這一借助院外研究力量、團結協作促研究的方針,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出于同樣的思路,為提供更好的面向全國與世界的學術平臺,段文杰先生自1980年任第一副所長伊始,就著手創造條件籌辦《敦煌研究》學術期刊。經過1981、1982年兩期試刊,1983年正式創刊,段院長親任主編,確定了“立足敦煌,面向世界”的辦刊宗旨。1984年志愿來研究所的趙聲良即被分配到該刊編輯室工作。后來,經段先生提議并和我洽商,聲良又于1988年下半年到我負責的中華書局《文史知識》編輯部進修了半年,以積累辦刊經驗。現在,《敦煌研究》已經成為國際敦煌學界公認的首屈一指的優秀學術期刊,成為培育敦煌學研究人才的重要園地。據我所知,現在敦煌學界許多專家學者的第一篇敦煌學論文,都是在《敦煌研究》刊發的。編輯部的團隊建設,自然離不開段、樊院長的正確指導,離不開梁尉英、趙聲良領導的編輯部同仁的辛勤工作。此中詳細情況,我和聲良均曾撰文敘及。
1988年,段院長的《敦煌石窟藝術論集》正式出版(甘肅人民出版社),該學術專著收入他的論文14篇,主要從美術發展史的角度,論述莫高窟各個時期洞窟藝術的內容與風格特征,也有他多年臨摹敦煌壁畫的體會。在該書“自序”的結尾,段先生寫道:“今后數年內,我將利用我三十多年臨摹工作所獲得的感性知識,在敦煌藝術創作方法、表現技法和佛教藝術美學等方面進行探討,為青年美術工作者學習敦煌藝術遺產、推陳出新作一些鋪路的工作。”“鋪路”之言,吐露心聲,令人感佩,他在進入古稀之年時,念念不忘的仍是對后輩學者成長的殷切期盼。
重視人才培養,一直是段文杰先生關注的工作重心,是敦煌石窟保護和研究事業得以發展、壯大、鞏固的根本保障。根據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所四十年》一文中所提供的資料,從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到文革前的1965年,先后到所里工作的人員有(個別人名略有修正,括號內人名則為我根據其他資料所補):
1944年——常書鴻、史巖、李浴、蘇瑩輝、董希文、張琳英、邵芳、張明權、周紹淼、烏密鳳、潘絜茲、陳芝秀、趙冠洲、龔祥禮、勝其力、羅寄梅等。(辛普德、范華、竇占彪。)
1946年——段文杰、霍熙亮、郭世清、凌春德、范文藻、鐘貽秋、劉漫云、張定南等。(周星祥。)
1947年——孫儒僩、黃文馥、歐陽琳、薛德嘉、李承仙、肖克儉等。
1948年——史葦湘
1952年——王去非、李其瓊。(李復、畢可。)
1953年——孫紀元、關友惠、馮仲年、楊同樂。
1954年——李貞伯、萬庚育。
(1956年——李云鶴、何靜珍等。)
1959年——劉玉權、何鄂、潘玉閃。
1962年——賀世哲、施萍婷、李永寧、劉忠貴、孫修身。(高爾泰。)
1963年——樊錦詩、馬世長。(肖默,從新疆調入。)
1964年——李振甫、何山。
1965年——樊興剛。
這六十余位主要是涉及藝術與歷史、考古方面的美術家、研究者,對于從事石窟保護、藝術創作與研究各方面工作的人員來看,肯定還是不完整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多年之后,段文杰先生之所以還要在文章中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正說明他內心蘊涵著濃烈的人文關懷精神,他重視人才的培養、引進、使用,就是抓住了保護敦煌、研究敦煌學、普及與弘揚敦煌文化的關鍵與核心——人。
其實,段文杰先生在關切研究院每一位“個人”的同時,還特別強調建設“團隊”的重要性。根據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這里要特別提及段文杰先生曾十分關注的研究院的三個“團隊”:科研處、接待部、敦煌學信息中心。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院學術委員會,由段院長的學術秘書李永寧擔任秘書長,負責全院的學術與科研的組織、協調工作,2005年改稱科研管理處(兼學委會秘書處)。1994年,張先堂從甘肅省社科院調入敦煌研究院,自1998年起調任學委會副秘書長,多年來與李國等多位處里同仁一起兢兢業業工作,承擔了舉辦各種研討會、論壇以及聯系、接待國內外學者的重任,為研究院的學術發展做出了不凡成績。多年來,隨著學者考察、師生臨摹,特別是旅游熱的興旺繁榮,院接待部不斷發展壯大。李萍主任自1981年春天進入研究所工作就在接待部,36年來她不但親歷了接待部的發展歷程,而且認真執行段、樊二位院長制定的方針,下功夫花氣力爭取通過各種途徑培養原先不同文化層次的講解員,從接待部到游客展示中心,到在國內外舉辦的多場敦煌藝術展覽,打造出了一支全國文博系統中人數眾多、講解語種最多、水平最高的接待隊伍(目前展示中心150人,接待部約160人),為普及與弘揚敦煌文化藝術打開了異彩紛呈的窗口,也成為連接敦煌與國內外廣大參觀者的一座寬廣的橋梁。和李萍同年進入接待部做英語講解的楊薇,則在段院長的鼓勵與支持下考入高校學習美術史,后在美國西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在已經成為美國頗有影響力的亞洲藝術與佛教藝術的高級評估師。她回憶和張艷梅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時,段院長每次來北京,都要抽時間看望她們,關心她們的學習與生活。最近她回國時和郝春文會長及我見面時說,她和許多接待部講解員都一直感恩段院長對他們的栽培與引導,希望我們能替她轉達感謝的心聲。院資料中心成立于1984年,是在此前的資料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老專家史葦湘先生一直負責資料室及后來資料中心的工作,可以說為資料建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擴建為研究院以后,段院長對組建資料中心有個“三步曲”值得一提:開始,根據國內外相關圖書、資料室的情況,從研究院經費短缺的實際出發,他指示院資料室要以院里免費得到的交換、獲贈圖書為基礎,以突出國內外藝術類資料為特色;然后,根據全院科研需要,加速擴展資料入藏范圍與規模,逐漸發展,形成了今天的敦煌學信息中心;他退休時,又囑托將自己收藏使用的全部圖書資料2784冊悉數捐獻給信息中心。張元林研究員1989年進院,曾擔任段院長學術秘書,2002年起負責資料中心的工作,十多年間,他和同仁一道苦心孤詣謀求中心健康發展,為提升研究院的學術研究水平做出了貢獻。endprint
誠然,為敦煌研究院做出各種貢獻的還有保護所、文獻所、考古所、美術所、陳列中心、攝錄部、人事處、保衛處、院辦和黨辦等團隊,組成這些團隊的每個勤勤懇懇的“莫高窟人”同樣都值得我們尊敬。
我之所以要從段院長講到眾人,從個人述及團隊,是希望說明:從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來,一批接一批奮斗在鳴沙山崖、宕泉河畔的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一批又一批“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施萍婷老師語),還有即便因各種原因離開了敦煌卻始終對莫高窟魂牽夢繞之人,他們堪稱“敦煌守護眾神”,護衛著“絲路之魂”,凝聚為“莫高之魄”。幾位院長則是他們的杰出代表。其中段文杰先生雖然在“反右”、“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歷經種種磨難,但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不計個人得失,善于團結廣大學者同心同德把學術研究搞上去。在他的領導下,敦煌研究院的保護研究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同時也建立起了一支為國際敦煌學界矚目、特別過得硬的學術團隊。
2015年初,我曾在浙江大學和新疆文物局聯合舉辦的“絲綢之路文化論壇·新疆”上發言提出:對“絲路文物”的研究離不開對“絲路人物”的新認識。文物的主體還是創造了這些“物”的“人”,這就關系到對體現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核心”的人的理解與分析。后來,我又在《睹物思人——簡論絲路人物》一文中強調:“文物作為歷史文化的物質遺存,是重要的文化載體。人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傳播、傳承、發展的本體與核心。”“物質文明印記著人類前進的足跡,蘊涵著豐富的人文精神,也必須靠人去升華、結晶為精神文明。精彩絕倫、內涵豐富的絲路文化,要靠一代代無私奉獻的絲路人物去傳承弘揚、發展繁榮。”(參見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編《絲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一書,即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第20—30頁。)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莫高窟人”,就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最富有犧牲精神的絲路人物。
前面提及“絲路之魂”。去冬今春,在羅華慶副院長精心策劃下,由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資助,敦煌研究院與成都博物館舉辦了“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并輔以若干講座,觀眾、聽眾踴躍,盛況空前。我在演講中將“絲路之魂”歸納為八個字:“交流互鑒,交融創新”(此歸納后來獲得樊錦詩名譽院長的贊同)。我認為,正是文化的交流互鑒促進了多元文化藝術的形成與發展,也正是文化藝術的傳承創新使得世界文明能夠延續、昌盛,而文明的創造、維護、傳承、研究、弘揚者是“人”,沒有“人”,就失去了“魂”,散落了“魄”,也無所謂“神”。七十多年來,從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到王旭東,到今天仍堅持保護、研究、弘揚敦煌文化的一大批“莫高窟人”,就是守護“絲路之魂”的“眾神”。有了他們,才能將“絲路之魂”演化成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為當代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營養與物質財富。而段文杰先生,則是“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上下而求索”、“導夫先路”(屈原《離騷》中語)的一位杰出的領軍人。
習近平主席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見新華網所載2016年5月18日新華社電文)創造、守護、傳承文明,延續血脈、弘揚精神、創新發展,其核心和關鍵即在于人,需要一批又一批像“莫高窟人”這樣勇于繼往開來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我想,這也正是今天舉辦這個以紀念段文杰先生百歲誕辰為主題的學術論壇的意義所在。
本文撰寫得到敦煌研究院趙聲良、張先堂兩位副院長在資料、文字上的補充與指正,謹致誠摯的謝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