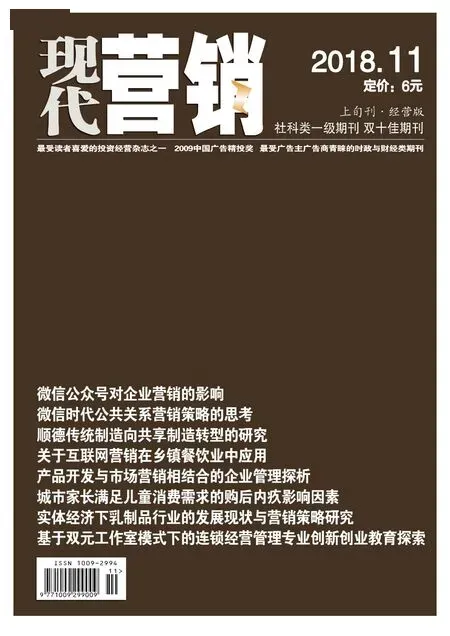香港產業結構變遷對內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啟發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100871)
一、香港經濟發展60年來的五個重要階段
根據香港經濟發展的周期性,可將其發展過程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轉口型貿易”經濟轉向以輕工業為主的加工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發展迅猛。制造業、消費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現代服務業的增加值比例為:24:22:10:15,其中,制造業規模最大。
第二階段是1967-1975年左右,由于引進國外先進設備,香港制造業的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原來單純的“外貿加工”轉向“自主制造”。前述四大行業的增加值結構為:27:21:7:17。
第三階段是1976-1985年,前五年增長速度超過11%,后5年增速有所下降,達5%左右。前述四大行業增加值結構為:22:23:8:16。
第四階段為1986-1998年金融危機時,前五年增長速度超7%,后8年增長速度不到4%。數據顯示,1994年時,港人均GDP達2萬美元,令香港邁入國際發達城市行列。前述四個行業增加值比重為:6:25:9:25。
第五階段也即1997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到2018年,得益于緊鄰內地的優勢以及WTO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上含紐約、倫敦在內的三大最重要的金融服務貿易中心之一。2000年前述行業增加值比重為6:26:10:24。
2001年受美國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以及境內外地緣沖突不斷的影響,香港經濟增長受到打擊,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負增長,近10年來增長維持在2%—3%的水平。
二、香港產業結構變遷的邏輯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60多年前,依托獨特區位優勢以及 “自由港”政策,香港航運業崛起,成為世界各國與亞洲經濟聯系的貿易往來窗口。不過,只是承擔轉口運輸功能的結構也暴露出香港經濟基礎較差,抗風險能力不強。
第一階段,美蘇爭霸導致世界格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利用內地廉價的生產要素和自身積累的航運優勢,港加工業迅速發展提升了制造業競爭優勢。
第二階段,戰后德國、日本和臺灣的制造業也紛紛崛起,香港面臨的國際競爭對手增加,加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令到低附加值制造業難以為繼。
第三階段,香港順勢將傳統加工業轉移到珠三角,利用當地成本優勢以及香港崛起為亞洲第一大航運港的服務優勢,香港發展起了國際運輸服務貿易業的跨區域合作優勢。
第四階段,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世界競爭格局進入以創新科技為角力場的時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加快了全球經濟“休戚與共”的進程。而香港對此未做長期布局,其除了金融貿易及中介服務業以外就是零售消費行業,制造業空心化現象嚴重,大型科企的缺失顯露出城市技術創新能力的貧乏。
三、香港產業“逆變遷”對內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啟發
筆者認為,究其原因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香港沒有捕捉到世界發達區域產業調整的信號,一味沉浸在原有產業優勢的良好感覺中,在美、德、日紛紛借助新興科技助力本國制造業、打造國際品牌之際,香港卻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 “逆變遷”。
產業“逆變遷”,是指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不能及時跟上產業轉移的方向,錯失將先進技術引入到產業變革中,在原有優勢產業即將退出歷史舞臺之際,無新的代表未來方向的產業接續上,從而導致GDP增速下滑、區域競爭力不進反退的現象。
香港產業出現“逆變遷”,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洞察并跟進各國產業發展向“制造業回歸”的新的趨勢。
香港當前單一的產業結構損害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的地位,造成其在科技領域競爭力乏善可陳、人才流失嚴重、地價畸高的局面。幸運的是,香港政府已意識到該問題。當下,香港正借助各種力量改善產業結構。
首先,產業變遷有自身規律。技術的發展帶來生產力的變化,產業轉移先是從一產轉向二產,然后再轉向三產。經濟學認為,一個地區第三產業占到GDP 70%以上就進入了發達經濟階段。然而,這一規律并不完全正確,它只看到了經濟體進入發達階段后的結果,而忽略了產業鏈分工中,一產和二產的作用,如果沒有高度發達的一產、二產作支撐、單純為提高第三產業占比的發展是基礎不牢的,最終會出現 “制造業空心化”。
第二,在產業梯度轉移中,發達地區務必要清醒認知“制造業≠低端產業”,制造業產業鏈的完整與否恰是一個地區競爭力的體現。國內珠三角、長三角某些發達城市曾一度提出“騰籠換鳥”計劃。但除深圳之外,多數地區經濟發展出現增速放緩局面。
第三,需要關注的是,近兩年來,我國工業增速回落,尤其是工業投資增速回落,從對外投資和對內投資的對比來看,制造業空心化風險加大。最新數據顯示,內地制造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是負增長6.1%。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中制造業直接投資超過2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100%,顯示大家不愿意在國內投資制造業了,而是走向了國外,這或進一步加劇國內制造業空心化。
最后,需要警醒的是,我國中西部地區總體發展水平仍欠發達,內陸勞動力資源豐富,用地成本較低,發展制造業一方面可解決當地就業,另方面能促進當地稅收、帶動當地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