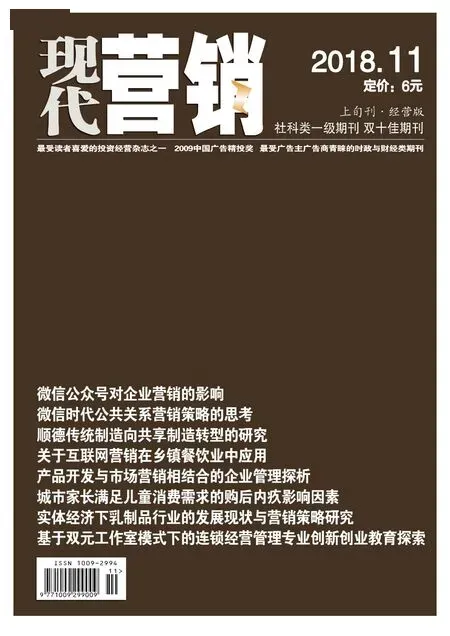移民的文化屬性與經濟的穩步發展
——云南大理銀橋鎮個案探究
(蘭州文理學院藝術學院)
一、移民的移居背景及動機使得大理的村鎮成了不二之選。
把移居大理的人群稱之為“新移民”,這個詞匯,最初我聽到時心里倍感洋氣。從2015年起,我有了移居國外的念頭,去了國外,該被稱為“移民”吧。辭海對移民的解釋有:1.遷往國外某一地區永久定居的人;2.較大數量、有組織的人口遷移。我想之所以稱移居大理的人群為新移民是因為這兩者的意義都不太匹配,所以,稱之“新移民”。
匆忙中,我加入了新移民的隊伍。
我的所圖很簡單,好的空氣好的水,不去工作孩子自己教育自己陪伴,遠離電子產品降低物質依賴。
我一直的工作是在大學教育別人家的孩子,在2018年的的4、5、6、7月份我平均每周在兩個城市飛四趟,一般是凌晨到一個城市,然后7點去上課,下午5點下課后趕去機場,凌晨到家。我的奔波目的只有一個,親力親為的自己面對孩子的生活和學習。在有課的階段我的月收入6000-7000元左右,月開支10,000元以上。我的身體在工作期的第三個月時會進入低谷,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開始生病,我一直以為自己很彪悍可以扛得住這樣的生活狀態。當我的情緒開始比較煩躁,易怒易悲,怨懟之情常常讓家里的長輩不知所措時,他們開始放棄式的妥協,常常在思考是在我工作忙時幫助我一起撫養孩子,還是索性不要再看我的臉色老兩口安享晚年悠閑的生活。
其實,這樣的生活,我已經過了6年……
之前我很樂于把孩子托付給父母教養,當他一天天長大,每一次我離開他去上課都讓他難過不已,開始學會將小腦袋藏在我懷的悄悄的哭時,我發誓,不要再離開他一步了。管理愛護好我的孩子是我不可以推卸的責任!這種念頭越迫切,就越壓抑。
有一天我發現我花的比掙的多,我知道我有了可以自由選擇生活軌跡的物質基礎,我開始竊喜,也開始思考,下一步我該怎么走?
發現大理的移民村太偶然了。我在2018年7月底陪同兒子參加夏令營,作為義工我被大齡的孩子惡作劇摔傷了。本來計劃8.1的內蒙古之行泡湯后,跑到移居大理的彩藍家做披薩,又巧合地認識了在家教育孩子的三寶媽。
OK,大理銀橋鎮上銀村這個地方讓我被深深的吸引。8.23我落戶銀橋鎮,正式成為新村民的一員。
銀橋鎮位于大理市中心地帶,距里市中心(下關)20.5千米,距離大理古城9公里。面朝洱海,背靠蒼山,南連大理,北接灣橋鎮。它有8個村委會,32個自然村(我住在鶴陽村),總戶數6824戶,總人口30154人。我所居住的鶴陽村是“娃哈哈”水廠的供水基地。214國道及大麗公路橫穿南北,鎮村公路也是修繕完整,我家門口小車可以直接開到。銀橋鎮現在的新移民有100多戶,在我的“銀橋新移民”微信群有280多個好友。大家多是集中在上中下銀這三個村子。這些新移民中有80%是為了孩子脫離體制在家教育而搬來的,在和10戶左右家庭聊天后,我的最大疑惑被釋放了。我問:“呆在村子里著急嗎?想離開嗎?“(家庭居住地背景:3戶廣州、1戶深圳、1戶北京、2戶成都、1戶上海、1戶鄭州、1戶杭州)。他們最久的是Rocky范一家居近4年,他們來自廣州。還有很多新村民于2010年始就已嘗試非旅游的短居大理。大家的答案超乎的一致:“不著急哈,我們現在是不愿離開,我們已經不再適應不再喜歡城市的生活,太吵了。”
大家移民關鍵詞是“子孫”,為孩兒而移!據資料顯示中國的在家教育發源地、聚集地是大理。所以,我聽完后立馬就有了匍匐在地膜拜,抑或可以與他們相擁而哭的念頭。這正是我想為自己和孩子甚至是父母尋求的生活生長環境!
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租院子唄。通過走訪和村子里有名的王婆(村子里的人肉“58同城”)對接上后,我了解到大理銀橋鎮的院子一般租約都是以10年為基礎,封頂20年。老院子基本在2萬以內1年,新院子基本上1層樓2萬元1年。我急于落戶,用了前后不到15天的時間匆匆簽下了1戶深圳人改建的老院子,為期一年共計1.8萬。在這一年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戶1年1萬租金以內的老院子,然后簽一個上限年限(20年)投資改建(至少30萬)。應了文章開頭提到的,大理的村鎮山好水好空氣好,新鮮的蔬菜和水果,還可以自己養點小家禽小家寵什么的,我就此養老吧。
二、移民落戶,文化背景的差異如何融合,又如何形成了移民的文化屬性?
“文化”的定義在百度百科里這樣解釋“它(廣泛的知識并將之活學活用與根植內心的修養culture)是非常廣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簡單來說文化就是地區人類的生活要素形態的統稱:即衣、冠、文、物、食、住、行等。給文化下一個準確或精確的定義,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文化這個概念的解讀,人類也一直眾說不一。但東西方的辭書或百科中卻有一個較為共同的解釋和理解:文化是相對于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產品。”
是的,我要落戶,前提的問題“如何和當地的人文化習俗習慣能夠融合并建立一定程度和范圍的群體關系”。三寶媽告訴我:“基本上新移民是和新移民圈子里的人接觸的,這里的白族人是很好的,人也樸實,對我們很好,但是基本不發生什么聯系”。好吧,不建立人物關系,還要對方對自己好?!朋友阿龍,湖南人,今年34歲,從2009年起移居大理開客棧到今年是第8年。阿龍操著一口流利的大理話。為啥?被騙怕了唄。最初建院子蓋樓,當地人說當地話買釘子只要一元錢一只,他買少于2.5元不賣。要去講道理嗎,當地人沒人理會的。所以,阿龍是建立關系的,他學會了當地的方言。
和全國大部分的農村很相像,這里的村子有著獨一無二的適合生活的優質的自然資源。銀橋鎮90%以上是白族,村間小道經常看到穿著民間服飾的阿孃,經典的搭配就是淺藍色上衣配黑坎肩,統一扎有一條淺藍色小圍裙,頭發基本全是盤起來的,經常有一只竹編背簍在身,步履蹣跚緩慢,若是重物必還有一條編織的很好的或麻或棉的頭帶分擔重量,這里的老人家是還需要干很多活的。當然還會碰到很多長襟大褂的青年人,有著意味深長的笑意和禪意的滿足,說著普通話抑或英文,基本可以判斷是新移民了。村子歷經10年的移民遷徙,但還是有著很突兀的文化差異,
還是回到之前的提問,若不是新移民和當地村民有文化的銜接和關系的建立,是利用還是扶貧?若要有文化的銜接和關系的建立,有成功的案例嗎?還是說目前還在探索。因為移民比搞鄉村建設更接近對方生活的實在,畢竟地理環境和歷史是產生的人文精神的土壤。若是有著深入骨髓的文化接納和生長,年輕的村民才會在意對傳統的文化的繼承和保護,新移民也不會在租來的老宅子里肆意改造豪無顧慮。可我作為新村民的一員,我和我的新村民們的遷徙動機,不是被當地的風土人情,人文景觀所吸引,我們建造的房屋,看似對老房子的修繕及保護,卻在內部結構和使用功能做了顛覆性的改造。農家的正屋、豬棚和貯藏室及院子我們用現代的設計理念獨特的設計手法及光影的使用表現出的是我們心中的烏托邦。也許只有在正屋的造型結構、材料使用及紋樣能感受到歷史和民俗的痕跡。但說到原汁原味的民族村落的再現,恐怕是新老村民都不想要的。我們的改造的老屋本該將本地自然、文化特色融入,進而生成留有原地氣韻的宅子,代代相傳。現在的老屋景象,卻在今天你蓋兩層,明天我蓋三層,蓋出有權有勢,有姿有色是最好的(社會價值觀的普遍性導向)。
城里孩子的烏托邦,村里孩子的大戶夢。雙方都拿對方當“傻子”!
教育的落后,在毫無意識和局限的認知中,村子里的大部分有效勞動力出門掙錢,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肩負著守護家園的人物。“他們”的村子人去樓空,“他們”去城市努力成為“北漂”、“上漂”、“深漂”的一員。而“北上廣”這樣的超一線或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石家莊、成都、西安等城市)惡劣的生存環境、惡劣的競爭壓力讓大批盛年的高學歷中產階級攜家定居在空落落的村子,試問,這種行為算不算精準扶貧?還是移民赤裸裸地對有限資源占用和利用?
這讓我想起了“溫州模式”,在上世紀浙江省南部很是炙熱,也成為中國經濟奇跡的縮影:貧困的村莊,卻成為中國最有能量的加工制造中心。這個省份也成了中國最富裕的省份。貧是暫時扶了,但村民的心更餓了。若沒有文化的共融和生長,建造有多少,破壞就有多少。
三、“臨界空間”決定了移民的文化屬性,更體現了移民的實際存在。
之前有閱讀到大理大學社會學博士高瑜在2017年發表“臨界空間的轉變——云南大理古城的個案研究”一文,在文中提到的“新住民”、“臨界空間”等信息點。
蘇格蘭人類學家victor turner(維克多·特納,1920-1983)曾提到臨界存在(liminality),即指“在此處又不在此處,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意指文化在和因商業發展而被迫產生交會的過渡地帶,臨界性形成,滲透并且定義新的都市空間。美國學者Sharon.zukin(雪倫.朱津)這就稱之為臨界空間,這類空間介于文化領域和商業領域之間,公共價值和個人利益之間。并且指出這不是一個過渡階段的狀態,而是一個進一步的狀態,在當代都市社會中它包含了經驗感受的不同層次。并且因為這樣的空間存在,使空間運作變得復雜,但它連接了轉換的地景和地帶。當大理古城發生了臨界空間的改變,“從大理古城洋人街的興起,到人民路的崛起,以至于到古城鄰近的客棧、小區的開發,以及雙廊古鎮漁村的精品酒店等。這些地景的變貌,一則讓人看到空間過程的變化,另則也突顯出不同人群進入的軌跡。不論是本地人的投身參與異國料理,或是外來藝術家帶來的波希米亞風,抑或是都會中產階級所引入的資本,這些都說明了文化的異質性創造與市場化的作用力,如何交會在一個西南邊陲小鎮里。“當然,這些都是來自于外部的沖擊,而本土的文化的融入顯得極其被動,是沒錢沒見識沒膽略鬧的嗎?
寫到這里卻有了一絲淡淡的哀傷。我熱愛這片土地,我更想了解這片土地的人。我要移民,不是在這里去居住在另外一個北京、上海、成都……沒有人文特質的土地只會被掠奪。所以,在國家提到精準扶貧更多的不該是受之魚而改授之漁。了解和熱愛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才是扶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