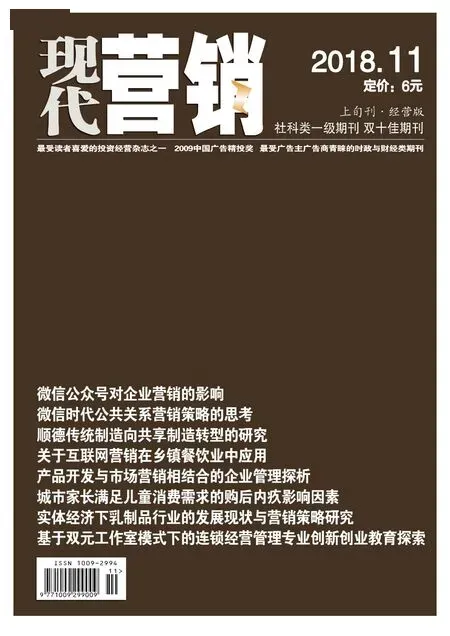漢代圍繞錢幣鑄造權的學術辯論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 廣東廣州 510006)
錢幣鑄造權究竟歸中央政府,還是歸民間私人企業主?這是一個藏富于國還是藏富于民的問題。西漢昭帝期間,曾經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一場政治學術辯論。辯論的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漢朝官員,另一方是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民間學者。
這次政治學術辯論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漢初文帝時期,國家為了促進生產,曾經放任民間鑄錢。這一方面為漢家經濟恢復創造了寬松的經濟條件,另一方面也為藩國諸侯創造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并為奸詐不法之徒提供了聚集的條件。漢武帝時期,朝廷施行內興功利、外伐四夷的政策,急需大量錢財,在國庫告罄的情況下,朝廷決定將鑄錢權收歸國家,這有效地緩解了漢家的經濟困境,有力地支持了漢家外伐四夷政策的實施。但是,在新幣發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病。桑弘羊站在朝廷立場之上,堅持由國家統一鑄造錢幣,認為這是強干弱枝、平息奸偽、均衡貧富的必要手段。文學則認為,應該允許民間鑄錢,保持貨幣多樣化,反對朝廷與民爭利。
這場政治學術辯論聚焦在三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社會貧富懸殊的癥結在哪里?御史大夫桑弘羊認為,貧富懸殊,這是由于民間少數人壟斷財富造成的。他指出,流通錢幣,交換有無,民眾衣食生活費用供給不夠,這是因為貨物被極少數奸商壟斷了。計算農業收入,再量入為出,而民眾還有忍饑挨餓的,這是因為糧食被極少數富人囤積了。一個有智慧的人收入可以抵一百個人的勞動收入,愚蠢的人卻連本錢都賺不回。中央政府對此如果不加以調整,民間就會產生侵犯他人利益的富戶。這就是為什么有的人儲存的糧食一百年也吃不完,有的人連糟糠都吃不飽。民眾太富有,就不可以用俸祿支使他;民眾太強勢,就不可以用刑罰來威懾他。如果不去分散聚積的財富,均衡獨占的利益,就會貧富懸殊。因此國家儲備糧食,掌管財用,限制有余,調劑不足,禁止擁有過多的財富,堵塞牟取暴利的途徑,這樣老百姓可以做到家給人足。按照桑弘羊這一說法,漢家收回鑄幣權,是為了解決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賢良、文學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社會貧富不均,是由官府侵占民眾利益造成的。賢良、文學指出,古時候重道德而賤利益,重大義而輕財富。夏禹、商湯、周文王三王的時代,道德大義交替盛衰。衰落了就扶一把,傾覆了就安定它。所以夏朝行政風格是忠厚,殷朝行政風格是敬鬼神,周朝行政風格是禮文繁縟,學校的教化,恭讓的禮節,鮮明燦爛,現在還能從文獻中看到。到了后來,禮義松弛崩壞,良風善俗熄滅,因而那些領取國家俸祿的官僚,違背禮義,爭奪財富,以大吞小,激烈地互相傾軋。這就是為什么有人儲備了百年糧食,而有的人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古代當官的人不種植收割,打獵的人不會捕魚,守關的人,打更的人,都有固定的俸祿,不得兼有職務以外的收入,不得將利益一網打盡。這樣,愚笨的人和智慧的人都會同樣有收獲,不會互相傾軋。他們征引《詩經·小雅·大田》的詩句,其中大意是說:“那里有漏掉的一把莊稼,這里有丟下的谷穗,它們屬于寡婦的利益。”這幾句詩說的就是官府不能將利益一網打盡啊。在賢良、文學看來,朝廷與民爭利,收回鑄幣權,這才是造成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
其次,應該用什么辦法制止假幣盛行、競相奢侈、互相傾軋的不良習俗。御史大夫桑弘羊認為,貨幣政策應該與時俱進,以此來糾正時俗之弊。桑弘羊指出,商湯、周文王繼承夏桀、殷紂王衰世,漢朝乘秦朝弊政之機而發跡興盛。行政風格有的質樸,有的富于文采,并不是隨意改變傳統法度。風俗變壞就要改變法度,并不是一定要改變古代傳統,而是要拯救失誤扶持衰世。因此教化與風俗一起改變,貨幣與時世一起變易。夏朝的錢幣是黑色貝,周人的錢幣是紫色貝殼,后代則用刀布做貨幣。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變衰,這是事物由始到終的運動。因此山林川澤不征賦稅,就會導致君主與臣民同等利益;刀幣不禁止私人鑄造,就會使真假貨幣并行于市。臣民富裕就會競相奢侈,私人操縱財利就會互相傾軋。賢良、文學則認為,要從根本上糾正假幣盛行,就要加強教化,做到移風易俗。他們認為,古時候有集市而不用錢幣,各人以其所有去交換所無,拿布帛去交換蠶絲而已。后世即有龜甲、貝殼和銅錢,幾種貨幣交替使用。錢幣屢次變化,民眾因此越來越虛偽。他們主張要以質樸去補救虛偽,用禮義防止過失。商湯、周文王繼承夏桀、殷紂王衰世,改革法度,改變教化,使殷、周王道興盛。漢初乘秦朝弊政機會,而不去改變法度和教化,反而積蓄財利,改變貨幣,卻想著要返回農業根本,這如同用煎熬去防止燒烤,用燒火去防止水的沸騰一樣。在上位的人愛好禮義,那么民眾就知道用禮義節制自己行為;在上位的人愛好財貨,那么下民就會冒死去追求財利。
第三,應該如何評價漢武帝收回鑄幣權的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指出,漢武帝收回鑄幣權,這是根據民間鑄幣導致的種種亂象而制定的政策。漢文帝時期,放任民眾鑄造錢幣、冶煉鐵器、煮制食鹽。吳王劉濞擅自壟斷沿海湖澤,文帝寵臣鄧通壟斷西山銅器。崤山以東奸詐狡猾的人,都聚集到吳國,秦地、雍地、漢中、蜀郡的奸民都依附鄧通,吳王、鄧通錢幣遍行天下。就是針對藩王作亂、奸民聚集等種種亂象,因此朝廷才有鑄錢的禁令。管制法規一旦確立,奸詐作偽之風就平息下來;奸詐作偽之風平息,民眾就不期望非法所得,而去各自從事他們的本行,這樣,他們不返回農業根本又做什么?因此國家統一鑄錢,民眾就不會產生二心;貨幣由國家發行,下民就不會產生疑問。賢良、文學則指出,國家收回鑄幣權之后,在新政策施行過程中,又產生了鑄幣官從中謀利、部分錢幣不合規格、商賈從中取巧、民眾懷疑新幣等問題。往古時候,貨幣多樣,財物流通,民生安樂。到了后來,漸漸去掉舊錢幣,另發行銀錫龜龍錢幣,不少民眾巧妙使用新幣。錢幣屢次改變,民眾越發懷疑。朝廷于是下令廢除此前天下各種錢幣,命令水衡都尉屬下均輸官、鍾官、辨銅令三官統一鑄錢。主管鑄錢官吏和鑄錢工匠從中牟利,有些錢幣不合規格,因此鑄出來的錢有薄厚輕重之分。農夫不習慣新幣,拿熟悉的舊錢幣來與新幣比較,相信舊幣,懷疑新幣,不知錢幣真假。商賈用質量好的錢幣換取質量差的錢幣,用半數真錢換取成倍的假錢。要買進就要損失實利,要賣出就怕失去常理,心中的疑惑越來越大。對鑄造偽幣雖然已經有了國法,但貨幣有好有壞的現象和過去一樣。選擇真錢會導致貨物的積壓,用錢的人尤其痛苦。《春秋》說:謀劃趕不上蠻夷就不要實行。因此官府對外不壟斷河海川澤,以便有利于老百姓的使用,對內不禁止鑄錢,以便溝通民間的交易。
在以上三個問題上,雙方的觀點針鋒相對。究竟應該如何評價辯論雙方的是非曲直,應該怎樣看待這場關于鑄幣權的辯論呢?從辯論內容可以看出,雙方的分歧是由立場與視角的不同造成的。桑弘羊站在官方的立場上,他更多地看到私鑄錢幣對國家政權所造成的危害,堅定地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賢良、文學則秉持鮮明的民間立場,他們強調的是官府鑄幣對民生利益的消極影響,希望官府關注民間利益。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封建國家掌控財權,將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手中,這是大勢所趨,也是歷史對這場辯論所作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