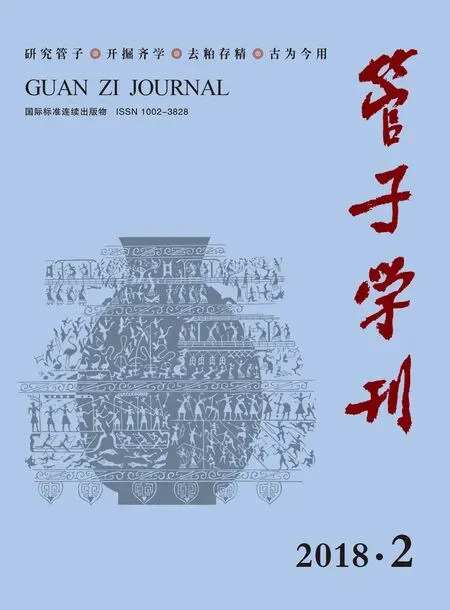中西形而上學建構中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聯系
吳越強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一、太陽·線·洞穴
我們通常把巴門尼德視作形而上學之父,誠然巴門尼德作為前蘇格拉底哲學中最早從形而上學經驗出發,將思想和存在進行同一性理解,通過“是者”意義表示世界本原,對于形而上學的發展有種創世紀的意義。另外,我們也習慣以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來命名這一系列理論,將亞氏的系統闡釋作為形而上學的系統發端。對于柏拉圖理念論在傳統形而上學中的地位則相對模糊。然而,介于巴門尼德和亞里士多德之間的柏拉圖理念論才是真正的第一個系統構建一套形而上學理論框架的學說。
柏拉圖綜合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等前蘇格拉底哲學,在流變和凝固中,從現象世界中凝練出了理念世界。并通過理念世界來對于現象世界重塑,在理論上第一個構建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本體論系統,并且解釋了這種本體論系統與我們身體把握到的外在世界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在理想國中是通過太陽喻,線喻,洞穴喻三者相互互補而實現。
在理想國第六卷中,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以外在世界中,影像基于太陽光的作用在視覺中成像這一樸素的光學原理類比,理念之于外在世界中種種的作用。在這種比喻中架設了一條本體和現象之間的單向聯系,在這種聯系中,理念是超然的,即“知識的對象不僅從善那里得到可知性,而且從善那里得到它們自己的存在和本質”[1]507更高的層次上,柏拉圖認為為了真正重新收獲理念,現象最終必然是要被拋棄的。
隨后,在對于溝通現象和理念中,柏拉圖通過將一條線劃分為大小不等的兩部分,即理念世界(可知世界)和現象世界(可見世界),在將這兩部分進行不均的兩分,實現從模仿可見事物的影像,到事物,再到抽象的數學概念直到理念本身,塑造一個知識論的層次結構。當然,就像理想國中提到相應于線喻將靈魂的四種狀態劃分,即“最高一部分是理性,第二部分是理智,第三部分是信念,最后一部分是借助圖形來思考或猜測”[1]510認識的層次也被確立了下來。
在實現知識論層次建設后,柏拉圖通過洞喻再次強化了人認識的途徑,以洞穴中的人及映射在洞壁上的影像,強調了現象世界的虛假性,又通過一個偶然的人,在他掙脫枷鎖,看到形成洞壁上影像形成的緣故,以及通過自身恢復直到看到洞外一切的全過程,重現了線喻中對于“知識”的劃分層次在認識中的過程。
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以太陽喻、線喻、和洞穴喻,完成了本體論和知識論在最樸素的形而上學理論中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闡釋了“如果不知道正義、榮耀的東西與善的關系,那么正義、榮耀的東西無法保證無知的衛士能夠高尚”[1]502。句話所表現的理念與現實聯系在柏拉圖理念中是如何展現的。這種聯系也被很多學者稱之為“靈魂轉向說(心靈轉向說)”,通過這種“轉向”本體論和知識論得以緊密聯系,并且在柏拉圖這里,也展現了傳統形而上學一以貫之的一種路徑,這種路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本體論出發對認識論的意義得以賦值的過程,這也是文藝復興以后理性啟蒙的“歐洲精神”所表現的。
在這條路徑上,永遠預設著一個實體性存在的偉大,并且伴隨傳統形而上學的發展,這種實體性存在的偉大能更好的推動,因為主客對立而被充分認識的外在世界的發展,但是這條路徑又永遠面對著因為理念世界和經驗世界之間的對立。最終伴隨科學發展,使得這種形而上學存在的根基,這種不證自明,被徹底質疑,而在這種情境下,從胡塞爾現象學開始,以面向現象本身出發,大陸哲學在客觀或主觀的復興形而上學的過程中,開辟了聯系本體論和知識論的形而上學的另一條路徑。
目前,遼寧省完成山洪災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項目的42個縣(市、區)共建有自動雨量站840個、簡易雨量站617個、人工雨量站97個,自動水位站194個、簡易水位站232個、多要素氣象站227個、鄉鎮視頻會議系統824個、預警廣播3 116套。全省共配備傳真機848臺、手搖報警器720個、鑼42 862個、宣傳手冊165 425冊、光盤錄音帶7 319個、明白卡447 925張、警示牌7 188個、宣傳欄7 261個。
二、從存在者到存在
海德格爾認為尼采通過“顛倒”柏拉圖實現了形而上學的終結,也就是所謂的傳統形而上學的完成,作為一個自詡為“本體論”哲學家的人,海德格爾以他獨有的概念體系,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
海德格爾從批判傳統形而上學出發,認為雖然傳統形而上學考慮了存在和存在者,但是作為預設存在的必然在,而在真正討論存在者和存在時,卻將兩者混用,沒有真正理清存在本身的問題,而片面的在存在者的問題上發揮,最終造成了當代實證哲學大潮下對于傳統形而上學的拒斥。所以海德格爾,特別從20世紀30年代后,就不再是“追問在者的在,而是追問在本身”。
海德格爾這條路徑不同于傳統形而上學的思路,將本體論和知識論雙向聯結起來,而是在確然的現象世界中卻追尋在本身,在“究竟為什么在者在而無反倒不在?”[2]3的問題展開中,確立當代形而上學的思路。
在這種思路中,“在”不在僅僅被理解為一種最普遍的概念本身,因為這種普遍而變得無話可說。而是通過存在者在此時此地的存在,即所謂的此在,將事物的歷時性得到體現。在體現后,將此在面向“無”來尋求存在,以此真正面向存在本身。也就是“只有當人之此在把自身嵌入無中時,人之此在才能對存在者有所作為”[3]140。在這種過程中,“無”不在被我們通常理解為沒有,或者荒謬等等。而是一種“本質”存在將被作用于追尋存在本身,即“這個無(NICHTS)是作為存在而成其本質的”[3]356。
海德格爾將“無”升華到“存在”本質和實證科學肆意的時代背景是相關的,就像他自己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提到的“無是所有科學都無法通達的”,那么為了破除“科學思維才是唯一的和真正的思,惟有它,也必須是它才能成為哲學運思的準繩”[2]26。那么從這種對面出發,也就能真正將形而上學在“存在主義”的意義上重新被建立起來了。
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在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聯結中,是一種回溯性的路徑,不同于傳統形而上學,清晰的割裂本體論和知識論,而在一種存在者的此時此刻向存在本身回溯。在這種過程中相較于傳統形而上學中主體的清晰度,這種形而上學不再過分運用泛濫的理性去追尋終極本體,而是將人的存在和世界相同步,再通過突出人的本質回溯到存在本質之上。
然而我們能夠發現海德格爾前期的這種“在場的形而上學”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不得不承襲了傳統形而上學的種種,這也印證了他所謂的“我們對形而上學基本問題的追問是歷史性的”[2]45。這也是海德格爾最終沒有真正完成他的《存在與時間》的一個緣故。
無論柏拉圖主義在傳統形而上學發端中構建的這種溝通本體論和知識論世界的路徑,還是海德格爾通過“此在”向“無”追問回溯的“存在”本質的路徑都是西方哲學語境下對于本體論和知識論關系的考慮。如果我們把視野放置到中國哲學上,我們首先會發現,在中國傳統哲學的論域我們并不能清晰的找到本體論和知識論這樣劃界分明的哲學版塊,但是伴隨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思想大變革,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逐漸形成,在現代新儒家的隊伍中,也出現了一種中西匯通下開辟出的連接路徑,即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
三、良知坎陷說
就所謂的“良知坎陷說”而言,“坎陷”語出《易傳·說卦》:“坎,陷也。”大體上是一種自由否定,或者說一種“自甘墮落”。因為通過這種“這種自甘墮落”才能夠實現內圣開出新外王的思路。誠然就“良知坎陷說”而言在牟宗三處,大體是能夠根據他的思想進行分期的,在此,我們討論的是他最終成熟的理論體系,也就是通過“良知坎陷”從“無執的存有論”開出“有執的存有論”。
對于這種中國現代哲學視野下連接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路徑,是基于以下幾個概念來達成。
1.存在之理和形構之理,這是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中提出的兩個概念,所謂存在之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本體論概念,即“此理不抒表一存在物或事之內容的曲曲折折之征象,而單是抒表一‘存在之然’之存在”[4]77。而形構之理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知識論概念,即“作為形構原則的理……言依此理可以形成或構成一自然生命之特征也。亦可以說依此原則可以抒表出一自然生命之自然征象”[4]77。所以所謂的良知坎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這兩個概念對于道德形而上學的劃分基礎上的
2.一心開二門,這是《大乘起信論》中的說法,即以一眾生心開心真如門及心生滅門。然而所謂的兩門并不是兩個割裂的獨立存在,在一心二門中,真如門是體,生滅門是相,提香交融,本來無二的關系。牟宗三也是借助一心開二門推出了下面這個概念。
3.兩層存有論,從“無執的存有論”開出“有執的存有論”,這兩層存有論,分別以“無執”對應本體界,以“有執”對應現象界,在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學中,這兩種存有論就像一心開二門一樣,不是獨立兩個存在而是“本來無二”的整體理解。
理清上述的概念后,我們就很好理解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學中聯系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路徑,即“良知的坎陷”,牟宗三用坎陷描繪從本體界到現象界聯系何以可能的基礎。當然在這條路徑中,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統攝于主體的,即“統而為一言之,視識心與現象為真心之權用”,而通過這種權用就能實現“道德的形上學不但上通本體界,亦下開現象界,此方是全體大用之學”[5]366。“良知的坎陷”實現了“無執的存有論”開出“有執的存有論”這種突破,并且因為上述的統攝,此處的“執”是“執持其自己”,當然這種所謂的“執持”在“執持”時也就自然而然的使其喪失了“自己”,但是也因此形成了“認知主體”。這種轉變是“知體明覺之自覺地自我坎陷”[5]106,所以在這整個過程中形式的我由“道德本體”坎陷而生,和現象對立,實現了認識何以可能。也就是通過此刻“有知”“有明”“有理”的“定常的不變的我”去作用在現象世界上,并且這種作用因為是“良知坎陷”后的,所以在過分迷失在現象界時,能被本體消解而得以返回。至此達成一種在中國傳統哲學下討論的當代形上學聯系,將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聯系在中國當代哲學話語中得以實現。
四、傳統儒家哲學中本體論和知識論的一個特點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雖然提供了一種連接本體論和知識論的方式,然而這種康德式連接卻在一定程度是,模糊了我們對傳統儒家哲學特點認識。倘若我們試圖在當代再次討論形上學的可能,就需要我們回到傳統儒家去理清中國哲學的根基。
和西方哲學傳統相比,原始儒家哲學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發展,關注點在本體論上,而不是西方那種“依循邏輯科學方法所指點的路徑,再去認識主觀世界或客觀世界,重點在知識論上面”[6]13。當然這也是牟宗三提出“良知坎陷說”開出現象界的思想緣由。
在此,我們需要明白的是這種對本體論的執著從何而來,又指向何方。《尚書》作為原始儒學形成的重要來源,似乎能在一些層面說明這個問題。洪范九疇提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尚書·洪范》)如果我們單純從結構上來看洪范九疇,就會發現,皇極在整個結構上的突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存在一種外在一切被皇極收攝,這與“儒家主要的就是主體,客體是通過主體而收攝進來的,主體透射到客體而且攝客歸主”[7]63是一致的。
我們再來看《大學》這個在宋明理學對原始儒學再發展上起到綱領性作用的文本。大學八條目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這種結構中,格物,致知的主客關系真正統攝了整個過程。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如是。這種關系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客體通過主體收攝。在這種程度上,傳統儒家也就實現了在日用尋常之中體驗高尚的目標,現象世界也就被點化到了理想之中。這和傳統西方哲學的基本方法思路正好是顛倒的。然而在形而上學結果上來說,我很贊同方東美在《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中的說法,“中國形上學適表現為一既超越又內在,即內在即超越之獨特形態,與流行于西方哲學傳統之超自然或超絕型態者,迥然有別”。
在這里似乎我們能夠清楚的說明傳統儒學的一個特點,知識論天然的被本體論所包含,在這種中國傳統形而上學上,一種德性式本體論始終統攝著一切,仿佛自然而然就達成一種和諧的統一。
綜上所述可知:無論是傳統形而上學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處開始的對于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聯系,或者是海德格爾從“此在”出發通過對“無”的審問直面存在本身,還是牟宗三通過“良知坎陷”實現由“無執的存有論”開出“有執的存有論”都是形而上學中本體論和知識論相聯系以此支撐起形而上學的重要路徑。然而通過對于這三條路徑的觀察,我們發現,他們都同時具備著一種深刻的本體論追求。然而我們如果審視中國傳統儒學的發展卻發現一種不同于這三條路徑的天然統一,在這種程度上,本體論追求并不需要通過知識論的聯系來完成,而是本體論自身的自洽。那么基于本體論追求出發去連接本體論和知識論,是否只是西式形而上學建構中不得不進行的一個步驟呢?如果,我們必須將目光從發端處看起,因為“我們只有通過闡明從它起源時就內在地具有的統一的意義(而這種統一的意義同時具有重新確定的作為原動推動諸種哲學嘗試的任務),才能獲得對自身的了解,并借此獲得內在的支持。”[8]27那么我們回過頭去審視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這種模式再對比西式的建構方法。如果說牟宗三選擇了,將傳統儒學的和諧坍陷來達成現實意義,那么是否,我們還能夠選擇另一條路徑來回到傳統呢?這就是本文審視這一切的目的,同時也是未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海德格爾.路標[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4]牟宗三.心體與性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6]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2.
[7]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