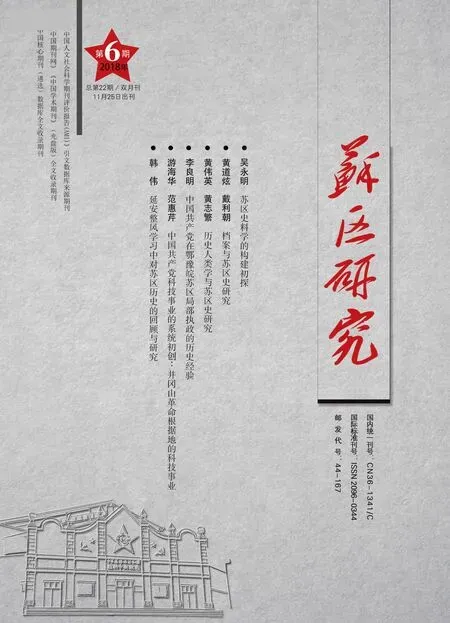蘇區史料學的構建初探
(南昌大學客座教授)
改革開放40年來,蘇區史研究成果有目共睹,這與蘇區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了很大進展不無關聯。同時也應看到,蘇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亦有不足,例如搜集不夠全面、考證還欠深入、整理不盡科學、使用不夠充分等等。對于這些問題,學界時有討論,但結合實例,就如何規范化收集、運用蘇區史料方面作出的專門論述仍然少見。我們認為,加強蘇區史料的搜集整理利用工作,不僅要在實踐上下功夫,還應從理論上探討蘇區史料學的構建。近年來,隨著《蘇區研究》的創刊,蘇區史研究受學界的關注越來越多,研究群體廣涉歷史學、中共黨史學、社會學等學科。這些為蘇區史料學的構建提供了契機。因此,本文擬結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央蘇區民間史料收集、整理與研究”前期實施的體會,就蘇區史料學的體系構建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蘇區史料學的界定與學科歸屬
對史料的重視在中國源遠流長,但作為專門的學科分支,史料學則遲至20世紀以來才逐漸具有獨立的地位。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史料學具有專門或獨立的學科地位。再進一步看,史料學分為通論式史料學和專門性史料學,前者著重從宏觀上闡述搜尋、鑒別、考訂和運用史料的一般性方法和規律,如榮孟源的《史料和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7);后者則闡釋某個時段、某一區域、某一領域或某一類別等具體史料的來源、搜集、整理和運用等,這類著作十分常見。在史料學的一般原理上,兩種史料學并無實質性差異。
蘇區史料學是一門具體而專門的史料學。目前,學術界對蘇區史料學并無專門的闡述,可能是由于長期以來黨史學界相對忽略了對史料學的探討,目前學界少見中共黨史或革命史的史料學專著,僅有的如張注洪《中國現代革命史史料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和周一平《中共黨史文獻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注]前書作者長期從事中國現代革命史及其史料學的教研工作,此書在他多年的講稿基礎上加工整理而成,分為“革命史研究與文獻資料概述”“革命史史料學專題探討”兩大部分;后書從理論基礎、文獻搜集、文獻整理、文獻編纂四大部分搭建了中共黨史文獻學的框架體系。二者各有千秋,均奠定了深入探討黨史史料學的基石,也為我們探索蘇區史料學提供了借鑒。從系譜學意義上說,蘇區史料學的原理奠定在史料學的基礎之上。在內容上,蘇區史料學是對與1927-1937年間中國蘇維埃運動尤其是全國各個蘇區發展有關的史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別、考訂和使用的理論與方法構成的一門科學。在實踐層面,蘇區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和考訂等工作積累有年,但還需進一步的理論化和規范化。
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蘇區史料學究竟是誰的分支?是中共黨史史料學或中國革命史史料學,還是中國近代史史料學或民國史史料學的分支?近代史史料學是一門專門性的史料學[注]就史料學的學科屬性問題,學術界仍有爭論,分別視之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基礎學科或一個領域。參見劉萍:《建國以來史料學的理論探討》,《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150-151頁。此外,中國近代史的時段劃分也有變化,以往學術界習慣將1840-1919年、1919-1949年分別稱作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而今將1840-1949年稱作中國近代史。,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基礎學科或一個專門的學科,拋開蔡元培的“史學基本是史料學”、傅斯年的“史學便是史料學”等強調一端的看法不論,在實踐上,早在1960年,戴逸、陳恭祿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學”課程和在南京大學開設“中國近代史史料介紹”課程;而1980年代初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中華書局,1982)、張憲文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等著作已經讓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呼之欲出。客觀地說,蘇區是中共革命的產物,是中共在革命進程中進行政權建設、社會改造的具體實踐,因而蘇區史天然地具有黨史和革命史的屬性。正由于此,傳統看法一般將蘇區史視為中共黨史或革命史的一部分。但近年來黨史學界出現學術化或歷史學化的趨向,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如下觀點:蘇區史是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重要歷史階段,亦是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適應,蘇區史自然地隸屬于近代史或民國史的范疇,蘇區史料學也屬于中國近代史史料學或民國史料學的一個分支。
二、蘇區史料學構建的初步設想
構建蘇區史料學學科,要準確界定史料學的概念、地位、任務、對象,探討和總結史料工作的理論原則和方法論,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史料收集與利用的具體實踐層面。
(一)蘇區史料的構成
蘇區史料,是有關蘇區歷史的發展、變遷的記載、實物及其它載體。蘇區史料所涵蓋的時間主體是在1927-1937年,但從建黨到大革命時期也應該納入,因為蘇維埃制度的思想與實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蘇區史料具有豐富的構成:其一,根據史料性質分類,如書籍、報刊文章、檔案文件、圖像、廣告、戲曲、歌謠、實物等;其二,按照史料歸屬的組織或生產者來分類,如黨政組織生產的史料、群團組織生產的史料、個人生產的史料、海外史料等;其三,按照史料內容涉及的區域進行分類,如紅區、白區及灰色區域的史料等。但在研究實踐中,最主要的史料有:一是原始檔案,如中央和中革軍委等有關部門積累的文書檔案資料,但從瑞金到達陜北后留下的原始檔案文獻較少,才50余斤,數千件。[注]劉英、丁家棟、楊潔:《長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1期,第146-153頁。還有國民黨“保存”的檔案,如國民黨將軍陳誠率部在江西“圍剿”多年,搜集了大量的文件資料,1935年編成《赤匪反動文件匯編》(6冊),約110萬字。1960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將臺灣所存的大量有關江西蘇區的約1500件歷史文獻整理成21卷縮微膠卷,即“石叟檔案”。[注]孫翠玲、屈凱:《陳誠收集的江西蘇區紅色文獻概述》,《圖書館建設》2012年第10期,第28-31頁。二是蘇區時期創辦的《紅色中華》《紅星報》《青年實話》《戰士》等報刊。三是口述及回憶文獻,如原蘇區的高級干部在延安時期的回憶史料及以此為基礎編纂的歷史文獻。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從1943年9月起召開了一系列地區工作和歷史的座談會,曾在各大蘇區工作的領導干部或重要當事人都回顧了革命歷史,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工作是對蘇區時期的回憶。這批史料雖然數量有限,且主要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參加整風學習、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清算錯誤路線的影響等目的而生,但已經成為最早一批有關蘇區歷史的回憶資料。且由于距離蘇區的時間最近,其可靠性和真實性也具有一定的保障。1949年后,在地方黨史業務部門的組織下,多次征集了革命者的口述及回憶史料。此外,還有書信、日記、圖像、證件等多種史料。
(二)史料搜集的方法論
蘇區史料的搜集,一要眼光向下,走向歷史現場。正如羅志田教授在談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狀況時指出的,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擴充,時至今日,史料擴充仍值得進一步提倡。例如,檔案特別是基層檔案的運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極為不足,造成史學言說中鄉、鎮、縣層次的論述仍然非常薄弱。[注]羅志田:《史料擴充仍值得進一步提倡》,《北京日報》2018年9月3日,第16版。實際上,前些年作者已經提出這個觀點,參見氏著:《見之于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論與表述》,《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頁。就蘇區史料而言,同樣如此。散布在基層縣市檔案館、博物館、革命紀念館等公藏機構的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布滿灰塵,很少有人觸碰,有待全面整理。二要不斷拓展史料的邊界,如20世紀初梁啟超所說的“取諸左右逢其原”[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頁。,關注各種類型的史料,不僅搜集直接史料、有意史料、共產黨史料、國內史料,還要擴展外延,相應地收集間接史料、無意史料、國民黨史料、海外史料等與蘇區歷史相關的一切史料。例如,傳統研究中不太關注影像史料。2016-2017年間,研究者在俄羅斯檔案館找到17個有關中共圖像的卷宗,里面有1千多張紅軍時期、土地革命時期的照片。這些影像檔案“極大地擴展了我們對紅軍時期的理解”。[注]李佳懌:《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攝影文獻研究所主任高初:中國戰時攝影,“燃起一股熱力”》,《文匯報》2018年9月28日,“文匯學人”第4版。據該文介紹,北京大學王奇生教授等16位歷史學家和高初等一批攝影文獻研究者分享戰爭時期的部分檔案,正在共同完成一套三卷本的新的軍事圖集。這些檔案史料的發現者,并非歷史學家,而是來自藝術界、美術館界、出版界。歷史學家擅長的是文本,但是圖片、影像、聲音等非文字史料同樣重要。三要充分利用網絡和搜索引擎,并使之與相關工具書、檔案館等公藏部門相互配合。像孔夫子舊書網、讀秀等網絡資源,極大地便利了史料搜集工作。
(三)史料整理和考訂的方法論
搜集是整理的前提,而整理、考訂則是史料得到科學利用的前提和基礎。因為諸多史料散亂,甚至真偽難辨,相互抵牾,史料的整理和考訂不可或缺。在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是對史料的分類。對此,各家見識不一。[注]就近代史史料而言,新近較具代表性的說法有:嚴昌洪編著的《中國近代史史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梳理了歷史檔案類、奏議類、書札和日記類、傳記類、報刊類、方志和典制類、結集類、史事記載和筆記及野史類、口碑和實物類、叢書和史料選集類等十大類史料;曹天忠所著《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闡述了檔案,會議記錄、社會調查、考察報告、游記,日記、書信、函電,文集、詩歌,回憶錄和口述史料,報紙,期刊雜志,叢書、類書、年鑒、統計資料,方志、年譜、家譜、族譜,傳記、筆記、野史、小說,電子化史料和數據庫史料等十一大類史料。對于蘇區史料,現行的分類方法主要有:按區域分,有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川陜蘇區文獻史料集成、鄂豫皖蘇區史料匯編等;按史料性質分,則有檔案、文件、個人作品、歌謠戲曲、實物等類。新近也有學者按照歷史文獻的文體予以整理,如分為文件類,電文、請示、信件類,讀本、講話、著述類,布告、通知、標語、傳單類,消息、報道類,詩詞、歌曲、戲劇、曲藝類,其他類等多種文體。[注]《凡例》,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川陜革命根據地博物館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我們課題組立足于蘇區史料分為官方史料和民間史料的基礎,進一步將后者細分為基層檔案類、家族契約與民間文書類、口述史料類、民間文藝史料類、實物遺存類等。從操作上來說,地方檔案館等政府部門和學術界通力合作,既有必要也很有意義。如長達260余萬字的《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就是由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合川陜革命根據地博物館整理、編輯而成,已經成為川陜蘇區史研究的核心參考資料之一。因此,相關公共場館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貫徹檔案法,使那些已經解密、符合公開出版條件的蘇區檔案資料,盡早公開出版發行,以惠及學界和社會。
對史料的考訂和鑒別,具體的方法論至少有二:一是考證史料的真偽,對于一些關鍵性史料,其中可能存在的缺文漏字、衍文增句、篇章錯位、失真等問題,需要借助傳統的校勘法、考據法進行嚴謹的考訂,確保史料最大程度的真實,從而避免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認識的偏誤。其具體方法,除了文本本身的考據之外,還須采取綜合比對法——將文字史料與實物史料、檔案資料與口述史料、民間史料與官方史料、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本國記載和外國記載、直說和隱喻等進行綜合互證。二是史料內容及其生產機制的考訂,從來源入手,“重返史料生成現場”,“充分斟酌、分析資料內容”,對“資料編纂的進程作全面探討”[注][日]石川禎浩:《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第93-100頁。他認為,之所以要從“考證學”走向“史料學”,主要是因為黨史資料的翻譯、整理、編纂等都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系統分析史料的生產機制、來龍去脈,史料背后的政治環境、經濟基礎或技術呈現,從而最大限度地達致史料的真實。當然,須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考訂史料的方法。
(四)史料利用的方法論
在史料利用方面,除了遵循一定的規范之外,具體的方法論尤其應該注意以下幾點:一則要綜合運用各種史料,不應片面依賴單一的史料,像圖畫、影像等資料也應受到重視。二則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史料匯編。如公藏部門整理、編輯或內部使用的史料集,亟待向學術界和社會開放,提高利用率。據筆者了解,江西省檔案館在2010年就開始組織縣市檔案館將所藏革命史檔案統一進行電子化掃描整理,但該電子版迄今未向社會公開,學術界的利用仍只是“冰山一角”。例如,要更加重視利用“文史資料”和“傳記文學”。前者是指中國大陸政協部門從1960年代開始進行的由各地政協委員(基本上是各界名流、社會賢達,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親歷者或見證人)寫作的回憶文章選輯,后者是臺灣私人出版機構編輯的專門刊登口述歷史和自傳之類文章的期刊,性質類似于文史資料選輯。[注]謝泳:《“傳記文學”和“文史資料”》,《廈門集》,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6頁。兩類史料匯集中,一些文章回憶了蘇區時期的歷史和社會風貌。三則要拓展史料利用的途徑,首先在學術研究層面,堅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力求史料與方法的統一,誠如翦伯贊所言:“要使歷史學走上科學的階梯,必須使史料與方法合二為一。既用科學方法進行史料之搜集、整理與批判,又用史料進行對科學方法之衡量與考驗。使方法體化于史料之內,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注]翦伯贊:《史料與史學》,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頁。其次在社會教育層面,在展覽、傳播與教育各渠道發揮史料作為素材或載體的最大功能。
三、新技術條件下蘇區史料數據庫建設的策略
在新技術條件下,傳統史料學面臨巨大的挑戰及機遇。蘇區史料的電子化數據庫建設,應該充分借鑒先行者的成功經驗。因為與其它領域相比,蘇區史領域的數據庫建設一直滯后。[注]已有學者作了探討。參見柳丹楓:《關于原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黨史研究數據庫建設的思考》,《出版發行研究》2015年第2期,第88-92頁。1999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文獻資料庫》,一套兩張光盤,資料分為建國前、建國后,分別匯集了2733件、619件重要文獻,共計2000多萬字。這是“我國出版界首次將黨的歷史文件、文獻系統地錄制成電子出版物”。[注]本刊編輯部:《集權威性、文獻性、收藏性、應用性于一體的<中國共產黨文獻資料庫>隆重推出》,《全國新書目》2005年第6期,第6頁。但是,黨史文獻的電子化工作還未廣泛推廣和普及。
蘇區史料數據庫的建設,應契合技術發展的潮流,著力實現精細化、數據化、概念化和可視化。一是匯集史料,針對某個研究主題生成的某個時段,建立包括書籍、報刊、檔案、圖片乃至口述史料在內的各種類型的史料集群;二是標準化處理,針對縮微膠卷等已經初步電子化的檔案史料,采取新技術進行掃描、復制并公開在網上。例如,借鑒地理信息系統(GIS)的原理,對每一份史料,都標注出版時間、出版地點、歸屬地、關涉主體、關鍵詞等,建立方便、快捷的文獻搜索系統,方便使用者隨時隨地調閱。這方面,可以借鑒的一個實例是:哈佛大學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它以人物為主項,對各種來源的史料作數據性的標準化處理,已有的數據類型有人名、時間、地址、職官、入仕途徑、著作、社會地位、親屬關系、社會關系、財產和事件。借此,學者可以進行地理空間、社會網絡、群體統計等多方面的分析統計,并將結果可視化。
蘇區史料數據庫的建設目標,應該是一個開放、可持續發展的公共學術平臺。所謂開放,就是對需要者開放,本地和外地、國內和國外學者都能夠隨時隨地進入、瀏覽、查閱甚至利用;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學界能夠借助技術手段隨時添加新的史料,使史料的搜集、整理、分類和利用等方法不斷細化和完善,同時不斷豐富史料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