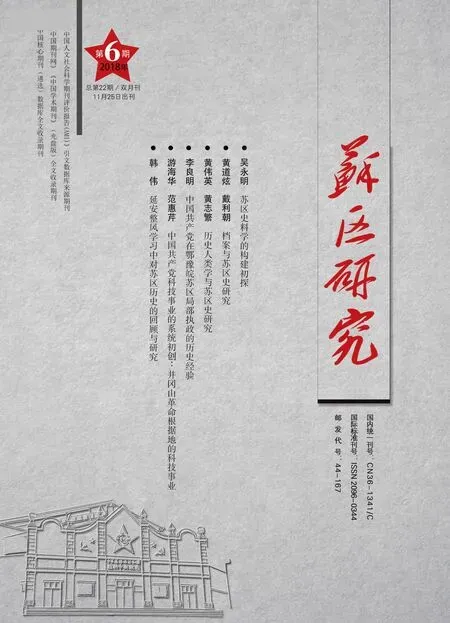歷史人類學與蘇區史研究
(南昌航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新中國建立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近些年,學界更多地用“蘇區史”的概念取代“革命史”,反映出研究取向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學者走向革命的歷史現場,進行田野調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日益廣泛地運用到蘇區史研究中。什么是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有何貢獻于蘇區史研究?
一、蘇區史:革命史研究的社會史取向
新中國建立后,西方國家有一個疑惑:為什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能取得勝利?因此,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在海外頗受重視。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學者較多地關注中國革命中的權力關系、政治制度和革命領袖,蕭作梁(Hsiao Tso-liang)對1930年代初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權力關系的考察、約翰·魯(John E. Rue)對1927-1935年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剖析、金一平(I1pyong J.Kim)對中國共產主義政治的分析等較具代表性。
1970年代末,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認為,只有把開始形成于江西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置于具體的社會背景中,才能真正明白中國革命,他對1927-1934年中共領導的革命和鄉村社會的考察開啟了用社會史的方法研究革命史之先河。之后,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1983)和韋思諦(Stephen C. Averill)都注重把江西蘇維埃運動置于區域社會場景中考察。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學者孫江把袁文才、王佐之死置于井岡山的地方性語境中進行了社會史的再考察。
總體而言,海外對中共革命的研究由起初的“眼光向上”,關注上層政治和革命精英,轉向“眼光向下”,將革命置于具體的鄉村社會場景中,從社會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國內亦如此。
建國后,新政權視革命史為意識形態宣導的重要工具,非常重視革命史的書寫,整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改革開放后,革命史進入學術研究的層面,起初多為宏觀研究。自1990年代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如張靜如、田居儉,力倡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革命史研究。
在國外學界的影響和國內學者的倡導下,國內對中共革命的研究開始擺脫革命史的視角,較多地從區域社會史的角度展開分析,注重從具體的時空和歷史場景下分析革命的發生、發展機制以及革命所引致的鄉村社會變遷。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可謂體現這一研究轉向的開山之作。之后,不少學者努力把革命置于具體的區域社會史脈絡中加以研究,如,饒偉新對贛南土地革命發生機制的分析,劉昶對共產黨在江南發動革命的考察,陳德軍對贛東北革命實踐的深描,黃琨對農民“個體的感受與抉擇”的研究,等等。黃道炫專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堪稱蘇區社會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回首革命之路,如果沒有一批知識精英的宣傳、發動和組織,革命即便發生,也很難收獲改朝換制、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之果;但如果沒有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民)的參與,革命無法形成巨大的歷史潮流。當學界廣泛地用“蘇區史”的概念取代“革命史”時,意味著我們對中共革命的研究,已經不限于對革命精英、政治制度的考察,而是“眼光向下”,關注以下問題:革命在什么樣的場景中如何開展起來?革命如何影響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行為抉擇?革命給中國農村帶來什么影響?當學界開始“眼光向下”理解中共革命時,用哪些資料來詮釋這場革命?如何獲得這些資料?不期然地,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日趨成熟的歷史人類學與蘇區史研究有了一場邂逅。
二、歷史人類學的緣起和方法
什么是歷史人類學?2005年,筆者之一[注]筆者之一系黃偉英,后文不復注明。在南昌大學攻讀碩士,“華南學派”的核心人物陳春聲、劉志偉等學者來講學,其時,歷史人類學在學界還沒有如現在這般廣為人知,我們熱切地向他們請教這個問題。2007年9月,筆者到中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陳春聲、劉志偉老師,專業是“歷史人類學”。從那時起至現在,筆者被無數次地問到:什么是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是研究人類還是歷史?歷史人類學是研究中國古代史還是近現代史?筆者一遍遍地解釋,歷史人類學不是一個學科,沒有具體的研究領域,它是一種研究方法。我們和傳統的歷史學者一樣,坐在書齋中閱讀資料;不一樣的是,我們會走進研究的區域進行田野調查,這種方法是從人類學那里學來的,所以叫“歷史人類學”。
1993年,“歷史人類學”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出現在中國。其時,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來到中國,在素有“眼光向下”及跨學科研究傳統的中山大學演講時,呼吁創立跨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歷史人類學。如果拋開“歷史人類學”的具體概念,“眼光向下”、注重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其實早有發端。1897年,梁啟超在《新史學》極力呼吁“史界革命”,強調治史要眼光向下,“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但梁氏亦感嘆由于史料缺如,真要寫“民間之事”,卻“真有無從下手之慨”。
解決書寫民眾歷史的資料難題之首功,應屬顧頡剛和傅斯年等學者。1927年,他們創立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顧頡剛在《<妙峰山進香專號>引言》中呼吁學者走出書齋、進入田野、廣泛搜集資料的一段話,至今仍被歷史人類學學者們奉為圭臬:“學問上的材料原是無窮無盡,縱橫歷亂的布滿在各人的旁邊,隨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們只知道要他,卻總不肯捋起袖子去收拾他。鳥籠的門雖開,而大家依然麕聚在籠中,啁啾自樂,安度囚牢的生活,放著海闊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這是何等的不勇啊!”傅斯年主張在歷史學研究上,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們通過田野調查或考古,廣泛搜集民間傳說、歌謠、神話、故事、檔案、賬本、契約等民間文獻,在此基礎上,書寫民眾歷史。
1980年代初起,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等學者與海外的科大衛、蕭鳳霞等學者合作,以珠江三角洲為田野,進行了長達十余年的調查與研究。2001年,中山大學成立了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2003年,開始舉辦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之后的15年,每年夏天,都會匯聚起一群年輕學者,一起研讀文獻,田野考察,展開討論。越來越多的學者麇集在從事歷史人類學研究、被稱為“華南學派”的學術共同體中。
概括而言,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特色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區域、個案研究,這種研究并非如批評者所言“雞零狗碎”,而是把區域的研究放在大歷史的思考中進行比較和討論,以重新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歷史;二是注重民間文獻的收集、整理與利用,族譜、碑刻、契約、科儀書等民間文獻都成為重要的研究資料,乃至于有人形容這些學者“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第三,注重實地調查。
三、歷史人類學與蘇區史研究
在中山大學攻讀博士期間,筆者沒有緊隨老師們從事明清史研究,而是以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贛南鄉村社會的變遷(1927-1953年)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在歷史人類學大本營接受的訓練深刻地影響了筆者的研究,因此,自然而然地就將這一方法用在了蘇區史研究中。那么,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進行蘇區史研究,有何裨益?
首先,借鑒歷史人類學“眼光向下”的研究視角,有助于獲得對中共革命的總體性理解。要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既要對革命的精英領袖、大事件展開宏觀研究,也離不開對革命中的蕓蕓眾生、與蘇區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小事件”的細致考察。當我們致力于這一學術追求時,唯有以“他者”的角色,走進蘇區的歷史現場,尋找歷史的主體(即蘇區民眾)對革命的書寫,聆聽他們對革命的敘述與詮釋。在他們的語境中,研究者會發現,革命深刻影響到蘇區每個家庭的日常生計、婚姻、繼嗣、祭祀、信仰、教育等。
當拓寬研究的視野時,研究者也會發現,革命對蘇區鄉村社會的影響并未因1934年紅軍北上戛然而止,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以繼嗣問題為例,革命中,有的革命者犧牲或北上后多年音訊杳無,如果他們并沒有留下后人,其繼嗣問題如何解決?他們的妻子命運如何?其父母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新中國建立后,對烈士、烈屬作了哪些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補償,鄉村社會對此有何反應?建國至今,政府怎樣反哺為革命作出過重大犧牲的原蘇區?原蘇區的基層政府和鄉村社會如何把革命歷史構建成紅色文化,從而形成獨特的政治資源?值得追究下去的議題很多,不一而足。對這些議題的考察,促使蘇區史研究者突破傳統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些具有分水嶺性質的年份的限制(如1934年、1949年),會通蘇區史、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
其次,運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對蘇區民間史料進行搜集和整理。以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贛南、閩西為例,該區域的民眾基本上聚族而居,家族傳統深厚,鄉民重視通過修譜、勒碑、立契等形式保存鄉村記憶。該區域的每一個家庭、家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土地革命的洪流中,人、財、物、社會結構、社會心理與地方文化等都受到沖擊并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些變化既反映在官方文獻中,也體現在族譜、碑刻、契約文書等地方文獻中。這些珍貴的地方文獻散布在鄉村社會、個人收藏愛好者以及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蘇區史研究者可以借鑒歷史人類學“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方法,系統地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各處的中央蘇區族譜、碑刻和契約文書,并加以分類整理。
最后,借鑒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置身于歷史現場,有助于更好地解讀蘇區史資料。蘇區史資料中往往隱藏著一些“地方性知識”,資料的制作者通常不會有意地去注解這些“地方性知識”,如果不回到歷史現場,而是坐在書齋中,無論研究者如何搜腸刮肚,都想不出其所以然。以筆者的親身經歷來說,筆者曾看到兩冊《土地革命分田簿》,詳細記載了孔目村的分田情況,是考察土地革命時期分田的極好資料。在對資料進行量化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產生了一些疑問。對該村進行為期數天的田野調查后,不僅得以釋疑,且注意到田皮權、田骨權在分田中所起的作用。又如,筆者曾看到一本《江西省興國縣榔武區土地及其他不動產假登記底冊》,是考察南京國民政府“收復”原中央蘇區后地權變化的一份重要資料,但其中記錄的復雜的人物關系、每份產業的所有者與“田主”(或山主、土主)、“純熙堂”等,都需要到當地調查才能梳理清楚。田野調查后,不但原有的疑問得以釋清,而且產生了新的學術靈感——自康熙年間以來,贛南鄉村社會逐步形成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數主的產權狀況,對土地革命時期的分田產生了哪些影響?“地歸原主”中,南京國民政府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土改運動中,新政權如何處理這種復雜的產權狀況?
總之,蘇區史研究者借鑒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到原蘇區鄉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不僅可以搜集到相關的民間文獻,加以分類整理;而且,在歷史的現場解讀這些資料,可以獲得歷史的體驗,進而懷著“同情之理解”拓寬和深化蘇區史研究,達到對革命的總體性理解,從而更好地理解、解釋歷史的中國和中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