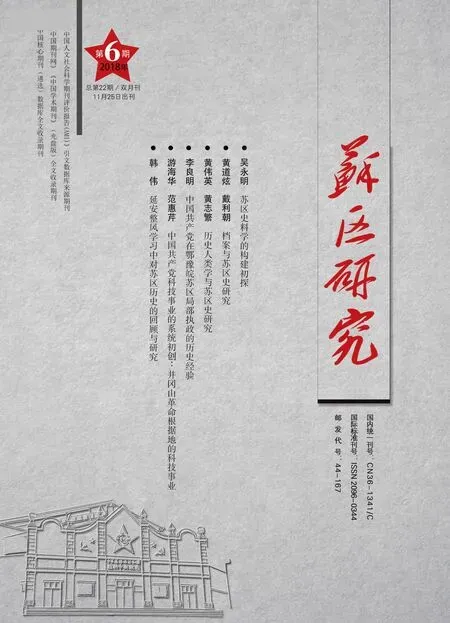中國共產(chǎn)黨科技事業(yè)的系統(tǒng)初創(chuàng):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科技事業(yè)
提要: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于何時?判定的主要依據(jù)是什么?關于這兩個問題,目前學界的研究沒有明確答案。事實上,為破除井岡山武裝割據(jù)的各種困境,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黨和紅軍采取了包括科技在內的許多辦法和系列舉措加以應對。從首創(chuàng)和系統(tǒng)性兩個角度看,井岡山時期在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機構、科技應用、科研成果、科技隊伍、科技教育、科技傳播等方面的諸多舉措和成績,標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科技事業(yè)的系統(tǒng)初創(chuàng)。
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注]科技是指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fā)展,以及其成果在生產(chǎn)實踐中的應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科技事業(yè),包括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機構、科技應用、科研成果、科技隊伍、科技教育、科技傳播、科技社團等。創(chuàng)建于何時?關于這個問題,在科技思想方面,已有的研究大都從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后中共黨人的科技觀講起;在科技實踐方面,學界大都追溯到延安時期和中央蘇區(qū)時期。[注]龔育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科學政策的歷史發(fā)展(建國以前的部分)》,《自然辯證法通訊》1980年第6期;武衡:《延安時代科技史》,中國學術出版社1988年版;齊衛(wèi)平:《延安時期黨領導的自然科學事業(yè)概述》,《黨史研究與教學》1997年第2期;曾敏:《中國共產(chǎn)黨科技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團2005年版;王海軍:《延安時期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科技思想及其實踐探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6期;邱若宏:《中國共產(chǎn)黨科技思想與實踐研究——從建黨時期到新中國成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萬立明:《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科技事業(yè)研究》,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眾所周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是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的第一塊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為什么不是系統(tǒng)初創(chuàng)于井岡山時期呢?判定中國共產(chǎn)黨科技事業(yè)系統(tǒng)創(chuàng)建的主要依據(jù)是什么?對于以上問題,目前的研究并未予以明確回答。
長期以來,關于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研究,學界大都集中在井岡山的軍事斗爭、武裝割據(jù)和土地革命,以及政權、經(jīng)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盡管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鑄幣、郵政和通信、醫(yī)療、軍需工業(yè)、教育等史實,有的有較為詳細的梳理,有的只簡略提及,但是現(xiàn)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從經(jīng)濟史、后勤史、中共黨史等角度進行書寫[注]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494-496頁、下冊第234-235頁;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6、255-265頁;唐小平、歐陽月明:《井岡山時期的后勤保障體系及其經(jīng)驗啟示》,《黨史文苑》2007年第24期;牛保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紅軍后勤保障工作》,《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至今仍無專文從科技史的角度進行考察。基于此,帶著前述問題,筆者在查閱當年革命文獻、親歷者回憶、地方文獻和其他資料的基礎上,嘗試從科技史的角度,梳理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對科技事業(yè)的系統(tǒng)初創(chuàng)概況,以豐富和完善我們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史這一問題的認識。
一、井岡山武裝割據(jù)的困境和科技應對思想與政策
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是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的第一塊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位于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它的創(chuàng)建,是一項全新的事業(yè),沒有前例可循;又是在大革命失敗和湘贛邊秋收起義受挫的背景下“逼上梁山”的,不僅黨內有非議,跟隨上山的人,也有部分抱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此外,井岡山的武裝割據(jù)遭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猛烈進攻,僅在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就先后遭受贛敵的四次“進剿”和湘贛敵軍的三次“會剿”。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對井岡山地區(qū)實行了嚴密的封鎖政策,嚴禁各種物資進入紅區(qū)。因此,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實行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
其一是經(jīng)濟困難。由于敵人嚴密封鎖,亟需的物資進不來,當?shù)氐奈锂a(chǎn)出不去,導致根據(jù)地內經(jīng)濟困窘。1928年10月初,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文獻記載,“一年以來,邊界蘇維埃政權割據(jù)的地區(qū),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nóng)小資產(chǎn)階級群眾及紅軍士兵群眾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注]《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10月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xié)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186頁。11月,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稱:“紅區(qū)白區(qū)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chǎn)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qū)幾乎完全斷絕貿(mào)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nóng)產(chǎn)品不能輸出,農(nóng)民斷絕進款,影響及于一般人民”;“因割據(jù)已久,‘圍剿’軍多,經(jīng)濟問題,特別是現(xiàn)金問題,十分困難”。[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1、79頁。
與此同時,在敵軍嚴密封鎖下,根據(jù)地內物產(chǎn)無法滿足日益壯大的軍隊需求。最初,湘贛邊秋收起義余部上井岡山的時候,只有700余人。1928年4月底,朱毛會師后,紅軍加上家屬激增到1萬余人。歷經(jīng)“八月失敗”,到11月份,紅四軍總人數(shù)大約為5000人。而井岡山的軍事核心地帶即井岡山軍事根據(jù)地,“人口不滿兩千,產(chǎn)谷不滿萬擔”,根本無法滿足幾千常規(guī)軍隊的糧食需求,紅軍的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除糧食外,紅軍“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fā)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xiàn)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8、65頁。1929年2月,剛剛卸任的湘贛邊特委書記楊克敏記述,“紅軍中的生活與經(jīng)濟是非常之艱難的……經(jīng)濟的來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縣如寧岡、永新、茶陵、酃縣、遂川土豪都打盡了”,部隊不僅廢除了薪餉,而且“最近幾個月來,不講零用錢不發(fā),草鞋費也沒有發(fā),伙食費也減少了。……所以最近以來,士兵生活特別的苦(無論士兵官長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樣)”。[注]《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65頁。
其二是軍隊和軍事問題。如兵員補充不易,“兵的增加和槍的增加仍不相稱,槍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損失甚易”,“因天天在戰(zhàn)斗,傷亡又大,游民分子卻有戰(zhàn)斗力,能找到游民補充已屬不易”;另外,“黨代表傷亡太多”,短時難以補充。如紅軍軍事技術太差,“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zhàn)只靠勇敢”。如武器和彈藥缺乏,“各縣赤衛(wèi)隊的槍支還是很不夠,不如豪紳的槍多”。[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3、64、66頁。1929年8月,鄧乾元記述,紅軍及赤衛(wèi)隊“第一困難是子彈,子彈是常常要消耗的,但是消耗沒有接濟的來源”。[注]《鄧乾元關于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對中央報告》(1929年8月),《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342頁。軍隊和軍事問題并沒有隨著紅軍的發(fā)展壯大、根據(jù)地的擴張而消失,而是如影隨形或隱或顯地存在。同年6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一口氣列舉了紅四軍中存在的14個問題和思想分歧。[注]《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這說明紅軍面臨的各種問題不僅數(shù)量多,有的甚至相當嚴重。
其三是傷員的醫(yī)療問題。1928年上半年,在粉碎贛敵的兩次“進剿”中,紅四軍的“傷兵增至500”。[注]《中共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4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150頁。此后,由于又粉碎了贛敵的兩次“進剿”和湘贛敵軍的兩次“會剿”,每“作戰(zhàn)一次,就有一批傷兵”;加上“營養(yǎng)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yī)生藥品均缺”,傷員持續(xù)增加,到1928年11月,紅軍“醫(y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頁。此時紅四軍的總人數(shù),只有5000人。以此計算,傷員數(shù)超過總數(shù)的16%。1929年2月,楊克敏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述,紅軍傷病員多、醫(yī)生少、醫(yī)術差、藥少,傷病員待遇差,“的確不足以鼓勵來者”。[注]《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65-266頁。顯然,這種情況如不加以改善,將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zhàn)斗力和作戰(zhàn)士氣。
此外,還有黨組織問題、政權問題、土地問題、地方主義問題、土客籍問題、投機分子的反水問題等等。
為破除困境,化解難題,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井岡山的黨和紅軍提出了包括科技在內的許多辦法,采取了系列舉措加以應對。其中,有關重視、利用、涉及科技的辦法和政策有:
醫(yī)療方面。1928年2月,毛澤東在工農(nóng)革命軍攻克寧岡新城后,宣布了醫(yī)治白軍傷病兵,優(yōu)待俘虜?shù)恼撸?月,湖南省委指示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傷兵醫(yī)院必須辦理完善”。[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大事記》(1927年8月-1930年2月)、《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特委及四軍軍委信——關于發(fā)展紅軍開展地盤及紅軍的編制策略土地分配問題》(1928年6月19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533、140頁。
交通方面。6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指出,湖南、江西省委“須各有一個專門的經(jīng)常的交通處接受前委的交通,使省委與前委的關系永不中斷”;同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須與省委建立親密交通聯(lián)系,不經(jīng)過蓮花轉”。[注]《中共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規(guī)定前委管轄范圍》(1928年6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特委及四軍軍委的工作決議案——特委與軍委均須與省委建立親密交通聯(lián)系》(1928年6月19日),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zhàn)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qū)卷》,人民郵電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頁。年底,毛澤東在給中央的信中,指出:“交通機關的建設極其緊要”,并指定專人在萍鄉(xiāng)、吉安分別負責建立井岡山與湖南、江西省委的交通機關;1929年1月,滕代遠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稱,“關于交通及機關名稱,均重新多多建立,以防止敵人的破壞”。[注]《前委書記毛澤東經(jīng)江西省委轉中央的信——關于交通及其他》(1928年)、《滕代遠向湖南省委的報告——關于交通及機關名稱》(1929年1月12日),《華東戰(zhàn)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qū)卷》,第44、45頁。
1928年10月初,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了軍事工程技術和醫(yī)療技術的重要性,認為“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醫(yī)院”是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三件大事。[注]《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10月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186頁。
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多次提到軍事技術[注]軍事技術是指建設武裝力量和進行戰(zhàn)爭的物質基礎與技術手段,包括各種武器裝備及其研制、使用和維修保養(yǎng)技術,軍事工程,軍事系統(tǒng)工程;有時也專指操縱、使用武器裝備的技能,如射擊技術、駕駛技術、電子設備操作技術等。和醫(yī)療技術的重要性。關于軍事技術,認為對于士兵,“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zhàn)斗,爭取時間訓練”;訓練下級軍官的教導隊,在“準備經(jīng)常辦下去”的同時,“希望中央和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在不降低紅軍戰(zhàn)斗力的條件之下,必須盡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赤衛(wèi)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后充當……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4、66-67、67頁。關于醫(yī)療技術,毛澤東指出,“醫(y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由于醫(yī)生和藥品奇缺,“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yī)和一些碘片來”;“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yī)治傷兵”。[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67頁。
12月,紅四軍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系列決議案。其中,關于軍事技術,通過了“在大小五井建筑鞏固工事”、“在根據(jù)地須建筑醫(yī)院營舍及紅軍紀念堂”、“軍事技術須加緊訓練,對于下級干部的軍事指揮更應注意,方足健壯紅軍戰(zhàn)斗力”議決;關于軍事人才,通過了“在軍隊組織中要特別健全偵察隊、衛(wèi)生隊、擔架隊、輜重隊、軍需處諸種組織,并須訓練專門人材”決議,并提出建立“軍事政治學校”等提案。[注]《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12月16日),后勤學院學術部歷史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時期》第2冊,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1929年2月,楊克敏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加強軍事訓練、請求中央解決醫(yī)藥和派遣醫(yī)生等。關于軍事技術訓練,他說,“關于干部的訓練,曾經(jīng)辦了一個四軍教導團隊,現(xiàn)又辦了一個紅軍學校,訓練一班下級軍事政治的干部人才,對俘虜?shù)挠柧氂绕湟o”。[注]《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62頁。關于醫(yī)療問題,楊說:“中央能否解決一些,……希望能買點藥送去,派同志中業(yè)[醫(yī)]西醫(yī)者數(shù)人前去工作”。[注]《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79-280頁。
二、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科研機構、科技應用和科研成果
為破除困境,化解難題,在上述科技思想指導下和科技政策推動下,井岡山的黨和紅軍創(chuàng)設了一些公共服務事業(yè),包括紅軍醫(yī)院、步云山兵工廠、塘邊兵工廠、紅四軍軍械處、紅色郵政和通信網(wǎng)絡、井岡山造幣廠、桃寮被服廠、紅軍印刷廠,以及成立了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等。這些公共服務事業(yè)和公共機構,既是戰(zhàn)時的生產(chǎn)單位或公共服務單位,也是戰(zhàn)時簡易的科研機構,在廣泛應用科技的同時,兼具科技研究如科技攻關、技術改進、科技發(fā)明、科學管理等功能。可惜的是,這些公共服務事業(yè)和公共機構,在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湘贛敵軍第三次“會剿”井岡山中,幾乎全部被攻上山的敵軍摧毀。盡管如此,在不長的時間內,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井岡山軍民廣泛地、大膽地進行了科技應用和科研創(chuàng)新,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
第一,在醫(yī)療方面的應用、創(chuàng)新和成果。
一是采用“中西兩法治療”,內科用中醫(yī)中藥醫(yī)治,外科(創(chuàng)傷)由西醫(yī)治療。1928年11月底,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對此已有明確記載。[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67頁。
二是實行分組管理和分科治療,體現(xiàn)了科學管理和專科治療的專業(yè)素養(yǎng)。
1928年10月,后方醫(yī)院從茅坪搬到山上以后,為方便管理和分科治療,當時醫(yī)院設有四個管理小組:第一組和第二組設在大井,主要收治內科病人;第三組設在中井,第四組設在小井,主要收治外科病人;每組均有醫(yī)務主任、醫(yī)生和護理人員。[注]董青云:《在井岡山紅軍醫(yī)院里》,星火燎原編輯部編:《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242頁;中共井岡山地委宣傳部主編:《革命搖籃——井岡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頁。曾經(jīng)有過療傷經(jīng)歷的江華回憶,中西醫(yī)治療是分開的,“在大井吃中藥,西醫(yī)在小井看外科”。[注]江華:《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羅榮恒、譚震林等著:《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第396-397頁。
三是建立了專門的藥房藥庫。據(jù)地方文獻記載,最早的茅坪醫(yī)院,在“茶山源設立了藥庫”[注]中共井岡山地委宣傳部主編:《革命搖籃——井岡山》,第52頁。;1928年4月,茶山源有400多擔藥材[注]《訪問賴章達記錄》,轉引自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研究》,第258頁。。醫(yī)院工作人員董青云記述,七溪嶺戰(zhàn)斗后,繳獲了大批西藥,“運到寧岡象山庵,堆滿了兩間房”;曾志回憶,“大井有個中藥鋪”。[注]董青云:《在井岡山紅軍醫(yī)院里》、曾志:《蔡協(xié)民烈士和紅軍生活》,《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243、358頁。1929年2月底,楊克敏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醫(yī)院設有“中藥西藥處”。[注]《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66頁。
四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簡,不但自制各種醫(yī)療用具,而且深入挖掘傳統(tǒng)中醫(yī)、中藥的治療價值。紅軍醫(yī)務人員不僅用竹木自制鑷子、膿盤、軟膏刀、軟膏盆和大小便器,用漂白布代替紗布、繃帶,用楓樹葉、大黃葉蓋傷口,用鋸木鋸骨,殺豬刀作離斷刀,而且到山上采挖草藥制成中藥,并從群眾中收集民間驗方,用草藥和土法治療,如用青合草治瘧疾,老茶葉水消毒、細辛止痛、細骨蓮接骨,換藥用硼酸、升汞沙、雙氧水、鐵氯酒、鹽水等,“化膿的很少”;內科多用中藥治(健胃用大黃),“治療效果也不錯”。[注]《井岡山時期紅軍衛(wèi)生救治工作的情況》(1927年10月-1930年),后勤學院學術部歷史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時期》第2冊,第735頁;中共井岡山地委宣傳部主編:《革命搖籃——井岡山》,第27-28、52頁。
對于醫(yī)院的醫(yī)療情況、醫(yī)療技術和醫(yī)療創(chuàng)新,當年的革命親歷者劉榮輝、吳樹隆、彭儒、張令彬、王云霖、王耀南等都有較為詳細的回憶。[注]劉榮輝:《上井岡山前后》、吳樹隆:《湘南暴動的前前后后》、彭儒:《井岡山上的艱苦生活》、張令彬:《幾件難忘的舊事》、王云霖:《小井紅軍醫(yī)院及其他》,《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10、102-103、156、224-225、254、264頁。
第二,在軍械、彈藥修理和制造上的科技應用、創(chuàng)新和成果。
在紅軍先后興辦的兩個兵工廠和紅四軍軍械處里,工人們既能修理槍炮,也能制造梭鏢、大刀、槍彈和手榴彈。曾經(jīng)擔任軍械處處長的譚冠三回憶,最初的步云山兵工廠,“只是修理一些簡單的兵械而已”[注]譚冠三:《回憶毛主席在井岡山的偉大革命實踐》,《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第472頁。;當?shù)氐脑L問記錄也顯示,兵工廠“主要修理槍枝”[注]訪問黃英階、張桂庭、劉桂生記錄,1970年7月27日。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上,第494頁。。1928年五、六月間的塘邊兵工廠,有“兩座火爐,制造來火槍(鳥槍)、短槍,共制造來火槍十六枝,短槍七枝,還修理了不少槍枝”。[注]井岡山專區(qū)宣委文物資料調查隊采訪資料,1968年9月2日。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上,第496頁。紅四軍軍械處的設備,除普通鐵匠鋪具有的一些工具外,主要是從湘南繳獲來的一具老虎鉗和一臺老式刨床;1928年12月,又繳獲了挨戶團一處兵工廠的全套設備,這時可以生產(chǎn)五響槍和“馬尾手榴彈”。[注]吳學海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頁。羅東祥對軍械處的設備和技術也有回憶,他說“主要是修理槍支和造單響槍為主,但也打一些梭鏢和大刀。軍械處里的工具有風箱、火爐、鏟子、鐵錘,還有一架專門用來車槍筒的鉆機”。[注]羅東祥:《在茨坪的黨政機關及其他》,轉引自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研究》,第244頁。
第三,在郵政和通信方面的科技應用及創(chuàng)新。
一是發(fā)行了首套蘇區(qū)郵票。1928年5、6月間,新遂邊陲特別區(qū)工農(nóng)兵政府發(fā)行了面值1分和5枚的兩種郵票(簡稱新遂票),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根據(jù)地的第一套郵票。同年11月,湘贛邊區(qū)寧岡郵局還發(fā)行了面值1分的郵票(簡稱寧岡票)。[注]李虹:《我國首套區(qū)票發(fā)行時間揭秘》,《黨史文苑》2011年第21期,第5-8頁。雖然這種說法遭受質疑,但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發(fā)行首套蘇區(qū)郵票,既有物證,又有證人證言[注]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郵政總局局長和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信柜主任的賴紹堯記述:“1928年初,湘贛邊區(qū)工農(nóng)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礎上建立了赤色郵政,并發(fā)行了郵票。這是中國人民郵政的開始”。賴紹堯:《中央蘇區(qū)郵政的歷史概況》,《江西文史資料選輯》1981年第6輯。,還有國家權威部門的會檢認證。[注]陳洪模、王小玲:《井岡山是我國首套區(qū)票的發(fā)行地嗎?與李虹同志商榷》,《黨史文苑》2012年第7期,第52-56頁;李虹:《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湘贛邊區(qū))是我國首套區(qū)票的發(fā)行地——對陳洪模、王小玲同志〈商榷〉一文的答疑》,《黨史文苑》2012年第9期,第48-53頁。
二是秘密聯(lián)絡手段和信號被廣泛采用。如,1928年,蓮花縣委為了與井岡山聯(lián)系便利,除指定兩名專程的交通員外,另行設立了兩路地下交通;其中,“緊要的特別信件俱用藥水(青礬、五倍子)寫”;1930年,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還出臺了文件,專門規(guī)定了交通接頭和保存文件應注意的種種方法,關于交通接頭,如“秘密交通機關要設幾個,并要指定灰色同志以負專責”;關于保存文件,如“在嚴重時,寫信要用秘密法!如譯定號碼符號,以代字,或用藥水寫或寓意寫法”。[注]《劉振鴻等關于蓮花縣赤色郵政的回憶》、《少共永新、寧岡縣委〈黨務訓練教材〉——關于交通接頭與保存文件》,《華東戰(zhàn)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qū)卷》,第590、60、61頁。1929年1月,敵軍強攻上山,紅五軍沖下時,“沒有電臺,全靠寫藥水信”[注]田長江:《在斗爭中成長》,《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408-409頁。和紅四軍聯(lián)系。
第四,在鑄幣方面的科技應用和創(chuàng)新。
井岡山造幣廠吸收了當?shù)亍爸x氏造幣廠”[注]20世紀20年代,廣東龍川縣銀匠謝榮珍、謝榮光兄弟,先后遷移到遂川五斗江、井岡山山區(qū)湘州的東坑村定居。他們利用自己造銀器的一技之長,辦起了造幣廠,專造“花邊”(銀元)。該廠曾為王佐的綠林隊伍造過“花邊”,后為官府下令取締和通緝。李春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紅軍造幣廠》,《金融與經(jīng)濟》1986年第2期,第61-62頁。的傳統(tǒng)鑄造工藝,創(chuàng)新了制模技術,并為銀元打上了“工”字印記。造幣的原料主要來自于打土豪得來和戰(zhàn)場上繳獲的大量銀器、首飾,即將銀器、首飾等材料回爐熔化制成銀餅,“再將銀餅置入原型銅模內。以碓石沖壓而成,由于操作笨重,每天只能生產(chǎn)六七十枚銀洋”。[注]吳自權:《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鑄幣》,《中國錢幣》1986年第4期,第2頁。根據(jù)制模、鑄造等技術上的難易程度,造幣廠選擇仿制了墨西哥版的1895年和1908年兩種花邊為直式鋸齒形和單麥穗形比較簡單的鷹元版別,并在鑄出后的銀元版面上加鑿一個“工”字,表明是工農(nóng)兵蘇維埃政府發(fā)行流通的貨幣。[注]羅開華、羅賢福主編:《湘贛革命根據(jù)地貨幣史》,第39頁。最初由于沒有經(jīng)驗,造出的銀元不響,表面不光滑,后來經(jīng)過反復試驗,發(fā)現(xiàn)銅模比鋼模好,又不斷改進提煉和壓模的技術,終于造出了質量較好的銀元。[注]訪問井岡山老人記錄,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下,第331頁。而據(jù)范樹德回憶,鑄造銀元的模子,既不是銅模,也不是鋼模,而是“硬度很強”的銻模;造出的銀元凹凸不平,工藝水平不高。[注]范樹德回憶:“為了造好銀元,我們每到一個縣城就去找首飾店,請首飾店里用銻制成一個造銀元的模子。這是硬度很強的模子……我們輜重隊曾經(jīng)將自制的五十塊銀元包在一張紙里,但五十元錢怎么也卷不成一個筒筒。如果是‘袁大頭’,五十元錢卷起來不太難。原因是我們造的這種銀元凹凸不平,工藝水平不高”。范樹德:《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505頁。造幣廠只存在六個月,用了千把斤銀料,做了萬把塊銀元。[注]羅開華、羅賢福主編:《湘贛革命根據(jù)地貨幣史》,第40頁。
第五,在服裝制造技術方面的應用和創(chuàng)新。
在桃寮被服廠,工人們不僅采用機器生產(chǎn),而且具備了布匹染色技術。被服廠的縫紉機,是攻打遂川縣城獲得的,“大概有六部縫紉機運上了井岡山”;曾志證實,“縫紉廠內有五六部機器”。[注]范樹德:《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后勤工作》、曾志:《蔡協(xié)民烈士和紅軍生活》,《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503、358頁。被服廠工人劉應龍回憶,“做衣服的白布用灰靛染色,沒有灰靛時就用茶籽殼、稻草灰的土辦法著色”。[注]劉應龍:《回憶桃寮被服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軍需生產(chǎn)部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軍需生產(chǎn)回憶錄》(1927-1949年),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范樹德記述,“從遂川貨棧運來的大部分白布染成灰、黑、藍色,供被服廠使用”。[注]董青云:《在井岡山紅軍醫(yī)院里》、范樹德:《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246、503頁。
第六,在印刷技術方面的應用和創(chuàng)新。
在紅軍印刷廠,負責人劉輝霄帶領工人們摸索開動了石印機,發(fā)明了替代性油墨。1928年5月,根據(jù)地的發(fā)展壯大急需印發(fā)各種文件和宣傳品,但是從永新繳獲的石印機沒有人會使用。學生出身的寧岡縣委宣傳部長劉輝霄,和幾個安源工人出身的戰(zhàn)士,邊擺弄邊摸索,慢慢使喚動了機器。后來,劉輝霄又在炊事員的啟發(fā)下,將洋油、煙灰、豬油等拌合在一起,經(jīng)過多次試驗發(fā)明了可使用的油墨。[注]永新縣文化館提供的訪問資料,1977年1月20日;劉先焜回憶(江西省委黨校提供的回憶材料)。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上,第495頁;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研究》,第245頁。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就是印刷廠印的。[注]韓偉:《關于秋收起義和向井岡山進軍等問題》,《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第443頁;永新縣文化館采集資料,1977年1月20日,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上,第496頁。
第七,在軍事工程技術方面的應用。
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動員群眾,修筑哨口工事。1928年11月底,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記述,井岡山軍事根據(jù)地,“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軍事根據(jù)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jù),利用山險是必要的”。[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8頁。雖然說井岡山軍民是利用傳統(tǒng)的建筑技術在山險修筑工事,談不上很高的科技含量,但是畢竟屬于軍事工程技術的范圍。
三、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科技隊伍、科技教育和科技傳播
井岡山軍民在廣泛進行科技應用和創(chuàng)新的同時,不但凝聚了各領域的科技隊伍,而且通過實踐中的傳習培養(yǎng)了后續(xù)的科技人才,傳播了科學知識和技術。與此同時,井岡山軍民還在根據(jù)地開辦了教導隊和紅軍大學,開創(chuàng)了集中學習模式以培養(yǎng)科技人才、進行科技傳播的先河。
首先,凝聚和培養(yǎng)了科技隊伍。表現(xiàn)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醫(yī)療隊伍茁壯成長。
茅坪后方醫(yī)院時期,據(jù)張令彬回憶,“只有幾個中醫(yī)”,衛(wèi)生隊長是何清南,黨代表是賴傳珠。[注]張令彬:《幾件難忘的舊事》,《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224頁。而據(jù)地方文獻資料,起初有兩個中醫(yī),一個西醫(yī),加上看護員和擔架隊共20多人。[注]中共井岡山地委宣傳部主編:《革命搖籃——井岡山》,第52頁。醫(yī)院搬到山上以后,醫(yī)院擴大了,院部下設有看護訓練班、擔架排、藥房和手術室等,醫(yī)護隊伍增加了很多人。劉榮輝記述,“湖南部隊上山以后,帶來了一些醫(yī)務人員”,小井醫(yī)院的負責人是段執(zhí)中,后來曾志擔任了醫(yī)院的黨代表;吳樹隆回憶,小井醫(yī)院的院長是原來二十八團的衛(wèi)生隊長段執(zhí)中,還有幾個護士,一個醫(yī)生叫李保山;張令彬回憶,大井醫(yī)院有個管理員叫張仰長,醫(yī)生姓曾;鄢輝和江華都回憶,醫(yī)院院長是曹嶸,黨代表是肖光榮;后來出任醫(yī)院黨總支書記的曾志回憶,是曹嶸任院長,有幾個護士,還有管理人員,全院只有十幾個黨員。劉、吳、張、鄢、江等人[注]劉榮輝:《上井岡山前后》、吳樹隆:《湘南暴動的前前后后》、張令彬:《幾件難忘的舊事》、鄢輝:《在紅三十一團》、江華:《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曾志:《蔡協(xié)民烈士和紅軍生活》,《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10、102-103、225、336、393、396、357頁。回憶表明,醫(yī)院的管理人員和醫(yī)護人員至少有10人以上,而從曾志的回憶語氣推測,醫(yī)護人員當為黨員的數(shù)倍。董青云回憶,醫(yī)院下分4個管理小組,每組有醫(yī)務主任1人、醫(yī)生2人,護理人員若干人,據(jù)此推算,醫(yī)院醫(yī)生至少有12人;另一工作人員王云霖回憶,醫(yī)院分為3個所,每所有1個所長、1個指導員、一個司號員、一個文書、一個理發(fā)員、一個炊事班、兩三個醫(yī)生、十來個護士,據(jù)此推算,醫(yī)院的管理人員至少有18人、醫(yī)生10人左右、護士四五十人。[注]董青云:《在井岡山紅軍醫(yī)院里》、王云霖:《小井紅軍醫(yī)院及其他》,《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242、254頁。地方文獻有一個確切的數(shù)目,說后來的紅軍醫(yī)院“發(fā)展到十六名醫(yī)生和四十幾個護理人員”。[注]中共井岡山地委宣傳部主編:《革命搖籃——井岡山》,第52頁。依據(jù)上述材料,不難推算,不包括管理人員,醫(yī)院的醫(yī)生和護理人員大約在六七十人左右。
醫(yī)療隊伍的發(fā)展壯大與醫(yī)療實踐中的傳習是分不開的。王云霖回憶,“當時醫(yī)院有一個看護訓練班,年紀輕的小鬼就送來受訓學看護”,“受幾天訓就當看護”,“團有衛(wèi)生隊,營連沒有衛(wèi)生機構”,于是“抽調一些年輕的小鬼送衛(wèi)生隊訓練,懂了碘酒什么的用法,分到了營里,營里才有了衛(wèi)生員了”;吳樹隆回憶,醫(yī)院“當時有一個看護訓練班”,“看護員都是新的,組織衛(wèi)生員們上課學習技術”,1928年后,部隊的“衛(wèi)生工作越來越好,抽調出些小鬼送衛(wèi)生隊訓練,從此以后營部才能輪到一個,懂點碘酒什么用的就分配走了。1931年連就有衛(wèi)生員了”。[注]《井岡山時期紅軍衛(wèi)生救治工作的情況》(1927年10月-1930年)、《〈井岡山時期座談會記錄〉中有關部隊醫(yī)救工作部分(摘錄)》,《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時期》第2冊,第736-737、735、736;738、739頁。
第二,軍械修理與制造隊伍由少到多。
最早的步云山兵工廠,“起初有七、八人,后來發(fā)展到十多人”;塘邊兵工廠,“有七、八個人”;茨坪的紅四軍軍械處時期,“由湖南遷來二十多個工人在里面做”。[注]訪問黃英階、張桂庭、劉桂生記錄,1970年7月27日;井岡山專區(qū)宣委文物資料調查隊采訪資料,1968年9月2日;訪問羅東祥記錄。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上,第494、496頁。1928年底,工人增加到30多人。[注]吳學海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第25頁。
第三,紅色郵政和通信網(wǎng)絡隊伍頗具規(guī)模。
由于赤色郵政的建立,以及交通站、遞步哨和聯(lián)合通信站的普遍設立,根據(jù)地有了一支龐大的通信隊伍。限于資料,這個隊伍的人數(shù)無法估量,能夠使用秘密通信技術的人員更是難以估計。根據(jù)地對于這類人才還是非常重視、著意培養(yǎng)的。據(jù)曾志回憶,當時井岡山上,“還有些小孩學吹號,有個號兵班,號兵班里有個九歲小孩,名叫楊紹良,在那里學吹號”。[注]曾志:《蔡協(xié)民烈士和紅軍生活》,《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358頁。利用約定的號子進行聯(lián)絡、互通信息,是部隊間重要的通信方式之一。馬技茹回憶,南昌起義時,“沒有無線電通信,主要是利用人工傳遞命令和司號、槍聲進行聯(lián)絡”。[注]《馬技茹介紹紅軍通信歷史》,江西省郵電管理局郵電史編輯室編:《蘇區(qū)郵電史料匯編》下,第234頁。因此,井岡山的號兵班,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根據(jù)地的第一個號兵班,應該培養(yǎng)了不少號兵。
第四,造幣隊伍從無到有。
為傳承傳統(tǒng)的鑄幣技術和經(jīng)驗,井岡山造幣廠最初延請了謝火龍、謝亞秋、謝亞五等人當師傅,指導工人進行生產(chǎn),后來工廠規(guī)模擴大,工人也增加了不少[注]李春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紅軍造幣廠》,《金融與經(jīng)濟》1986年第2期,第61頁。;從開始的幾個人,增加到十多個人[注]訪問井岡山老人記錄,轉引自許毅:《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財政經(jīng)濟史長編》下,第331頁。。
第五,縫紉隊伍成長迅速。
桃寮被服廠的骨干,最初是“從部隊中抽調了十余個會縫制衣服的紅軍戰(zhàn)士,并從農(nóng)村聘請了一批裁縫師傅”[注]《井岡山的武裝割據(jù)》(革命歷史資料叢書之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頁。組成,朱毛會師后,有部分從“湖南來的婦女也都到被服廠里去工作”。[注]陳茂:《從湘南到井岡山》,《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第565頁。范樹德回憶,被服廠的手工活,是在當?shù)卣偌恍D女做,“有時二三十人,有時五六十人。被召來的這些婦女就成為我們的臨時成員”。[注]范樹德:《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504頁。工人劉應龍回憶,他負責的組,“人最多,有13個人”,被服廠“起初三四十人,后發(fā)展到130多人”。[注]劉應龍:《回憶桃寮被服廠》,《軍需生產(chǎn)回憶錄》(1927-1949年),第4-5頁。可以看出,在被服廠成立后的半年左右,其生產(chǎn)人員,從最初的三四十人增長到百人以上。
第六,印刷隊伍限于資料,具體人數(shù)不詳。
其次,在凝聚和培養(yǎng)科技隊伍的同時,井岡山軍民還應現(xiàn)實需要在根據(jù)地嘗試集中學習以培養(yǎng)軍事人才的辦學模式。
1929年2月,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對此有記述。他說:“關于干部的訓練,曾經(jīng)辦了一個四軍教導團隊,現(xiàn)又辦了一個紅軍學校,訓練一班下級軍事政治的干部人才”;報告后面再次提及,“最近又辦了一個紅軍學校”。[注]《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62、273頁。其中,紅四軍軍官教導隊1927年12月創(chuàng)辦于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當時稱工農(nóng)革命軍軍官教導隊。[注]范樹德:《文家市會合之后》,《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490頁。1928年秋,教導隊遷到茨坪。教導隊下設三個區(qū)隊,區(qū)隊長分別由陳伯鈞、陳士榘和張令彬擔任。[注]賀禮保回憶:“我原是二十八團一營的。1928年8月從桂東回來,在遂川負傷,我們這些傷員被編入教導隊。梁軍與我編在一起,他是廣西人,一臉麻子,擔任教導隊隊長”。分別參見宋裕和:《井岡山上的紅軍軍官教導隊》、賀禮保:《井岡山的戰(zhàn)斗生活片段》、張令彬:《幾件難忘的舊事》,《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144、214、223頁。教導隊的主要任務是訓練下級軍官。參訓人員都是從部隊和地方武裝中挑選出來的先進分子,第一期教導隊只辦了兩個月,于1928年2月參加新城戰(zhàn)斗時提前結束,培訓學員100余人;1928年11月,教導隊的總人數(shù)為150人。[注]中共寧岡縣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寧岡蘇區(qū)志》,1993年印,第204頁;《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4頁。訓練的主要內容是政治和軍事,政治課占40%,軍事課占60%;其中,軍事課主要是學習軍事知識和技術(如戰(zhàn)術指揮、十二字游擊戰(zhàn)術),以及軍事操練等,如爬山、跑步、出操、練習槍法、野戰(zhàn)。[注]宋裕和回憶,“在教導隊學軍事,搞軍事訓練”;龍開富回憶,“軍事干部要到教導隊受訓,陳士榘、張令彬是教員,主要是訓練班以上的干部和積極分子”。分別參見宋裕和:《井岡山上的紅軍軍官教導隊》、宋裕和:《毛主席留我們在山上》、龍開富:《在毛主席身邊》,《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145-146、169、325頁;張令彬:《毛委員創(chuàng)辦紅軍教導隊(摘錄)》,后勤學院學術部歷史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時期》第2冊,第492-493頁。1929年1月,敵人發(fā)動第三次“會剿”時,教導隊撤銷了;其中,教導隊的一隊和二隊變?yōu)榧t五軍的特務隊。[注]宋裕和:《毛主席留我們在山上》、賀禮保:《井岡山的戰(zhàn)斗生活片段》,《星火燎原·井岡山斗爭專輯》,第170、214頁。紅四軍軍官教導隊,不僅“是紅軍的第一個教導隊,也是我軍最早的訓練基層干部的機構”。[注]張令彬:《毛委員創(chuàng)辦紅軍教導隊(摘錄)》,《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時期》第2冊,第491頁。
至于紅軍學校概況,除楊克敏在報告中兩次提及外,筆者并未發(fā)現(xiàn)加以說明的一手材料。間接的材料也不多,如《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附錄材料“軍隊組織系統(tǒng)”關于1928年12月以后的紅軍第五軍記載:紅軍學校校長為彭德懷[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85頁。;《彭德懷年譜》記載,1929年“1月上旬,兼任井岡山紅軍學校校長”[注]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另外,1929年10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五軍的報告》記載,紅五軍除統(tǒng)轄五個縱隊,軍部還有紅軍隨營學校等直屬單位;其中,紅軍隨營學校是“中央特令辦的,現(xiàn)有學生50名,3月為一期”。[注]《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五軍的報告》(1929年10月),《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407頁。該紅軍隨營學校何時開辦,不得而知。井岡山的紅軍學校,是否就是紅五軍的隨營學校,還是彭德懷到井岡山后在紅四軍軍官教導隊余部基礎上創(chuàng)辦的學校?該問題值得挖掘史料進一步探討。不過,從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四五縱隊800余人抵達井岡山和紅四軍會合(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主力下山),次年1月底留守井岡山的紅五軍在強大敵軍的進攻下不得不下山、井岡山失守等情況推斷,紅軍學校在井岡山存在的時間不到兩個月。
再次,井岡山的科技傳播主要通過兩條途徑進行。一是在各個生產(chǎn)和服務單位,通過生產(chǎn)和服務實踐傳播科技知識和技術。如在醫(yī)院、兵工廠、造幣廠、服裝廠等通過師傅帶徒弟的形式傳授科技。二是在教導隊和紅軍大學中,通過集中教育的形式傳授科技知識和技術。這兩方面上文已有述及,此處不贅。
四、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系統(tǒng)初創(chuàng)于井岡山時期
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于何時?判定的主要依據(jù)是什么?對于這兩個問題,目前學界似乎沒有明確的答案。從學界已有的研究看,在科技思想方面,大都從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后中共黨人的科技觀講起;在科技實踐方面,大都追溯到延安時期和中央蘇區(qū)時期。其背后隱含的觀點,即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于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后,因為這時期的共產(chǎn)黨人已經(jīng)擁有了自己的科技觀(思想);或者為應創(chuàng)建于中央蘇區(qū)時期,因為在中央蘇區(qū),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科技思想和政策,而且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科技實踐。
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值得商榷。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的主要判定依據(jù)應該是科技實踐,而不是科技觀(思想)。科技觀(思想)不能脫離科技實踐單獨作為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的標志,但可以作為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的歷史背景;科技觀(思想)只有和其直接指導下的科技實踐一起,才是比較完美的科技事業(yè)創(chuàng)建標志。以此判斷,第一種觀點誤將科技觀(思想)等同于科技事業(yè),而第二種觀點忽視了在中央蘇區(qū)之前,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井岡山軍民系統(tǒng)初步進行科技實踐的事實。
據(jù)本文的探討,為破除井岡山武裝割據(jù)的各種困境,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井岡山的黨和紅軍采取了包括科技在內的許多辦法和系列舉措加以應對。在科技思想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利用相關科技醫(yī)治白軍傷病兵、建立秘密交通網(wǎng)絡、修筑完備的工事、建設較好的醫(yī)院、提高官兵軍事技術等思想和政策。在科研機構方面,井岡山的黨和紅軍創(chuàng)設的紅軍醫(yī)院、兵工廠和軍械處、紅色郵政和通信網(wǎng)絡、造幣廠、桃寮被服廠、印刷廠、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等公共服務事業(yè)和公共機構,既是戰(zhàn)時的生產(chǎn)和服務單位,也是戰(zhàn)時簡易的科研機構,兼具科技研究如科技攻關、技術改進、科技發(fā)明、科學管理等功能。在科技應用和科研成果方面,上述戰(zhàn)時生產(chǎn)和服務單位,廣泛地、大膽地進行了科技應用和創(chuàng)新,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如在紅軍醫(yī)院,采用“中西兩法治療”、實行分組管理和分科治療、建立了專門的藥房藥庫、自制各種醫(yī)療用具、深入挖掘傳統(tǒng)中醫(yī)中藥的治療價值。兵工廠和軍械處能夠修理槍炮、制造簡易槍彈。在郵政和通信網(wǎng)絡中,發(fā)行了首套蘇區(qū)郵票、應用秘密或約定的聯(lián)絡手段和信號。造幣廠鑄造了“工”字銀元。被服廠不僅采用機器生產(chǎn),而且掌握了布匹染色技術。印刷廠摸索發(fā)明了替代性油墨,采用石印機印刷。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動員群眾修筑哨口軍事工程。在科技隊伍方面,不但凝聚了醫(yī)療、軍工等各領域的科技隊伍,并且通過實踐中的傳習培養(yǎng)了后續(xù)的科技人才。在科技教育方面,開辦了教導隊和紅軍大學,開創(chuàng)了集中學習模式以培養(yǎng)軍事技術人才的先河。在科技傳播方面,一是在各個生產(chǎn)和服務單位,通過生產(chǎn)和服務實踐傳播科技知識和技術;二是在教導隊和紅軍大學中,通過集中教育的形式傳授科技知識和技術。
當然,由于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存在時間較短(前后不過兩年多時間,如果算到1929年1月為止,只有1年零4個月)、頻繁緊張的戰(zhàn)斗(敵軍先后發(fā)動4次“進剿”、3次“會剿”)、敵軍的嚴密封鎖、自身的經(jīng)濟困難等多種原因,用后來者的眼光審視,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科技事業(yè)自然存在種種不足。
其一,盡管井岡山時期不乏重視、利用科技的思想和政策條文,但據(jù)筆者目力所及,沒有出臺過任何一份專門的、完整的科技政策文件。
其二,沒有創(chuàng)立科技社團,這方面還處于空白。
其三,井岡山斗爭時期,本來有可能使用有線電話,建立有線電話隊伍,但并沒有建立。
其四,若以科技事業(yè)的某一方面來衡量,井岡山時期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有待完善。如科技傳播方面,傳播途徑相對單一,主要是通過實踐傳授和集中教育的形式進行,沒有通過組建宣傳隊、書寫標語、創(chuàng)辦報刊、編寫書籍等多種形式展開廣泛宣傳;傳播對象相對狹窄,主要面向“體制內”的受眾,在各個生產(chǎn)和服務單位、教導隊和紅軍大學中進行,沒有面對社會大眾。
其五,若以某一項科技應用來衡量,井岡山時期并非事事最早。如同井岡山時期的1929年夏,李強和張沈川在上海組裝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第一架收報機;同年冬,組裝了收發(fā)報機,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注]張沈川:《難忘的回憶——關于我黨早期地下無線電通信的創(chuàng)建》,《蘇區(qū)郵電史料匯編》下,第136、138-139頁。比井岡山時期更早的1925年2月,在李大釗領導下,陳喬年等在北京開辦了昌華印刷廠,職工35人。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第一所秘密印刷機構。[注]平雨:《中國共產(chǎn)黨最早的印刷機構》,《出版參考》1997年第10期,第10頁。
如果我們將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科技事業(yè),劃分為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機構、科技應用、科研成果、科技隊伍、科技教育、科技傳播、科技社團等8個方面內容的話,那么,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時期,井岡山軍民除沒有成立科技社團外,在其他7個方面都已經(jīng)開創(chuàng)了事業(yè),其中許多科技政策、科研機構、科技應用、科研成果、科技隊伍、科技教育、科技傳播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都是首次,有了從無到有且實實在在的成績。因此,從首創(chuàng)和系統(tǒng)性兩個角度上說,筆者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科技事業(yè)系統(tǒng)初創(chuàng)于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