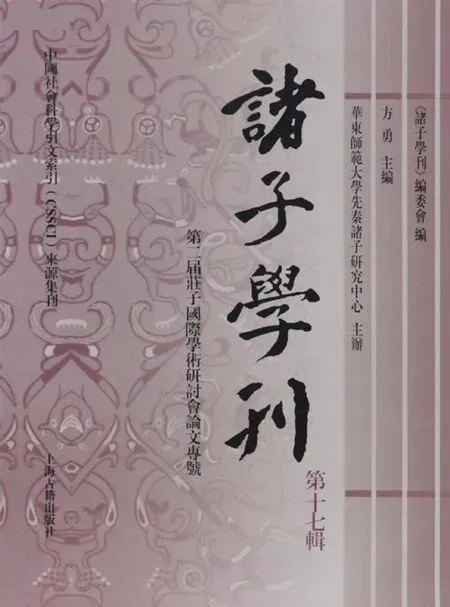丘處機西遊詩對《莊子》理念的闡發(fā)
賈學鴻
內(nèi)容提要 丘處機前往中亞所作的西遊詩,帶有明顯的暢《莊》傾向。早在磻溪修煉期間,丘處機所作的詞就對《莊子》的理念多有闡發(fā),並且身體力行。丘處機帶著深厚的《莊》學積澱踏上漫漫的西行征途,沿路的言志抒情詩往往成爲闡發(fā)《莊子》理念的載體。他把萬里跋涉作爲窮觀六合、飛騰八表的實際演練,把清靜無爲作爲修煉的歸宿。西行詩對民風習俗的展示,聚焦于大樸未散的上古天真,與《莊子》的至德之世一脈相通。丘處機西行詩以贈答、做法事、題壁等方式在沿途傳播,受衆(zhòng)來自多個階層。
[關(guān)鍵詞] 丘處機 西行詩 《莊子》理念 傳播
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丘處機應(yīng)成吉思汗的徵召前往西域,在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抵達成吉思汗行營所在的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雙方進行多次交談。蒙古太祖十九年(1224),丘處機隨行弟子李志常返回燕京撰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對於沿途自然景觀、風土人情等作了詳細的敘述,還收録丘處機在往返途中所作的七十首詩詞。
《長春真人西遊記》的重要價值長期未能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直到清康熙朝(1736—1795)後期,錢大昕在蘇州玄妙觀閲讀《道藏》,才開始對它的重要價值加以肯定。清末民初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爲該書作注,並且予以很高的評價。這部書的重要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長春真人西遊記》是研究丘處機及全真道的重要著述,也是我國十三世紀上葉一部重要的中西交通史文獻,此書可與晉代法顯的《佛國記》、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媲美,對研究元史、西域史、地理、民俗等均有參考價值。在世界中世紀的地理遊記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國外有俄、法、英諸種語種譯本。(1)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二),知識出版社(滬版)1994年版,第218頁。
丘處機西行走的是絲綢之路北路,《長春真人西遊記》對於研究中世紀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有多方面參考價值。丘處機是全真道北七子之一,被龍門派尊奉爲師祖。全真道屬於道教宗派,與先秦道家存在密切關(guān)聯(lián)。《莊子》是先秦道家學派的主要經(jīng)典之一,因此,研究《長春真人西遊記》的主角丘處機與《莊子》的關(guān)聯(lián),從學理上講應(yīng)該具有可行性。
一、 《磻溪詞》反映的《莊子》理念
丘處機有《磻溪詞》傳世,收録詞作百餘篇。磻溪,水名,一名璜河,在今陝西寶雞市東南,是丘處機隱居修煉的地方。元代道士李道謙撰輯的《七真年譜》有如下記載: 大定十四年,“長春西入磻溪”;大定二十年,“長春真人自磻溪遷居隴州龍門山”(2)胡道靜、陳蓮笙、陳耀庭選輯《道藏要籍選刊》(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64頁。。丘處機拜王重陽爲師,是王門七大弟子之一。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王重陽病逝。大定十四年(1174)到大定二十年(1180),丘處機在磻溪隱居修煉,時間長達六年之久。他的詞集稱爲《磻溪詞》,很大程度是爲了紀念這段難忘的人生經(jīng)歷,所收録的詞均作於西行之前,是考察丘處機早期思想的可靠文獻。
《磻溪詞》中反覆出現(xiàn)的一系列術(shù)語,最初都見於《莊子》,如逍遙、物化、忘形等。還有忘機,則是由《莊子》的否定機心、機事化生而來。從所用名詞術(shù)語進行判斷,丘處機所寫的詞確實受到《莊子》一書的影響,這是宏觀審視所得出的初步結(jié)論。如果進一步深入到丘處機具體詞作所運用的典故,會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更多的關(guān)聯(lián)。
《磻溪詞》首載《無俗念》詞十二首,“景金本《磻溪詞》注云:‘十二首亦名《酹江月》,居磻溪。’”(3)唐珪璋編《全金元詞》(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52頁。這十二首詞是丘處機隱居磻溪時所作,首篇即以《居磻溪》爲題。其中第三首《贊師》,上闋有“化鵬超度能幾”之語。所謂的化鵬,顯然是運用《莊子·逍遙遊》開頭一段鯤化爲鵬的典故。《沁園春·心通》開頭寫道:“大智閑閑,放蕩無拘,任其自然。”“大智閑閑”,語出《莊子·齊物論》。丘處機在運用這句話時,對它賦予新的內(nèi)涵,與《齊物論》中的含義相反。《磻溪詞》有《報師恩》五首,詞牌本名《瑞鷓鴣》。其中第一首題爲《削髮留髭》,下闋如下:
改頭換面人難悟,走骨行屍我不憂。得意忘形還樸去,從教人笑不風流。(4)同上,第468頁。
這裏所説的“得意忘形”,是綜合《莊子》兩篇文章用語而來。《外物》稱:“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成玄英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5)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46頁。《外物》稱“得意而忘言”,指的是已經(jīng)修煉入道,丘處機所説的“得意”,也是體悟道性之義。忘形,用的是《莊子·德充符》中典故:“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郭象注:“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6)同上,第218頁。從《德充符》原文本義到郭象注,強調(diào)體悟道性必須忘形。丘處機所説的忘形,實是源自《德充符》的上述論斷。
《磻溪詞》收録的《滿庭芳·述懷》上闋如下:
漂泊形骸,顛狂蹤跡,狀同不繫之舟。逍遙終日,食飽恣遨遊。任使高官重祿,金魚袋,肥馬輕裘。爭知道,莊周夢蝶,蝴蝶夢莊周。(7)唐珪璋編《全金元詞》(上),第458頁。
結(jié)尾所涉莊周夢蝴蝶的典故,出自《莊子·齊物論》。至於開頭一段話語,則是源自《莊子·列禦寇》: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8)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第1040頁。
《列禦寇》這段論述用的是韻語,押幽部尤韻。丘處機的《滿庭芳·述懷》開頭一段,對於《列禦寇》上述話語不但師其意,而且?guī)熎湓~,也是用尤韻,二者的源流關(guān)係十分明顯。丘處機的《磻溪詞》絶大多數(shù)寫於隱居磻溪期間,在人生的這個階段,他對《莊子》一書已經(jīng)了然於心,詞作中反覆運用這部道家著作的典故,用以抒發(fā)自己的隱逸情懷。不僅如此,他還身體力行,踐履《莊子》一書所表達的人生理念。元代道士秦志安所編《金蓮正宗記》卷四對於丘處機隱居磻溪的情況有如下記載:
一旦祖師赴蓬萊之約,遺物離人而入於天矣,大葬禮畢,西遊鳳翔,乞食于磻溪太公垂釣之所。戰(zhàn)睡魔,除雜念,前後七載,脅不占席。一簑一笠,雖寒暑不變也,人呼爲簑衣先生。妙合虛無,理通玄奧。(9)胡道靜、陳蓮笙、陳耀庭選輯《道藏要籍選刊》(六),第652頁。
丘處機隱居磻溪期間以乞討爲生,放浪形骸,不修邊幅,前面援引的《報師恩》以《削髮留髭》爲題,是對自我形象的真實寫照。丘處機是在公元1174年到1180年期間隱居磻溪,下距遠行西游長達四十年。也就是説,青年時期的丘處機,已經(jīng)對《莊子》一書心領(lǐng)神會,並且身體力行,是虔誠的莊門後學。
二、 西遊詩言情抒志的暢《莊》傾向
丘處機是帶著早年深厚的《莊子》積澱西行的,在他沿途創(chuàng)作的詩歌中,不時可以見到《莊子》這部道家經(jīng)典歷史折射所留下的投影。
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丘處機率弟子十八人從萊州(治所在今山東掖縣)出發(fā),經(jīng)濰陽(今山東濰縣)、青州(今山東益都)、常山(今河北正定),到達燕京(今北京)。然後出居庸關(guān),至德興(今河北涿鹿)龍陽觀度夏。八月初抵宣德州(今河北宣化)朝元觀講道,然後又返回龍陽觀過冬。這個階段是丘處機西行的準備時期,在此期間所寫的詩,反映出他遠行前真實的心理狀態(tài)。
丘處機在燕京停留時入住玉虛觀,與諸大夫多有唱合。他在德興龍陽觀度夏期間以詩寄燕京諸大夫:
登真何在泛靈槎,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yún)峰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遊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10)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頁。
首句用的是《博物志》卷十《雜説下》的典故,傳説天河與海相通,每年八月有浮槎往來其間。一位海島居民乘桴槎前去,見到天上牛郎織女所在之處(11)張華撰、范寧校正《博物志校正》,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1頁。。丘處機則認爲,修煉入道不必借助傳説中靈異的木筏前往天界,而是隨處都有令人歡樂的對象。天堂的雲(yún)峰、下界的海市蜃樓同樣賞心悅目。詩中提到神遊八極,正是《莊子》書中反覆出現(xiàn)的得道者的形象。《逍遙游》中的藐姑射神人“乘雲(yún)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應(yīng)帝王》篇的無名人“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xiāng)”。《刻意》篇則把養(yǎng)神之道歸結(jié)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所有這些,正是丘處機詩中“神遊八極”的歷史折射。神遊八極是修煉入道的方式,所以下句稱“道合三清路不差”。三清,道教所尊崇的三位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道君、太清太上老君。或稱“一氣化三清”,三清是元始天尊的化身。丘處機詩所説的“神遊八極”,爲的是引出他的此次西行,帶有起興的作用。結(jié)尾兩句“弱水縱過三千萬,騰身即刻到仙家”,暗指即將開始的西行遠征。弱水,傳説中環(huán)繞昆侖神境的密度很小的水,連羽毛都無法浮起。騰身躍過弱水,暗指到達遙遠的西域,即當時成吉思汗行營所在的西亞。這首詩把西行遠征説成是入道成仙的過程,其中絲毫見不到對此次西行的畏懼感,而是指向?qū)Φ缊鱿删车淖非蟆?/p>
元太祖十六年(1221)二月八日,丘處機一行從宣德州朝元觀啓程,正式開始西行的漫漫征途。“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遠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絶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12)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5、6頁。野狐嶺是中原和塞外的天然分界,南北景色迥異。面對如此鮮明的對比,丘處機卻泰然處之,從容淡定,沒有因爲南北自然生態(tài)的巨大反差而出現(xiàn)心靈的波動。“三月朔,出沙阤,至魚兒濼,始有人煙,多以耕釣爲業(yè)。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
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阤三月尚凝冰。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13)同上,第6頁。
沙阤,指沙漠。魚兒濼,指今內(nèi)蒙古東南的達里諾湖。丘處機一行出發(fā)後歷經(jīng)杳無人煙的鹽鹼地、大沙漠,到達魚兒濼已是春天三月,但是氣溫依然很低,凝冰未曾消融。丘處機詩中提到的若士、盧敖,指的是同一傳説中的兩個人物,具體記載見於《淮南子·道應(yīng)訓》: 盧敖游于北海,遇見一位奇人,稱他爲若士。盧敖與他對話,自稱已經(jīng)“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窺”,想與若士結(jié)爲朋友。若士則云:“若我南遊乎罔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xiāng),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蒙之光。”他已經(jīng)遊遍整個大地,走到四方最邊遠的區(qū)域。若士又稱:“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留。”高誘注:“九垓,九天之外。”(14)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08、409頁。盧敖注視著若士的騰空遠遊,並且慨歎:“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丘處機詩中所説的“更尋若士爲黃鵠”,意謂自己要像若士那樣遠遊四方,上天入地。結(jié)尾兩句“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這説要像盧敖那樣自我審視,找到差距,最後樹立起窮觀六合的崇高志向。丘處機在旅途中歷經(jīng)艱難困苦,可是,他並沒有絲毫的沮喪,而是把西行征程比作若士的窮觀六合,鼓勵自己實現(xiàn)這種理想。《淮南子·道應(yīng)訓》的這則寓言結(jié)尾引《莊子·逍遙遊》的“小年不及大年”三句話作總結(jié),宣揚的是《莊子》的理念,就此而論,丘處機這首詩是間接地繼承《莊子》的游四海、出六極的神遊理念,把征途上遇到的艱難險阻置之度外。
丘處機這首詩提到“要識修鯤化大鵬”,鯤化爲鵬的寓言見於《莊子·逍遙遊》,寄托的是生命一體、物物相生的理念。丘處機運用這個典故,則是賦予它新的內(nèi)涵。《磻溪詞》收録的《無欲念·贊師》全文如下:
漫漫苦海,似東溟、深闊無邊無底。逯逯群生顛倒競,還若遊魚爭戲。巨浪浮沉,洪波出沒,嗜欲如癡醉。漂淪無限,化鵬超度能幾。
唯有當日重陽,惺惺了,獨有沖天志。學《易》年高心大悟,掣斷浮華韁繫。十載丹成,一時功就,脫殼成蟬蛻。從師別後,更誰風範相繼。(15)唐珪璋編《全金元詞》(上),第453頁。
丘處機把鯤化爲鵬喻爲人生的超度蟬蛻,猶如浴火重生,把人生提升到至高的境界。沒有實現(xiàn)這種以形相禪之前,人如同魚,只能在水中遊動。一旦實現(xiàn)這種嬗變而成爲鵬,正如《逍遙遊》所描寫的那樣:“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絶雲(yún)氣,負青天,然後圖南。”這正是丘處機所追求的,屬於最上乘的“六合窮觀”。丘處機是把西行遠征視爲人生超度蟬蛻的過程,他要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把旅途變成人生修煉的道場。
丘處機一行經(jīng)長松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nèi)杭愛山)抵達金山(今阿爾泰山)東側(cè)的科布多附近,暫時駐留在那裏。“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面對惡劣的氣候條件,丘處機作詩自歎:
某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嶽多遊遍,八表飛騰後入神。(16)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9頁。
首句“某也東西南北人”,丘處機用來描述自己的經(jīng)歷。前四句詩屬於寫實,似乎有幾分蒼涼。可是,從第五句開始,筆鋒陡轉(zhuǎn),格調(diào)大變。“未死且令觀世界”,意謂在自己離開人世之前,成吉思汗的徵召令他得以觀看世界,開闊視野。“殘生無分樂天真”,殘生,指餘生、殘留的歲月,時間有限之義。無分,沒有料想到,出乎意料。分,指料想。這兩句是説時間有限的餘生未曾料想到還得以遠游觀世,因天真而快樂。最後兩句是以積極樂觀的心態(tài)看待此次西遊,認爲這是實現(xiàn)飛騰八表進入神仙境界的途徑。丘處機面對惡劣的氣候和自己已是高齡之年的現(xiàn)實,抒發(fā)純?nèi)翁煺娴目鞓罚磉_八表飛騰的理想,是以苦爲樂,化憂爲喜,這正是《莊子》一書有些寓言所表現(xiàn)的黑色幽默。《大宗師》篇記載,子輿病重,在井口鑒照已經(jīng)變形的軀體,讚揚造物者的偉大,表示自己要安時處順。《至樂》篇記載,支離叔“柳生其左肘”,但他坦然面對,以“死生爲晝夜”。丘處機西行詩所表現(xiàn)的超脫、曠達,與《莊子》的這些寓言一脈相承,息息相通。
丘處機一行經(jīng)今新疆輪臺至回紇昌八剌城,從那裏向北翻越天山。翻越天山之前,“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丘處機作詩一首:
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yún)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17)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11頁。
當時正值八月、九月之交,但寒冷如冬,故曰“三冬”。這首詩前邊四句屬於紀實,渲染夜晚的黑暗及風雨交加的場景,道出了所處環(huán)境的惡劣。後四句則是進行轉(zhuǎn)折,表達自己的心志。風雨交加,漆黑寂寥,卻稱“氣候韶”,韶,美好之義,放在這裏似乎不可思議。而在丘處機看來,寒冷似冬的秋天風雨交加,樹葉飄落,合乎當?shù)氐淖匀灰?guī)律,人們應(yīng)當加以認同、順應(yīng)。秋天是草木凋零的季節(jié),蓬草折斷,隨風飄遊,丘處機認爲,人也應(yīng)當像蓬草那樣,無心而純?nèi)巫匀弧K^的“全身都放下”,指的是身心俱寂,沒有任何慾念,這正是《莊子》書中反覆提到的自我拋舍,如《齊物論》稱“吾喪我”,《大宗師》謂之“坐忘”。
丘處機把西行旅途作爲修煉的道場,所要實現(xiàn)的理想是六合窮觀,八表飛騰,道合三清,進入神境仙鄉(xiāng)。所采用的修煉方式則是澄心息慮,清靜無爲。對此,當代學者已有如下論述:
丘處機的修煉思想以斷情絶欲爲修道的前提,以清靜無爲爲修煉要旨。認爲“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18)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二),第334頁。
丘處機早年的修煉,以隱居潛修爲主。王重陽去世後他在磻溪隱居六年,又到隴州龍門山潛修七年。後來先後入主山東棲霞太虛觀、掖縣昊天觀。丘處機西行之前的經(jīng)歷,以定居修煉傳教爲主。此次應(yīng)詔前往西域,是對他以往修煉功夫的嚴峻考驗。丘處機從容面對,安然淡定,經(jīng)受住了此番考驗,先前修煉所積澱的《莊子》理念,在此期間發(fā)揮出很大的作用。
趙九古是丘處機西行的隨從弟子之一,不幸中途病逝。逝世前幾天對人説道:
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19)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13頁。
丘處機秉持的是安時處順、隨遇而安的人生理念,這正是《莊子》一書反覆闡述的道理。《德充符》認爲事之變、命之行,“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就會“與物爲春”,保持心靈的平和淡定,這就是所謂的“才全”(20)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第212頁。。對於這種理念,《田子方》闡述得更加充分: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而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21)同上,第714頁。
《莊子》哲學給人以生存智慧,使其具有應(yīng)變能力,能夠適應(yīng)身邊環(huán)境的變化。丘處機西行秉持的正是《莊子》闡發(fā)的人生理念,因此,他把西行的漫漫長途變成修煉心性的道場,把萬里跋涉視爲窮觀六合、飛騰八表的實際演練,是通向神境仙鄉(xiāng)的途徑。
丘處機一行到達邪米思幹城(或譯爲尋思幹,今撒馬爾罕),距離成吉思汗的行營已經(jīng)不是很遙遠。丘處機在此駐留期間,寫了多首詩詞,其中有兩首《鳳棲梧》詞書寫在所居宮殿的牆壁上。第一首稱:“四海八荒唯獨步”、“九天齊上三清路”,這是把此次西游視爲向三清道境的飛升。第二首寫道:“死去生來生復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凈超於彼。”(22)唐珪璋編《全金元詞》(上),第478頁。這幾句可以説是對自己西行旅途心性修煉所作的總結(jié),“無心休歇地”,正是《莊子》所説的安時而處順,外化內(nèi)不化。
三、 西遊詩的民俗畫面與《莊子》描述的至德之世
丘處機西遊,親眼目睹、親身感受到沿途許多有異於中土的民風習俗,並且寫入詩中。這類題材的作品,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與《莊子》的關(guān)聯(lián)。
丘處機一行離開燕京,過居庸關(guān),在德興龍陽觀度夏。“觀之東數(shù)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愛,師往來其間。”並且寫詩以紀實:
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yún)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皋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堤陰讓坐。)溪邊浴罷林間坐,散發(fā)披襟暢道情。(23)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3、4頁。
“午後迎風背日行”,“背”字缺,據(jù)《道藏要籍選刊》本補。詩中讚揚“東皋遊戲俗無爭”,東皋,用的是唐初文人王績的典故。王績,字無功,生活在隋唐之際。他在唐初棄官隱居著書,號東皋子。東皋,泛指田野和高地,後來代指從事農(nóng)耕。李志常所作的注指出,丘處機的這句詩指的是龍陽觀一帶居民能夠謙讓,沒有紛爭。龍陽觀所在的今河北涿鹿一帶,和壩上地區(qū)相距很近,那裏民風淳樸,爲在大堤乘涼的丘處機等人讓坐,這使得丘處機深有感慨。這種淳樸的民風,正是《莊子》一書反覆讚揚的至德之世的大樸未散的民性。《天地》篇寫道: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對於這段論述,宋人林希逸有如下解釋:
“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不以爲恩也。(24)林希逸著、周啓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04頁。
林氏所作的解釋符合《天道》原文本義。在《天道》作者的觀念中,遠古至德之世民性樸素,雖然沒有仁義忠信之名,所做所爲卻合乎仁義忠信。人與人之間友好相處,沒有所謂恩賜的觀念。至於稱至德之世“民如野鹿”,也是取其群體內(nèi)部和睦融洽的屬性而言。鹿是群居動物,而且比較溫馴,因此,《詩經(jīng)·小雅·鹿鳴》以“呦呦鹿鳴”起興,取其群體內(nèi)部相依相伴之義。丘處機從龍陽觀當?shù)鼐用衲茄Y感受到謙讓無爭的美德,這與《莊子》許多篇對至德之世淳樸民風的歌頌有相通之處。
丘處機一行越過野狐嶺之後,進入人煙稀少的荒涼區(qū)域。“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丘垤醎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逶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shù)千里,亦無大山。”蓋里泊,指今內(nèi)蒙境內(nèi)伊克勒湖。對於這段行程,丘處機的詩作了紀實:
坡陀折疊路彎環(huán),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jīng)年時有馬回環(huán)。地無木植唯荒草,天産丘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顔。(25)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6頁。
詩中所展示的自然生態(tài)非常惡劣,交通閉塞,人的物質(zhì)生活資料也很匱乏。可是,當?shù)鼐用駞s自得其樂,人的幸福指數(shù)與客觀環(huán)境形成巨大的反差。詩中所描寫的物類事象,與《莊子》書中對至德之世的讚美有相似之處。《胠篋》寫道: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當是時也,民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成玄英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26)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第358頁。成氏所作的解釋簡明確切,指出了至德之世充滿歡樂的原因。《胠篋》對至德之世所作的描述,取自傳世本《老子》八十章對小國寡民社會所作的説明。關(guān)於其中的“甘其食”以下四句,河上公作了這樣的解説:
甘其疏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質(zhì)樸之俗,不轉(zhuǎn)移也。(27)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04頁。
河上公把《老子》八十章所提到的食、服、居,分別釋爲疏食、惡衣、茅茨,合乎原文所藴含的深層意義。丘處機詩中所提到的乳酪、皮裘、氈帳,也屬於疏食、惡衣、茅茨之類,是很簡陋的衣、食、住的物質(zhì)條件。那裏的土著居民對此“亦開顔”,同樣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丘處機這首詩對當?shù)赝林用竦淖撁溃梢詮摹独献印泛汀肚f子》那裏找到文化源頭。
丘處機一行路過蓋里泊之後,經(jīng)漁兒濼,抵達貝加爾湖以北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四弟)帳下。又西行經(jīng)過呼倫湖,翻越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以南的高山,前往長松嶺。到達長松嶺之前,所經(jīng)區(qū)域土著居民的習俗引起丘處機一行的高度關(guān)注。那裏的居民以放牧狩獵爲業(yè),以黑車白帳爲家,以皮革爲衣,以肉酪爲食。男性結(jié)髮垂耳,女性的樺皮冠則高達二尺,並且飾以布帛,冠頂做鵝鴨形。“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對此,丘處機用詩作了敘述:
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jié)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28)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7頁。
這首詩對於當?shù)赝林拿耧L習俗擇其主要方面作了描述,並且表現(xiàn)出認同感。“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當?shù)匾阅翗I(yè)爲主,丘處機認爲這是造物主的安排,當?shù)鼐用袷琼槕?yīng)這種安排。“飲血茹毛同上古”,是説那裏保持上古的原始遺風,用的是《禮記·禮運》的典故:“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陳澔注:“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並食之也。”(29)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88頁。茹毛飲血,指飲食上的原始形態(tài),丘處機詩中取的是這種含義。《禮記·禮運》緊接上段文字之後寫道:“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孫希旦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上古之居處、飲食、被服,過於樸陋,而不宜於人。後聖通其變,而相生相養(yǎng)之道乃盡。(30)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88頁。
孫氏所闡釋的是儒家的歷史進化觀。丘處機雖然是道教全真道一代宗師,但是,他認爲“三教同源一理”,“故兼修三教經(jīng)書”(31)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二),第215頁。。他對《禮記·禮運》的上述記載應(yīng)該是熟悉的,因此他稱當?shù)赝林用瘛帮嬔忝瞎拧保瑧?yīng)是用《禮運》的典故。中土經(jīng)歷了由上古樸陋的生存方式到“後聖有作”的演變,丘處機認爲當?shù)赝林A羯瞎胚z風,沒有經(jīng)歷中土那種歷史演變,故詩中稱“聖賢不得垂文化”,意謂那裏沒有實現(xiàn)“後聖有作”。
那麼,丘處機對當?shù)赝林3稚瞎胚z風所持的態(tài)度如何呢?詩的結(jié)尾作了回答——“歷代縱橫只自由”,那裏的人們世世代代不受拘束,只是自由自在而已。縱橫,指放浪形骸,不受拘束,而這正是全真道所欣賞的,丘處機早年在磻溪修煉時就是如此。這從前面援引的《金蓮正宗記》卷四的記載可見一斑。
丘處機從漠北土著的民風習俗中見到原始遺風,認爲它給人帶來的是自由。《莊子》一書對遠古至德之世所作的描述,同樣讚揚那種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tài)。《馬蹄》寫道:“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對此,成玄英疏寫道:
夫行道之時,無爲之世,心絶緣慮,安居而無爲;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32)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第341頁。
成玄英是西華道士,所作的講疏頗爲確切。他把未受禮樂仁義沾溉的原始先民概括爲心絶緣慮,率性而動。丘處機在漠北所見到的土著居民“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同樣是率性而動,天真自由,與上述《馬蹄》的描寫可以相互印證。丘處機從保持遠古遺風的漠北土著居民那裏,見到了純?nèi)翁煨缘淖杂蔂顟B(tài),這是《莊子》一書反覆讚美的對象,也是丘處機本人追求並付諸實踐的人生境界。丘處機詩中稱“聖賢不得垂文化”,所謂的文化,指的是以文而化之,暗用《周易·賁·彖》的如下典故:“剛?cè)峤诲e,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高亨先生注曰:“人文指社會之制度文化教育等。……社會之制度文化教育皆在使人有所止。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33)高亨著《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98年版,第172頁。丘處機所説的“聖賢不得垂文化”,意謂禮樂仁義等還沒有施加於漠北土著,因此他們自由自在,不受約束。對此,丘處機並無惋惜,而是感到慶幸,這與《莊子》一書對禮樂仁義的批判也是合拍的。
丘處機西行詩對沿途民風習俗所作的展示,並不是純客觀地紀實,而是寄托他崇尚天性自由的人生追求,是在中古絲綢之路上感受到大樸未散的天真可愛,仿佛回到《莊子》多次讚美的至德之世。
四、 西行詩的暢《莊》背景及在沿途的傳播
丘處機是在七十三歲高齡踏上西行的漫漫長途,儘管有弟子隨行,官軍保駕,路上還是歷經(jīng)險難,備嘗艱辛。當然,途中偶爾也有條件較好的休憩場所,在那裏進行休閒。總體上看,無論是遭遇艱險,還是輕鬆休閒,《莊子》一書的思想理念,經(jīng)常與他形影相伴,或形諸吟詩,或流露於話語,不時地顯示出來。
丘處機一行到達尋思幹,入住算端所建的新宮。先前該國太師曾經(jīng)住進新宮,因懼怕盜賊而遷到別處。丘處機入住之後感歎:“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34)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14頁。《莊子》首篇是《逍遙遊》,其他篇目也多次把逍遙作爲理想的人生境界加以追求。丘處機面臨危險仍然強調(diào)任運逍遙、超脫於利害生死之外,這正是《莊子》一書人生哲學理念的核心。
丘處機的隨行弟子趙九古中途病逝,埋葬在當?shù)亍7祷赝局薪?jīng)過這裏,“衆(zhòng)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皆假,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zhòng)議乃息”。丘處機參破生死,並且超越狐死首丘的傳統(tǒng)觀念,沒有把趙九古的骨骸帶回中土,而是留在他病逝的原地。丘處機所説的四大,用的是佛教術(shù)語。古印度有地、水、火、風爲構(gòu)成一切物質(zhì)四元素之説,佛教認爲人的形體也是這四種元素構(gòu)成,故以四大用作人身的代稱。“四大皆假”,意謂構(gòu)成人的形體的元素不過是生命的憑藉,它的存在是暫時性的。《莊子·大宗師》稱得道者把人的肉體生命視爲“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同樣用“假”字加以概括。林希逸稱:“假於異物,便是《圓覺經(jīng)》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35)林希逸著、周啓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第117頁。林希逸往往援佛入莊,不過,他對《大宗師》生命理念的繼承和闡發(fā),所用的“假”字留下《莊子》一書的歷史投影。
丘處機一行在尋思幹停留的時間較長,將近四個月。在此期間生活比較安閒,參加多次聚會,創(chuàng)作一系列詩詞。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二月,“時僚屬請師復游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未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丘處機是在良辰美景、遊興大發(fā)之際寫詩贈給同遊者。第一首結(jié)尾兩句是:“未能絶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第二首尾聯(lián)稱:“竊念世間酬景短,何如天外飲長春。”(36)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15頁。在遊興正酣時刻所寫的兩首詩,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然無爲,是“天外飲長春”的道境仙鄉(xiāng)。《莊子·天運》稱:“古之真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逍遙,無爲也。”借道、托宿於仁、義,表面上屬於有爲;遊逍遙之虛,則屬於無爲。丘處機所説的“且向無爲樂有爲”,與《天運》的這段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把道境在時間上的無限性與人間事象的短暫性加以對比,更是《莊子》常用的表達方式。
丘處機把漫漫的西行旅途,變成他進行修煉的道場,所創(chuàng)作的許多詩篇,成爲闡發(fā)《莊子》理念的載體。丘處機所作的這些詩不是自娛自樂,秘而不宣,而是用多種方式加以傳播。由此而言,西行旅途又成爲傳播《莊子》理念的空間。這類詩的傳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打醮,即設(shè)壇做法事。“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丘處機這次法事活動爲衆(zhòng)人作頌一首:
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37)同上,第5頁。
這首頌作於1221年正月十五,地點是宣德州的朝陽觀。這首頌把人的肉身視爲是非煩惱的根源,佛教意味頗濃。但是,它所闡發(fā)的理念亦與《莊子》有相通之處。《大宗師》稱得道之人,“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潰癰”。林希逸解説如下:“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之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38)林希逸著、周啓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第117頁。丘處機此次登壇做法事,所寫的頌是開導教徒超越形體的局限性,得到精神解脫,這與上引《大宗師》的論述在理念上一脈相通,客觀上起到傳播《莊子》生命理念的效果。丘處機西行走出中土之後,再也沒有道觀可做法事,因此,這種傳播方式?jīng)]有在旅途上持續(xù)下去。
二是送行、流覽之際以詩示衆(zhòng)。1220年丘處機從朝元觀前往龍陽觀,“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zhòng)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回生死苦難甘。’”(39)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5頁。這是勸導送別的道友,要超越生離死別的傷感,否則,面對生死很難坦然淡定。《莊子》一書反覆強調(diào)的,正是對生死的超越,《大宗師》篇後部的幾個寓言故事,都是圍繞這個中心展開。丘處機在尋思幹停留期間作詩頗多,主要是兩次春遊所作。第一次春遊的場面是這樣的:“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之疏圃。憇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40)李志常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第15頁。前引作於尋思幹的兩首詩,就是在談玄論道的氛圍中寫出來的,其中有的詩句用於闡發(fā)《莊子》的生命理念和人生理想,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三是牆壁題詩。丘處機在龍陽觀過冬期間,“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以殿西廡云”。所題詩如下:
杖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沉沉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41)同上,第5頁。
這首詩題寫在龍巖寺的西廊,廡,指堂下四周的廊屋。詩人“神游八極騰虛明”,已經(jīng)進入道境。通過山間晝夜陰晴的變化,暗示自然造化的微妙神秘,無法把它的本來面目真實地展現(xiàn)出來,體現(xiàn)的還是《莊子》對自然造化的讚美和崇拜,正如《大宗師》所説的“覆載天地,刻彫衆(zhòng)形而不爲巧”。如前所述,丘處機在尋思幹停留期間,“遂書《鳳棲梧》二首於壁”,也屬於暢《莊》之作,體現(xiàn)的是安時處順、外化內(nèi)不化的情懷。
丘處機的西行詩以多種方式在沿途傳播,它的受衆(zhòng)也來自不同的階層,最直接的受衆(zhòng)是丘處機的隨行人員,包括他的弟子和護送官員。他們與丘處機朝夕相處,這些詩他們絶大多數(shù)都能接觸到。第二類受衆(zhòng)是參加丘處機法事活動的道教信徒,丘處機在打醮之後爲衆(zhòng)人作頌一首,參加法會的人員是這首頌的接受者。第三類受衆(zhòng)是沿途接待丘處機的人員。丘處機在燕京玉虛觀曾經(jīng)與多人唱和,到龍陽觀度假又對他們以詩相贈。在尋思幹停留期間,“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游郭西,宣使洎諸宮載蒲萄酒以從”(42)同上,第15頁。。丘處機在尋思幹的兩次春遊都有詩,當?shù)赜行┕賳T參與兩次春遊,他們是丘處機當場所作詩的受衆(zhòng)。至於丘處機的題壁詩,有的是在德興龍陽觀,有的遠在中亞尋思幹的宮殿,日後來到這兩處的人們,很多人會成爲題壁詩的受衆(zhòng)。
《莊子》這部道家經(jīng)典最初寫作是在戰(zhàn)國中期,下距丘處機所在的金元之際已經(jīng)一千五百年左右。通過梳理丘處機西行詩對《莊子》理念的繼承、闡發(fā),可以看出《莊子》對歷史煙雲(yún)的穿透力,雖然歷經(jīng)一千多年而依然在道教全真派宗師那裏煥發(fā)生機。丘處機西行詩的暢《莊》傾向,則在空間維度上勾勒出《莊子》西傳的軌跡。這是中世紀絲綢之路一道亮麗的風景,也是《莊子》研究可供延伸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