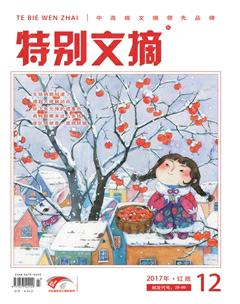上海女人的細節(jié)密碼
李大偉
相比男人,在上海的女人越來越國際化。她們很少去老城隍廟,更喜歡去思南路,坐在街沿露天吧,臺布綠色的,圍欄木柵的,一杯咖啡、兩塊曲奇,三五閨蜜,瞎七搭八。開口漢語,難免英語,更時髦的說法語,以示高雅、小眾、稀缺,企圖超凡脫俗,立志擺脫大眾。
上海女人越來越小資化。什么叫小資?“一份工作、四季衣裳、八面玲瓏、十二分焦慮”。特立獨行是她們的行為特點。大家看電影了,人家看話劇了;大家英語了,人家學法語了;大家去歐洲了,人家去非洲了;大家有條件住星級賓館了,人家住民宿了;大家喝早茶了,人家喝下午茶了。什么是溫柔?嗲唄;什么是幽默?貧唄;什么是仗義?傻唄。什么是小資?裝唄,比如草庵里彈古箏,書房里穿尼褂。總之,立異為高,與眾不同。
上海是國際化的大都市,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移居客,就比例而言,追求浮華的小資越來越多,講究經(jīng)濟實惠的上海女人越來越少;會說外語的女人越來越多,會說上海話的女人越來越少。小資是知識的產(chǎn)物,是西洋的產(chǎn)物,不是上海的產(chǎn)物。上海女人是阿慶嫂,講究經(jīng)濟實惠。但數(shù)量決定質量,上海女人的成分被龐大的小資數(shù)量稀釋,于是本地特色被異化了。在全國人民眼里,上海女人被簡略為一個字:“嗲”;壓下秤砣,翹起另一端的“作”。嗲與作:一根線上的兩個螞蚱,上海女人被嚴重歪曲了。
上海是個工業(yè)城市、經(jīng)濟城市,生活成本高,夫妻雙職工才能撐起一個家庭的體面。所以,上海女人絕大部分既是工人、店員、職員等工薪階層的家子婆,自己又往往是勞動人民的一員,“勤快會做”是基本面。早飯是泡飯,急急忙忙開水泡軟隔夜留的干飯,飯勺撳散結塊的飯團,“豁落豁落”,三口兩口下肚,然后上班。下班后急急忙忙趕回家,淘米汏菜。上海女人的綽號:馬大嫂(諧音:買、汏、燒)。
上海女人會“做”不會“作”,她們的口頭禪:“恨不得兩只腳掮在肩上。”當手派用場,尤其在星期天,這句口頭禪使用頻率更高。做孩子的知道,大人忙的時候,小孩識相點,否則“竹筍烤肉片”。被子自己“絎”,衣服自己洗,西褲自己熨,從里到外都是自己做。家,不是按揭買來的,像鳥兒銜草筑巢,是一天天做出來的。上海女人,來不及“做”,哪有空“作”!“會做伐?”是評價新娘子的首選標準。“好看伐”則是評價姨太太的。上海女人有句勵志的口頭禪:“好看又不能當飯吃。”在從前,即便姨太太,也要燒得一手好小菜,有客來訪,拿得出手。
過去對上海女人的最高評價:阿慶嫂!現(xiàn)在的女人,不雇鐘點工的叫“勞”婆,雇傭鐘點工的叫兼職太太,雇傭住家保姆的叫全職太太,是嫁得好的榜樣。升格為“搪瓷七廠廠長”——蕩在家里、住在家里、吃在家里。瓷與住、七與吃,在上海話里,發(fā)同一個音。懶女人就是享福人!昏過去。
過去,知識女性像勞動人民:鄙視坐而論道,講究“起而行”;現(xiàn)在“勞”婆更像知識分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當插花瓶,僅供瞻仰。
二十年前,上海開始去工業(yè)化,上海女人做白領的多,但白領不代表上海女人,好比我的爸爸是男人,但男人未必都是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