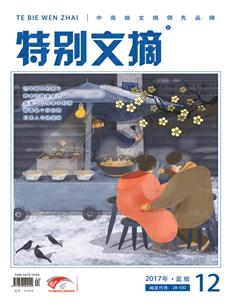起身餃子落身面
周海亮
年輕的父親是一位石匠。每個星期父親都會回來一次,騎一輛舊金鹿自行車。我跑到村頭迎接,拖兩把鼻涕,父親不下車,只一條腿支地,側身,彎腰,我便騎上他的臂彎。父親將我抱上前梁,說,走咧!然后,一路鈴聲歡暢。
那時的母親,正在灶間忙碌。年輕的母親頭發烏黑,面色紅潤。雞蛋在鍋沿上磕出美妙的聲響,小蔥碧綠,木耳柔潤,爆醬的香氣令人垂涎。那自然是面。純正的膠東打鹵面,母親的手藝令村人羨慕。那天的晚飯自然溫情并且豪邁,那時的父親,可以干掉四海碗。
父親在家住上一天,就該起程了。可是我很少看見父親起程。每一次,他離開,都是披星戴月。
總在睡夢里聽見母親下床的聲音。那聲音輕柔舒緩,母親的賢惠,與生俱來。母親和好面,剁好餡,然后,搟面杖在厚實的面板上,輾轉出歲月的安然與寧靜。再然后是拉動風箱的聲音,餃子下鍋的聲音,父親下床的聲音,兩個人小聲說話的聲音,滿屋子水汽,迷迷茫茫。父親就在水汽里上路,父親干了近30年石匠,回家、進山、再回家,再進山,兩點一線,1500多次反復,母親從未怠慢。起身,餃子;落身,面。一刀子一剪子,扎扎實實。
父親年紀大了,再也揮不動開山錘,而我,卻開始離家了。學校在離家一百多里的鄉下,我騎著父親笨重而結實的自行車,逢周末回家。
迎接我的,同樣是熱氣騰騰的面。正宗的膠東打鹵面,蓋了蛋花、蔥花、木耳、蝦仁、肉絲,綠油油的蔬菜,油花如同琥珀。
返校前,自然是一頓餃子。晶瑩剔透的餃子皮,香噴噴的大餡,一根大蔥,幾瓣醬蒜,一碟醋,一杯熱茶,貓兒幸福地趴在桌底。我狼吞虎咽,將餃子吃出驚天動地的聲音——那聲音令母親心安。
起身的餃子落身的面,我真的不知道這樣的風俗因何而來。也許,餃子屬于“硬”食的一種吧?不僅好吃,而且耐饑,較適合吃完以后趕遠路;而面,則屬于“軟”食的一種吧?不僅好吃,而且易于消化,較適合吃完以后睡覺或者休息。一次說給母親聽,母親卻說,這該是一種祝愿吧!“餃子”,交好運的意思;而“面”,意在長長久久。
想想母親的話,該是有些道理的。平凡的人們,再圖個什么?出門平安,回家長久,足夠了。
然而母親很少出門,自然,她沒有機會吃到我們為她準備的“起身的餃子落身的面”。可是那一次,母親要去縣城看望重病的姑姑——本計劃一家人同去的,可是因了秋收,母親只好獨行。
頭一天晚上,我幾乎徹夜未眠。我怕不能夠按時醒來,我怕母親吃不到“起身的餃子”。然而我還是沒能按時醒來,似乎剛打一個盹兒,天就亮了。
起身的餃子落身的面,這習俗讓我憂傷并且難堪。
母親是在三天后回來的。歸來的母親,疲憊異常。我發現她真的老了,這老在于她的神態,在于她的動作,而絕非半頭的白發和佝僂的身體。走到院子里,母親就笑了——她聞到了蛋花的香味,小蔥的香味,木耳的香味,蝦仁的香味——她聞到了“落身的面”。那笑,讓母親暫時變得年輕。
母親吃得很安靜,很鄭重。吃完一小碗,她抬起頭,看看我和父親。母親說,挺好吃。
三個字,一句話,足夠母親和我們幸福并珍惜一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