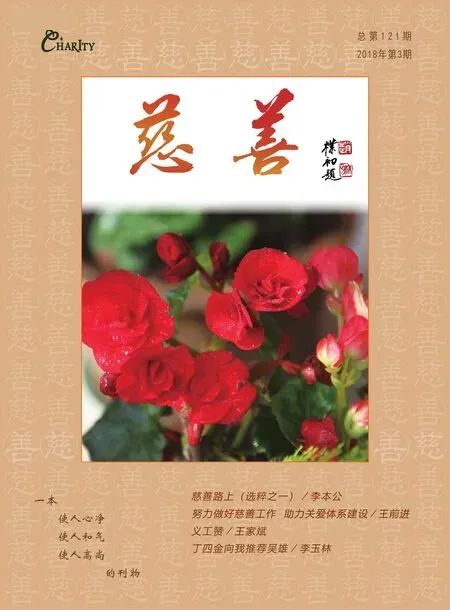懷念母親
文/趙浩義
清明時節回家祭祖。祖墳坐落在秦嶺山脈一峰下面的林子里,松柏挺拔,桃花盛開,猶如仙山瓊閣。在曾祖父、祖父、父輩的墓碑前一一上香、燒紙后,在母親墳前坐了下來,回想母親的歷歷往事。
1921年的10月,母親出生在南秦河畔的一個杏林之家。外公是有名望的老中醫,在縣城開間很大的藥鋪,由于身高體胖,晚年走不動路的時候,四臺大轎出診行醫懸壺濟世。優越的家境,母親可謂是大家閨秀。不僅女紅做得好,而且斷文識字,能讀報紙上的文章。
母親20歲時嫁到槐蔭堂趙家。槐蔭堂是一個大家族,曾祖父弟兄二人、祖父輩弟兄六個都沒有分家,在一個鍋里吃飯,家有幾十畝地,在縣城開有商鋪數間。母親和幾個嬸娘就成為家里的炊事班,天不亮就下床為一家60多口人做飯,晚上還熬夜為城里的蠟燭鋪制作蠟燭。到上床的時候已是午夜時分,腰酸背疼。
母親生下大姐的時候,家道中落。先是兩個曾祖父分家,接著祖父弟兄四個也分了家。分家時,爺爺已雙目失明,父親因患肺癆從于右任創辦的三原中學退學回家。1950年祖父去世時,家里連棺材都買不起,父親穿著孝服四處告借,最后砍了一棵桐樹打了口棺材才將爺爺草草入葬。
爺爺去世后,父親患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幾畝土地就全由母親一人操持。好在新中國成立后土改土地劃歸集體,先是合作社,后又人民公社,母親就成為村上婦女中掙工分最多的社員,同男勞力一起下地干活。
父親的肺癆全憑他從外公那里搬來的一堆醫書,刻苦研讀自學診治,日漸好轉終于康復。1955年我出生時,父親已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中醫進入鄉聯營衛生所掙工資了,每月38元,加上母親掙的工分,勉強維持一個8口之家的生計。
1958年人民公社實行大食堂吃飯,家里的鐵鍋被收走“大煉鋼鐵了”,一頂石磨也劃歸集體被拉走了。當時家里每頓飯全靠母親從食堂擔回來的兩大罐子稀飯。吃飯時,母親總是先讓奶奶和我們孩子吃飽,到自己飯碗里已經所剩無幾,加之又要參加繁重的勞動,母親常常餓暈在地頭。記得有幾次在擔飯回家的路上,母親突然暈倒,罐碎稀飯全灑在了地上。回到家中望著孩子們嗷嗷待哺的目光,母親好一頓號啕大哭。有一次哭聲驚動了好心的村干部,連忙安排食堂再做飯送到家里,全家人才免了一頓挨餓。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遭遇了一場大饑饉,村上的人靠稻糠皮、野菜充饑,連榆樹皮都被剝光了,餓死了幾個人。母親和奶奶整天上山挖野菜,挖來的野菜再拌上稻糠就是一頓飯,做好了先讓奶奶和孩子們吃,到了母親碗里就只有一點湯水了。母親因為餓得了浮腫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虧父親行醫到深山里買回了一些喂牛的黑豆,才救了母親一條命,全家人也逃過一劫。
“文革”到來,我家被補劃為“地主”成分,家中的五間大瓦房和兩畝地的大院子被村上沒收改為村辦小學,我們8口之家被趕到了二爺家的房子居住。狹小的空間,一家人都打地鋪。二爺在新中國成立前曾當過小學教員,又在家搜出了一頂禮帽,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經常被拉出去批斗。
我家被補劃“地主”的主要原因是新中國成立前三年雇了“長工”。事實是一位叫“老李”的70歲老人討飯時被大家族收養,1946年分家時老李已年逾八十喪失了勞動力,母親同情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就將老李領回家像老人一樣贍養,直到去世。母親認為老李已喪失了勞動力,不能視為長工,就邁著三寸金蓮的小腳步行數十里去公社、縣革委會申訴。多次申訴后縣上派人到村上調查,村上的老年人都站出來證明老李不是長工,這才去掉了我家地主成分重定為中農,一家人又搬回原來的房子住。
大姐嫁給了一名公安干部。每年要交給隊上的糧款都是姐夫前來交錢,家庭經濟開始好轉。但村上還有許多貧困家庭,母親時常接濟,給這家端一盆米,給那家送一升面,和我同班的兩個同學交不起學費輟學在家,她讓我把錢送過去讓同學復學。父親回家后母親總是給他說誰家的孩子病了、哪家老人頭疼,把人家領到家里針灸。當時村里人都很窮,看完病買不起藥,父親就免費給藥,時間長了父親每月得為人墊付藥費10元左右。因此父親在南秦川道上博得“好先生”的美名,村上人也稱母親為“賢惠大嫂”。誰家做了好吃的,總是端一碗送來。有一天一個討飯的老大娘餓得暈倒在我家門前,母親把老人扶到家中細心調理,吃了幾頓飽飯老人有了精神要走,母親又挽留住下來,直到她的兒子來接才把老人送走。
“文革”高潮,學校停課鬧革命。我回村上當了“放牛娃”,每天扛著扁擔到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由于路途遙遠,雞叫就得出發,母親總是半夜就起身做飯,飯做好搖醒我起床,吃完飯送給我一個用棉布包裹的飯盒,送我到村口和伙伴們一起出發。不等天亮就走到砍柴的目的地,太陽升起時柴就砍好,扛起七八十斤重的柴擔就往家趕,當時我只有十二三歲,七八十斤重的擔子越擔越沉,走不動時想起母親送我出村時那瘦削的身影,頓時渾身有了力量。記得有一次,山里人因我們到他家的自留山砍柴把我們柴擔子奪了,我空著扁擔往回走,淚流滿面傷心至極,我不是心疼那一擔柴,而是覺得對不起半夜就起來做飯,又把我送到村口的母親。
“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母親鼓勵我復課考學,每天晚上陪我看書到深夜,天不亮又叫我起床讀書,她總是念叨著要“頭懸梁,錐刺骨”。家里有一張供桌,每天起床母親總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凈凈,把書擺放得整整齊齊。高考前的三個月,她不讓我下地勞動,總是做最好的食物讓我吃。當我把錄取通知書送到她面前時,她笑著說了一句話:“我娃行,能吃公家飯了。”離家上學的那天早上,母親把她縫好的嶄新被褥遞給我說:“你哥被村上推薦上了大學,要不是恢復高考,你這一輩子就只能當農民了,到了學校要好好念書,以后的路就靠自己走了。”我背起鋪蓋往前走,走了一里多回頭看,母親還是站在村口那棵大樹下的一塊石頭上往前眺望。這使我想起了朱自清筆下“父親的背影”。
改革開放后,我們兄妹六個進城工作(只有老五因病在家里務農),相繼結婚生子,母親又開始了新的一輪勞役。先是給大哥管護兩個孩子,接著又是為二姐、四弟、六妹、七弟看孩子,整整看了十五年,孫子們一個個都長大了,上小學、上中學、讀大學。這時母親已年過花甲,本想能享幾天清福了,不料父親卻突然中風,終年臥床生活不能自理,這就又苦了母親,一伺候又是十年,直至1994年父親病逝。此時,母親已七十六歲了。終生辛勞,背也駝了,頭發也白了,但身體卻還硬朗。
2000年,我調到省城工作想把母親接來,無奈一直住著一間房子。2002年10月份單位分配我一套三居室住房,我第一天搬家,第二天起床就對妻子說:“我回去接媽。”妻子說:“東西擺了一地,等收拾好了再接吧!”我說:“不行,已經給媽說了,媽在村口等著。”驅車120公里趕回村子,老遠就看見母親提著一個包袱在村口的那棵大樹下眺望,我上前握住母親的手含淚說:“媽,您在家等嘛,外面風大。”接回西安,一位朋友為母親接風在酒店設宴,母親進門說:“茅子在哪里?”朋友不解問:“茅子是啥?”我說:“我媽想上洗手間。”惹得一桌人哄堂大笑。
妻子出身農村,通情達理,很是孝順,為了照顧母親主動聯系借調到西安上班。每天早上起來把飯做好送到母親面前,中午又步行數里趕回來為母親做飯,每天還留下一些錢讓她到街上吃零嘴。兩個兒女也很懂事,爭著在地板上打地鋪把床讓給奶奶睡。母親在我這兒生活了一年多,體重增加了20斤。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妻子扶著母親到鐘樓看花燈,母親后面跟了一群記者,鎂光燈嚓嚓地閃。母親問妻子:“咋這么多的人跟著我照相。”妻子笑著回答:“媽,人家在照您的三寸金蓮,您同大熊貓一樣,是國寶。”
大哥和我在單位都有職務,后來七弟也做了單位副職,母親常對我們弟兄三個說:“媽不指望你們升官發財,但一輩子要積德行善,善事做多了,老天會庇護你們子孫平安。”2015年我退休后被一家民營企業聘去北京做一個公司經理,到任15天接到老領導劉維隆會長電話:“浩義,聽說你退休了,來到省會做慈善。”開始我想:人家大老板在西安等了我七天,才來咋能提出辭職,但想起了母親的話,就以老婆有病為由向老板請辭,老板見我去意已決,拿來一包錢送我,我說是我對不起你,分文未拿,連夜坐火車趕回西安到省慈善協會報到。朋友問我:“每月幾萬元的高薪你不拿,回來做慈善又不發工資。”我用徐山林老會長的話回答:“退休后一不干掙錢的忙事,二不干養花的閑事,就干扶貧的善事。”
2003年,七弟帶母親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相,照相館將母親照片放大展在大街的櫥窗中,行人頓足:“這位老人好慈祥呀!”
2004年春節前,母親突然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請了一名保姆來照料,但母親身高體胖,保姆扶不起來,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我或妻子下班后攜手才能幫母親上洗手間。母親的病經過診治略有好轉,大哥前來要將母親接回家,走時母親手抓著門框不放喊著:“我不想回、我不想回去……”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幕。我也不讓母親走,大哥急了發脾氣:“86歲的老人了,必須老在家中!”就這樣,我流著眼淚送母親出門。
2004年3月15日,我在北京參加CCBA會展,大哥發來短信:“母親病危,速回!”我連夜乘飛機趕回西安,回到家中母親已躺在靈床上了,面帶微笑,安然慈祥。
母親是一只蠶,為了兒女抽盡了身上最后一根絲。
母親是一盞燈,淳樸善良的天性照明了兒女人生的路。
母親,您太累啦,歇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