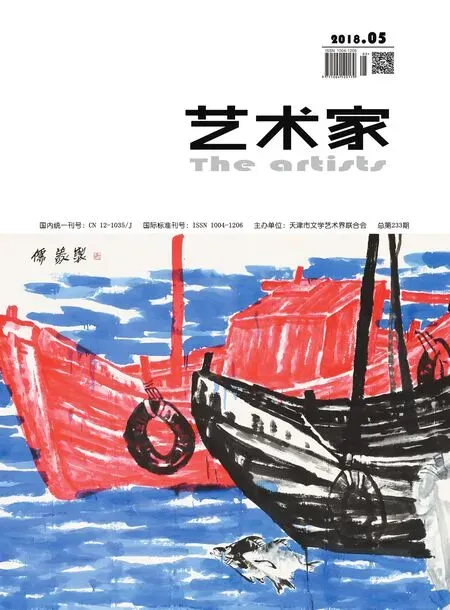探究高胡演奏與高胡樂曲的發展
□朱偉平 廣東粵劇院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響,廣東音樂一直區別于高亢的中原和婉轉的江南,以旋律亮麗而自成一派。而廣東音樂中獨具特色的樂器,便是由二胡衍生的高胡。高胡誕生近90年來,造就了多位高胡大師,由高胡演奏的樂曲上千首,而高胡演奏的技藝也在時光流逝中得到淬煉。
一、高胡的誕生
說起高胡,不得不提起嶺南音樂大師呂成文先生,他出生于廣東香山縣,不久便隨養父前往上海,開始了長達32年的旅居生活。而在上海的生活經歷,讓他接觸到了流行于江南地區的傳統樂器——二胡。當時的二胡多以蠶絲作弦,攬在懷里拉奏,音調處于中高位,婉轉悠揚,不適合用來演奏亮麗的嶺南樂曲。偶然的一次,呂成文發現用雙膝夾住二胡拉奏,聲音更緊亮,后來受到小提琴用鋼弦的啟示,便改制出了音區更高、音調更緊亮的嶺南高胡[1]。
二、高胡演奏
高胡問世之初,多演奏《桃花扇》《荷花亭》《梅花三弄》等江南小曲,后來呂成文先生創作了《平湖秋月》《漁歌唱晚》《落櫻花》等曲目,又將《小桃江》《瀟湘琴怨》等傳統曲目提高八度來演奏,一時受到嶺南地區大眾的熱捧,從此高胡便作為廣東特色樂曲在民間流傳開來。而高胡大家之所以能奏出高山流水般的雅韻,在于對襯音、滑音、花音得心應手地運用[2]。
(一)襯音
襯音是指把上方附有襯音符號的音迅速一弓演奏出三個音來。在實際演奏中,一般采用兩種形式:5(6)5和5(4)3,即快速從第一個音過渡到第三個音,中間那個并不用顯現出來,也不能清晰地出現。這就要求演奏者不厭其煩地勤加練習,從中尋找靈感。而在廣東音樂中,并沒有對襯音運用的硬性規定,演奏者憑借經驗與對音樂的理解自由添加,如果運用得恰到好處,往往會產生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效果。
(二)滑音
滑音由呂文成開創,而后經朱海、劉天一、沈偉等名師進一步發展改良,是一種詼諧高雅的演奏技藝,包括半音上行滑指、半音下行滑指、半音來回滑指三種主要技巧。滑音一般應用于《漁歌唱晚》《青梅竹馬》等輕快活潑的曲調,對于《二泉映月》《禪院鐘聲》等情感凝重抑郁的曲目,則要求嚴肅矜持。
(三)花音
亦稱加花,常用在較長和較平緩的音調間,使原本單調枯燥的旋律變得此起彼伏,豐富音律,妙趣橫生。例如,將3---|變成323412|或5-|變成5455|。和滑音一樣,花音的運用也要恰到好處,不可見縫插針,破壞曲調原有的韻味。
三、高胡樂曲
20世紀20年代之前,西方作曲法尚未在中國流傳開,嶺南的作曲人依靠傳統的工尺譜創作出了簡短的樂章。這些長10——40小節的旋律,因為易懂易學而廣受歡迎,深入人心。
到了30年代,高胡的出現加上抗戰的背景,呂文成創作了《泣長城》《落櫻花》《送征人》等激勵報國衛家的慷慨悲歌。新中國成立后,穩定的局勢為高胡樂曲的復蘇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林韻創作的《春到田間》,由劉天一演奏,是歷史上第一首高胡獨奏曲,旋律新鮮獨特,內容也不同于以往的嶺南曲目。而后,劉天一也自創了高胡獨奏曲《魚游春水》,成為傳世之作。
60年代,廣東音樂專科學校開設了高胡課程,正式將高胡作為一門獨立的樂器進行教學。“文革”后出現了以余其偉、喬飛、李助 為代表的高胡創作家、演奏家。而表現手法也由借景抒情拓展到直抒胸臆,由獨奏或與傳統樂器協奏發展為與現代管弦樂合奏,表達的思想情感也更為豐富。不少作品,如《思念》《粵魂》等還富有深刻的哲學底蘊,這段時期高胡也進入成熟期。
到了21世紀,搖滾嘻哈、重金屬電子音樂的流行也給高胡帶來沖擊。在大融合的環境中,高胡也在默默跟隨時代步伐,不斷前行。如知名的高胡演奏家余其偉、李肇芳、卜燦榮、王永龍、余樂夫、吳岳林等在不斷探索高胡以及樂曲的發展,創作了如《琴詩》《出海》《香江行》等知名樂曲。而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下,我國傳統的民族樂器也走向了廣闊的舞臺。吳岳林在北京音樂廳舉行的高胡交響音樂會,卜燦榮在新加坡舉辦的音樂作品會,都以現代的藝術手法傳達著高胡的獨特魅力。
自高胡創制以來,演奏技藝不斷改良提升,從弓法、指法、揉弦到表現力、音韻都有了長足發展。但應該看到,和其他傳統樂器一樣,高胡也遭受著西方金屬樂器的沖擊,發展空間受到一定的擠壓。我們在堅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的同時,應當以包容的態度汲取西方樂器的優點,為我所用,促進高胡與時俱進,表達時代的精神。同時,應該注重培養青少年對高胡的興趣,為高胡的傳承積蓄后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