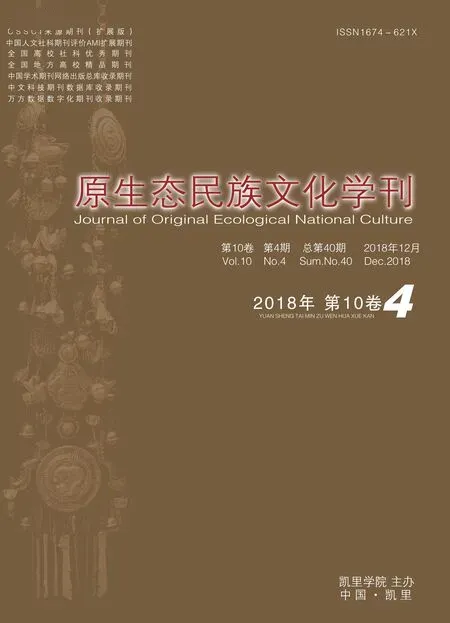主持人語
楊庭碩
(吉首大學教授)
本期推出的3篇論文,所涉及到的生態系統在空間上相距萬里之遙。北面涉及到寒溫帶針葉林生態系統,南面則涉及到云貴高原的河谷生態系統。但3篇論文討論的主題卻高度一致,那就是在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各民族的本土知識和技術在其間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
林航教授的《鄂溫克族馴養馴鹿的本土知識》一文,討論的主題是鄂溫克族民眾馴化飼養馴鹿的本土知識和技術。作為人口較少的鄂溫克族,此前早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但此前研究的重點總是較多地關注鄂溫克族文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而較少關注鄂溫克族文化的盛衰與生態維護的關聯性。該文的價值恰好在于,用生動可靠的事實揭示了鄂溫克族的本土知識和技術在興安嶺生態恢復中的不可替代價值和作用。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總是習慣于認定人是生態系統破壞的主要責任方,也就很自然地主張要實現生態的恢復,必須把人排除在外才能做得好。殊不知,生態系統的純自然恢復,遵循的是純粹的自然規律,各生物物種之間的種間競爭和種內競爭必然要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不可預測的自然風險還會繼續干擾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其結果都會表現為恢復的速度極為緩慢,恢復的成效雖然可以確保生物多樣性的穩定,但不一定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此前人類干擾的副作用也沒有得到有效地化解,該文的特殊價值恰好在于,以生動的實例證明鄂溫克族與興安嶺生態系統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已經達成了協同進化關系,彼此之間相依為命,互為補充,互為支持。而人類在其間發揮的主導作用,恰好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價值,這是因為在人與生態系統之間,只有人才能扮演能動的可積累的有目的的主位角色。鄂溫克人掌控了馴鹿,就可以使馴鹿的生態作用得以放大,得以按照人類的意志和利用的需要,使生態系統恢復的走向更加符合人類的需求。同時,對恢復過程的負面作用得到有效地抑制,而正面的作用可以得到強化,從而使得我們所渴望的生態系統恢復時間得到縮短,恢復的成效更能滿足當下的需要。因而將人視為生態維護對立面的習慣性偏見,通過該文的分析也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還有諸多的細節,至今還鮮為人知,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更其重要。對此,我們翹首以盼,希望在該文的基礎上有更多的新作和認識。
學術界早就公認濕地生態系統乃是“地球之腎”,以至于近年來學者們致力于探討濕地生態系統的恢復時,大多聚焦于平原壩區的濕地生態系統的恢復,卻較少關注高原河谷帶零星分布的永久性濕地生態系統。然而,這樣的生態系統功能尤其不該忽視,因為它是優化中下游水環境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張寶元的《西南山澗濕地的苗族文化生態研究——以意大利藏“百苗圖”所載“爺頭苗”的特殊犁具為例》一文則是另辟蹊徑,在資料的占有上,取自于至今鮮為人知的20世紀初意大利所藏《百苗圖》的抄臨本;在分析手段上,更多地關注到了對圖志文獻的利用,特別是對特殊農具的形制復原和功能探討,形成的結論則做到了發前人之所未發,意在證明當地民族所用的特殊農具,長期以來都被曲解為普通的“犁”。與此同時,該文的分析則明確指出,這種特殊農具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農具,而是適用于永久性濕地生態系統稻田種植的特殊農具,其功能在于清除陳年稻樁,以利下一年的插秧操作。整個操作過程與翻土無關,其特殊的適應價值在于,在這樣的河谷濕地生態系統環境下,土壤的透氣性能不佳,土壤結構很容易脫砂,反復翻土反而會加劇透氣性能的下降,從而影響到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而使用這樣的特殊農具后,不僅可以確保水稻的穩產高產,還能夠支撐伴生動植物的生物多樣性水平。更值得提出之處在于,與這種特殊農具相伴的稻魚鴨共生種植模式,目前已經被確認為國家級和世界級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但圍繞此項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和技術探討,至今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重點關注。圍繞這份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技術探討,至今還鮮有提及這種農具的存在,因而該文的發表不僅可以豐富此項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內涵,還能為當代高原濕地生態系統的恢復利用與維護提供來自歷史的啟迪和借鑒。
同樣是對云貴高原的河谷生境和稻作生計的關注,王健的論文《植物、宴飲與鬼神:傣灑人的生態文化變遷》以兩種作物——甘蔗和水稻切入到當地的生態文化變遷上來。水稻的種植在當地的傣族稻作文化中,有一套完整的種植技術、生態觀念、時空觀念和財富觀與之相匹配。甘蔗與水稻同為當地馴養的植物,區別之一是甘蔗不僅可以在山地種植,更可以在稻田種植。隨著市場和資本的推動,這一作物在當地的生態系統和經濟文化中迅速取代水稻,這一方面在悄然摧毀傳統稻作生計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一整套生態文化;另一方面,甘蔗的種植在當地并沒有形成一整套與之相匹配的生態文化。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這背后的隱患,令人擔憂。因為生態災難的歷史表明,大多數災難的成因不僅僅是“天災”所致,往往更有“人禍”的因素。也就是說,人類的行為若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整套文化因素相制約,必然釀出生態惡果。
任何意義上的生態建設都必然是人類主導下的社會行動,離開了人和相關的民族文化,生態建設都不可能按照人類的需要去實現恢復和優化。如何在這一過程中充分認識和利用相關的本土知識和技術,就顯得至關重要了。圍繞這一問題的探討,至今顯得遠遠不夠,為此我們寄希望于年輕一批學人的快速成長,承擔起此項重大的研究使命,使得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做得更好,更快,獲得可持續的公益服務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