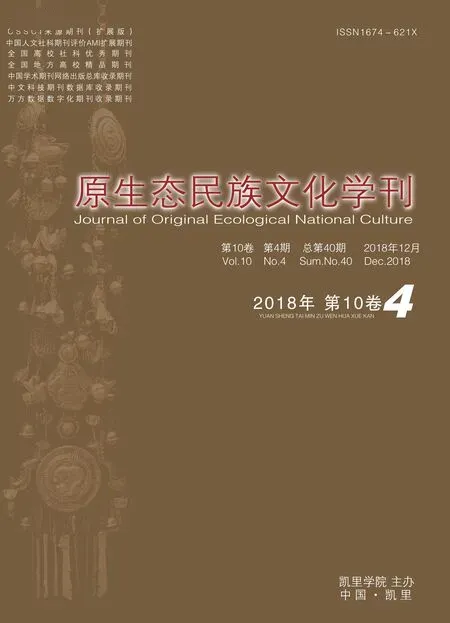清水江文書研究的地點感
張應強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
地點感(sense of place)又譯為“地方感”,該概念較早見于地理學領域,是某個特定人群或個體對某一地方的特殊而真實的感覺和感知,包括認同、歸屬甚至是強烈的依戀。此后這一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旅游研究、城市規劃等領域被運用。近年來,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文學等人文社科領域開始關注這一概念。地點感不僅可以作為我們考察和認知研究對象的切入口和出發點,還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及反思的方法和視角。近年來隨著中國各地民間文獻收集整理研究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走出書齋,在民間文獻產生、收藏或者描述的地方展開實地調查,在田野中解讀文獻,并在相關研究中體現出清晰的地點感。可以說這是理解和解釋民間文獻的不二法門,也是近年民間文獻研究得以不斷深化的道理所在。正如陳春聲在針對區域社會歷史研究時所言:“在追尋區域社會歷史的內在脈絡時,要特別強調‘地點感’和‘時間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區域社會歷史的敘述時,只要對所引用資料所描述的地點保持敏銳的感覺,在明晰的‘地點感’的基礎上,嚴格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后序列重建歷史的過程,距離歷史本身的脈絡也就不遠了。”[注]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讀書》,2006年第9期,第19-28頁。于清水江文書研究而言,在文書產生、收藏或描述的地方追尋和建立清晰的地點感,是研究者把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把握區域社會發展歷史與文化脈絡的起點。
我們強調建立地點感的意義,其中還包括的一層意思是希望反思研究者與地方的關系。“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特別是民間文獻這樣的研究資料的共享而不是獨占,是學術共同體追求和維護卓越學術目標的基本倫理價值;不僅于此,鑒于清水江文書民間收藏的特點,當研究者們受惠于這一珍貴研究資料時,是否也該反思自己又對當地收藏者及地方社會做了什么貢獻與回饋。可以肯定,只有研究者對所研究的地方形成了認同、歸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回饋的理念并付諸行動。這或許是我們強調民間文獻研究中建立地點感的重要性的同時,在另一層意義上對明晰學者應有的擔當和責任的理性期待。美國人類學家邁克爾·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了“有擔當的人類學”(engaged anthropology)的理念,強調研究者對所研究的地方和人群的尊重與人文關懷。這樣的理念同樣適用于我們這些長期受惠于清水江流域的研究者。我們不能將自己與這一地方割離開來,應該抱持一種禮物精神或互惠邏輯,營造一種“有擔當的清水江文書研究”的學術風氣。
就清水江文書的研究來說,地點感的建立關乎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實質上這涉及到民間文獻研究的一個根本視角和特征,即內部視角和地方性。這種視角只有研究者形成了一定的地點感之后才能擁有或無限接近。清水江文書在經過收集、整理與出版之后,進入到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圖書館以及學者的書齋。從形式上逐漸與其產生的地方——清水江流域分離開來。但在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按照傳統的書齋式方法對其展開研究。我們必須清楚,清水江文書的根始終在清水江流域,唯有借助這一流域“文化持有者”的視角,即內部視角,方能達致從“地方”到“地方性”的認知和理解。清水江文書是清水江流域社會歷史文化過程留下的“一塊拼圖”,我們必須不斷嘗試回到地方,“走向歷史現場”,在一個具體的文書產生地點及其文化語境中,全面把握、理解進而解釋這些民間文獻。
本期收錄的3篇論文分別是唐智燕的《清水江文書中特殊計量單位詞考源》、羅云丹《從清水江文書看清代及民國時期天柱、錦屏民間的婚姻習俗》和范國祖的《清水江文書漢字記苗音苗語地名整理研究》,分別從清水江流域的計量單位、婚姻習俗和苗語地名切入清水江文書研究;在呈現清水江文書的地方性和內部視角的同時,也關照到了清水江流域與外界的關聯,從各自不同的方面提示了保存敏感的地點感的重要學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