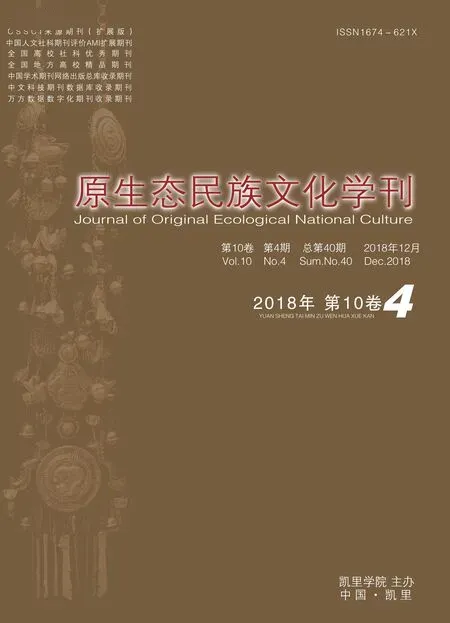西夏行政法制的特點及對當今我國民族地區之借鑒*
于語和,劉珈岑
(南開大學法學院, 天津 300350)
黨項,是原西羌中的一個分支,也稱之為黨項羌。南北朝時期主要于析支(今青海黃河曲)聚居,隋末開始漸漸發展,向周圍地區擴散。黨項族主要活動范圍東到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1],也就是現在的新疆青海一帶。當時黨項作為氏族部落,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主要以畜養牛、羊、馬等牲畜的畜牧業為生,既無文字,也無歷法,部落之間并不統一。早期的黨項氏族社會中并未產生法律制度,氏族成員產生的沖突和摩擦主要依靠沿襲流傳的“習慣”和“俗法”進行處理。至宋朝時期,黨項社會內部已經產生了成文的“習慣法”,有和斷官依法裁斷。《宋史·黨項傳》記載,宋景德四年(1007年),唐龍鎮黨項族內部有族人結仇,由此造成附近帳族雞犬不寧,家家戶戶叫苦連篇,于是“詔遣使召而盟之,依本俗法和斷”。仁宗天盛年間,西夏頒布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以下簡稱《律令》),其內容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包括刑事、民事、軍事、行政等范疇,堪稱一部較為完整的綜合性法典,為我們研究西夏法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獻。
隨著《律令》的發掘和研究,西夏法律研究在不斷進步,但仍屬于新興學科。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條件和文化水平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改進。但不可忽略的是,少數民族地處偏遠,加之地理位置的阻隔和經濟欠發展,少數民族人民的法律意識普遍呈現出淡薄狀態,行政法律體系在少數民族地區亦沒能得到很好的貫徹實施。今天,想要完善少數民族行政法制建設,就要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汲取成功經驗。本文僅就西夏行政法律體系特點進行分析,結合現代少數民族地區實際情況,為推動少數民族地區行政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提供鏡鑒。
一 、西夏行政管理體制的特點
西夏的行政管理體制產生于中國傳統封建職官制度發展的成熟期,框架基本仿照宋朝,但鑒于民族本身的經濟文化特性和社會組織結構,又保留了符合西夏現實情況的黨項舊制,展現出中原傳統官制與黨項羌舊制相融合的行政法律體制。
(一)番漢合一
黨項族在內遷前并無行政體系,只有部落首領統制;內遷后受中原先進政治文明影響,也急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體系,因此直接移植了宋朝的職官制度。主要表現在:一是在內表現為接受并適用了儒家三綱五常、君臣倫理的思想體系,《律令》的指導思想就是“君為臣綱”。西夏選官制度主要采用世襲制,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和五等喪服制,戶絕者的財產可由五服中所近人取得,五服這一說法是典型的儒家概念。引入科舉制后,考試范本采取的也是中原傳統的《論語》《孝經》《孟子》等儒家經典[2]。另外西夏對官吏的管理中融合了德治與禮治的思想,即除了通過法律手段來制約和管理官場,亦運用道德倫理束縛官吏思想,使其遵紀守法,恪守官制。如《律令》中規定位高臣子以威勢隱藏他人妻女強以和合者,根據官職高低要予以處罰,這反映了倫理道德和官法相結合的特點。二是在外則表現為行政建制的全面仿宋。對比《律令》和《宋刑統》,二者規定的行政機構基本一致,西夏僅在番漢權力優先級和少數黨項特色規定上有所增添。在中原官制的管理方面,西夏不僅吸收了其對于職官機構的設置理念,還充分汲取了一些具體的官吏管理制度,例如職、官分離制,職官選敘、考課、監察、官法等制度,且有嚴格的官刑與吏律規定。
西夏作為黨項貴族建立的國家,借鑒中原官制只是“番制為體,中學為用”,不僅在行政體系中保留了許多黨項舊制,番人在行政權力和運行時也有諸多特權。
首先,在職官設置中,部落首領仍被授予非常重要的官銜和統領一方的權力。他們終身任職,世襲授官,既為朝廷命官,又是部落首領。在中央還單獨設有寧令、謨寧令、廠盧、素赍、祖儒、呂則、樞銘等番官名號,只能由番人擔任。在權力優先級上,當番、漢、西番、回鶻共職時,“位高低名事不同者,當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但如果二者“位相當,名事同”,那么不論官高低,都以番人為大。
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黨項族早期以狩獵游牧為主,建國后也“以羊馬為國”[3],畜牧業是西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牧官在西夏行政體系中的地位也頗為重要。西夏最高經營管理畜牧業的部門是群牧司,位于中等司,設六司正、六承旨,主要職責是指導全國畜牧業生產,經營和管理國有牧場;馬院主管飼養馬匹和駱駝,用于進貢和與鄰國交換;經略司在官畜患病時也承擔一部分管理職責。
在處罰的規定方面,軍事法典《貞觀玉鏡將》和后來的綜合法典《律令》,都在處罰手段上設有“罰馬”這一項。如此設定的主要原因在于,“游牧”是西夏境內黨項族的主要經濟生活方式,因此,馬對于黨項人來說,在生活和經濟中就顯得格外重要,將罰馬作為處罰手段,也體現了西夏軍事法律中結合民族自身特色的特點。
(二)等級分明
西夏的行政管理體制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封建政權而存在,不可避免地帶有等級性。中央機構主要分為五等司,各等之間等級分明,不同等級之間的官吏享有的特權不同,禮儀規范也不同。
西夏的官依其官品可在諸多領域內享有特權。首先,官吏享有官位世襲和蔭補的權利,官宦之子可憑祖、父地位在仕途上享受特殊待遇。西夏皇室中,仁忠、仁禮二人就是以恩蔭的方式入朝為官的,分別官至禮部郎中與河南轉運使,遵頊也曾以此方式襲爵,說明了西夏存在官的優先承襲權,《律令》對此也做了相應的規定。其次,官吏享有教育特權。西夏從立國初重“蕃學”到后來重“儒學”,在維護黨項民族文化的同時利用儒家思想文化維護統治。但是,無論是元昊時期各州設立的“番學”,還是后來的“國學”“小學”“大漢太學”,優秀的官宦子弟都可入學享受教育。皇室內部的“小學”,只要是宗室子弟無論年齡大小都可入學學習。這些都表明了官宦和宗室子弟享有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和更好的教育資源,即所謂的受教育特權。
官吏享有的法律特權是最明顯的,《律令》在這方面有諸多規定。 首先,法典顯示出了強烈的等級性,主要體現在殺傷罪的量刑上。庶人殺傷有官之人要比傷害庶人的量刑嚴重許多。庶人故意傷害庶人未遂的,主犯徒10年,從犯徒8年;而庶人故意傷害有官之人的,根據有官之人的品級予以加重處罰:對有“未及御印”官,未傷則造意徒12年,從犯10年;對自“及御印”至“拒邪”[注]“未及御印”“及御印至拒邪”和“及授”為西夏官階的三種等級,等級依次提高。六品以上為及授官,犯罪需要奏報才能定罪;六品以下為及御印和未及御印,享有的法律特權較為有限。的官員,故意傷害未遂的主犯也要絞殺。而有官人打傷庶人的,則依二庶人毆打罪狀法斷之,可以官品當。而官當除名也只是暫時離職,并非與仕途絕緣,仍有官復原職的機會。可見官員在刑罰上的特權十分明顯[4]139。其次,西夏與中原相同,八議之內的官員享有特權,犯死罪時要上奏皇帝后實行,長期徒刑以下的依次減一等。最后,《律令》也處處體現著官吏的懲治獎罰與官品的密切聯系,職務官品越高承擔的法律責任越輕,獎勵則是官品越高獎勵越重。
為了維護統治秩序,法典也規定了官吏朝服、座次等之間的差異以體現等級性。在朝位座次方面,根據法典的規定,中書、樞密的大人承旨及經略當請,應分別坐。有當校文書時,當請承旨、都案、案頭局分人等引導校之,然后京師、各地邊司等大人、承旨、習判刑等一同正偏當坐。名事同,位相當時,番官和漢官座次也不同。總的來說,基本是當官品、職位相當時,黨項族節親主的地位最高,其次是番人,末等是漢人;文武官職相當時,以文官為大。這說明西夏雖然作為少數民族政權,但是廣泛吸納了各族人員參與政治,同時為了保護本民族的利益和地位,也給予本民族官吏禮遇上的特別對待。
(三)重典治吏
“明主治吏不治民”,西夏早期存在外戚專權的問題,官吏內部結黨營私積弊已久。為了肅清吏治防止腐敗,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西夏在《律令》中設置了許多職務犯罪的罪名,量刑也較為嚴重。
首先,法典嚴懲貪贓枉法,專門設置了貪狀罪法門,并且后面大量刑罰規定中很多犯罪都比照貪狀罪處罰。西夏法典將貪贓行為分為“枉法貪贓”和“不枉法受賄”兩種,對于收受賄賂在判案中重者輕判或輕者重判的,或行賄和受賄雙方達成合意的,根據錢財多寡和情節輕重予以處罰。受賄者最輕處杖刑十三,最重可判絞殺,行賄者按從犯量刑。即使并未接受錢財,官員飲食當事人酒肉也要按照酒肉價值以貪贓罪判斷[4]147。兵器校驗時,若巡檢者受賄徇情,弄虛作假以次充好,侵害軍隊利益,則與隱瞞他人之罪及弄虛作假罪比照并罪加一等。
其次,為了防止官吏懶政和不作為,法典也明確規定了各種公務的辦理時限和赴任期限。比如,在行政機關發送公文方面,法典明確規定了期限要求。凡有拖延公文日期的行為,按期限的長短和延緩公事的輕重緩急程度予以懲處;審案有一定的期限,死刑、長期徒刑40日,獲勞役者20日內處理完畢;磨勘納籍時若監軍司大人未行動,延誤5日以上就要罰馬甚至降官等。西夏疆域廣闊,有些地區條件艱苦,官吏并不十分愿意赴任,所以對于官吏延遲赴任也有詳細規定。對于大人、承旨、習判、都案、案頭等不赴任及超出寬限期,又得職位官敕文已發而不赴任,超過1個月當革職,司吏、使人、都監超過1個月要徒3年。
另外,監察也是治吏的有效手段,西夏中央有御史臺和諫官,地方刺史、經略使、巡檢等也承擔監察職能,共同形成了對不同級別官吏的監督體系。就經略使而言,主要負責定期監察轄區內官員的工作進度質量;審查當地的刑獄審判案件、訴訟有無冤假錯案;核查邊中各地有無謀逆行為和謀逆語言論等[4]114。不限于此,對于轄區內部的各種財物經略使也有監管權,邊中諸司各自所屬種種官畜、谷物,何管事所遣用數,承旨人當分任其職,所屬大人當為都檢校為提舉,所借領、供給、交還及償還、催促損失等,依各自本職所行用之地程遠近次第,自3個月至1年一番當告中書、樞密所管事處。附屬于經略者,當經經略使處依次轉告。不附屬于經略使處,當各自來狀。……經略上有管事司及本人處六庫等,依地程遠近次第轉告……[4]529
總體來說,《律令》在治吏方面的規定較為完備,達到了肅清吏治、獎懲有度的實效,對于維護西夏行政管理體制的正常運行、維護王朝的長治久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番漢融合的行政體制形成原因
西夏行政體制的形成,與其繼承和吸收中原職官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但是又有自身的文化背景和顯著的民族特色。在眾多影響其發展的因素中,以下兩個方面最為至關重要。
(一) 漢唐影響
西夏位于中華民族固有版圖的正中心,也處于宋、遼、金、回鶻、吐蕃的中間,亦是絲綢之路主線的必經之路,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言而喻。西夏疆域中的河西走廊涼、甘、肅、瓜、沙五州,自西漢張騫“鑿空”以來,一直是中西交通主線所經。周邊各國經濟往來文化交流,多數要經過西夏。唐末至宋初吐蕃勢力控制隴右地區后,中西陸路交通主線改由長安北向靈州,但仍然回到河西走廊,經涼州、甘州西去。被西夏控制的朔方地區,包括夏州、靈州及整個河套地區。其中:夏州北出經天德軍直達貝加爾湖,唐太宗時辟為參天可汗道,成為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通四夷道”;宥州是唐末繞道阿爾泰山南麓通西域道上的一個大站;靈州則是唐大中五年至宋初中西交通主線的必經之地。也就是說,傳統的中西陸路交通主線,都要穿過西夏境內。交通地理位置上的優越,使西夏本身的貿易、外交往來十分方便。因此西夏的行政制度受到了周邊各民族政權制度文化的影響,呈現出番漢雜糅的局面。
創建西夏的黨項人本來是比較原始的游牧民族,建立獨立政權后,其統轄區內有大量漢人及其他民族成員,又處于漢文化的長期影響之下,因此,只有漢族的儒學文化,代替和改造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西夏作為宋朝屬國時,其服飾、天文、歷法、官職、宮殿和寺廟建設,一直模仿中原王朝。元昊即位建國后,番學漢學在不斷的斗爭和融合后,儒家的治國方略得以逐步確立。至西夏仁宗時期,重文偃武和崇儒尊孔的傾向愈演愈烈。在西夏統治的盛世時代(乾祐1170-1193年),仁宗李仁孝重視教育,建立學校,推行科舉,推崇儒學,建立翰林學士院,使西夏文化走上了輝煌時期。儒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受到重視。大量的儒家經典被翻譯成了西夏文,作為學校的教材經典。隨著儒家思想的進一步傳播,西夏吸引和培養的儒學大家越來越多,如著名的學者斡道沖,精通《尚書》和其他經典,將《論語》翻譯成西夏文,并著有《論語解讀》等著作,后成為仁宗時期的宰相,在西夏頗受愛重。
(二)黨項遺風
黨項族是游牧民族,內遷前以部落部族形式居住在青海、四川一帶的游牧區,逐水草遷徙,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較低,人們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部族首領就是他們的最高統治者,實行世襲制。內遷后,黨項族多與漢族及其他民族雜居,相對削弱了血緣關系。立國后,西夏境內既有農耕社會的州、縣、鄉、里組織,又有少數民族部族的存在,生態地理環境的變化,使黨項族舊有的部族首領制無法滿足新的需要,以前的部族首領統制模式有所弱化,繼而出現了符合中原州、郡、縣、鄉、里管理的以中原職官制度為主導的職官制度。立國后,隨著統治區域的拓展和經濟的發展,西夏的職官的設置開始沿襲中原官制框架,建立較為完備的體系,職官機構、職務上的分工也就日益細密,職官的員數也隨之増長,如:農田司、群牧司、御史臺、樞密院、中書、轉運司等的設置。而到仁孝年間,西夏的職官設置就更為全面了,將職官機構劃分為上、次、中、下、末五個等級,新出現了許多機構和職官名稱,殿前司、正統司、統軍司、經略司、皇城司、宣徽司、內宿司、函厘司、大恒歷院、御庖廚司、養賢務、資善務、回夷務、刻字司、各工院(鐵工院、木工院、磚瓦院、紙工院、出車院、織緒院等)都反映了西夏經濟的全面發展給職官制度帶來的影響,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事務的増多,使西夏政權的職官機構設置向著系統化方向發展。
游牧民族在維護其政治統治的過程中都是既有向其他政權學習的欲望,又有保留本民族傳統的本能,反映在職官制度領域便是在新的職官制度中往往會保留了舊有的歷史傳統和習俗。部族首領制是游牧民族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制度,是游牧民族姓氏為種落,聚族而居的部落組織以及逐水草而遷徙居無定所的狩獵、游牧經濟形態的產物。一方面,西夏保留著部落意義上的首領,“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5]。這里的首領嵬名山就是大部落的領袖,對內統領族眾,對外代表本部族。另一方面,《律令》中有大量條款涉及西夏首領,表明西夏立國后也存在職官意義上的首領。西夏基層軍隊稱為溜,因此其軍事負責人又稱為溜首領:“一諸首領所領軍數不算空缺,實有抄六十以上者,掌軍首領可與成年兒孫共議,依自愿分撥同姓類三十抄給予。”[4]265以此看來,職官意義上的首領也保留著世襲傳統,是西夏行政管理體制中管理基層重要的一環。民族本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往往會對一個民族政權的職官制度產生很大的影響,而鑒于西夏所處的地理生態環境和政治生態環境的作用,其職官發展制度采取吸納外來文化,保留內部傳統也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
西夏官吏的選敘以世襲為主,主要就是針對黨項部族而言的,民族文化傳統決定了他們中大多數人只能以恩蔭和世襲的方式入官,而非以科舉考試的方式獲得。當時的宋人范純粹認為,邊塞部落的人以種族血脈論貴賤,因此當部落首領去世時,即使繼承人是區區稚子也能服眾[6]。部族首領制在西夏職官制度中的存在,表明了西夏是在尊重本民族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制定了適合本民族和本國實際情況的職官制,這是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交流與調適的結果。現實情況決定了首領制在西夏的存在是自始至終的,他們在西夏的政治、經濟、軍事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西夏,黨項的部落宗族既是一個軍事實體,又是一個經濟實體,他們是一個血緣關系的共同體,貫穿于黨項社會和國家的全部過程。
除保留部族首領制外,民族傳統對西夏職官制度的影響還體現在職官服飾、印章等方面。西夏武官戴冠,金涂銀束帶,垂碟摟,佩解結錐,束帶主要用于佩掛各種隨身物品,西夏官員穿窄衫、束腰帶等都反映了當時北方少數民族傳統服飾特點,與其生產生活環境相關,是為了便于上下馬和行動。說明西夏在吸收中原官員官服制度的同時也部分保留了本民族服飾傳統。西夏官印在承襲唐宋之制的同時也有自己的特點,古代印紐穿孔的形制在西夏官印中得以保留,這主要源于黨項族是“馬背上的民族”,印紐上穿孔便于佩帶和保管。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7]西夏獨特的行政法律制度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和民族融合中形成起來的。
三、 西夏行政法律體制對當今民族地區借鑒
(一)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西夏成熟的行政管理制度深受其周邊各民族政權政治文化的影響,因此西夏行政法律制度在演進發展的過程中,各個方面都不斷地受到外來制度文化的影響,如教育科舉制度、職官制度等。西夏景帝李元昊就曾對宋朝一些失意的文人予以重用:“或任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元昊還在中央政府中設立蕃、漢學院,同時規定:“漢學院練習西夏字的正草二體,兼及篆、隸,官秩與唐、宋的翰林相同。”[8]這就為西夏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西夏的行政法律體系也有這樣的特征,不僅受到中原官制的影響,也受到周邊其他民族政權官制的影響,呈現出雜糅并蓄的特點。漢人儒士參與少數民族的政權、參政群體的多元化是其發展行政體制的重要舉措。
統治者為了本朝的經濟、政治的發展和完善,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固,勢必會重視教育和培養人才,西夏也不例外。其歷代統治者為了加強行政管理,十分重視教育,一直推行漢文化,并仿效唐朝和宋朝科舉取士的方法選拔人才。我國當代少數民族發展亦可如此。現如今,考取公務員、選調生成為大多數畢業生所青睞的選擇,鑒于此,中央可順勢將一些“基層工作經驗”的鍛煉地點放在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并給予這些大學生適當的利益引導和優惠政策,在一些偏遠地區恰巧需要一些有新文化知識、新思想的熱血青年來支撐、輔助其發展。在加大少數民族教育力度方面,中央可加大對少數民族中等、高等學校的教育投資,給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提供更多外出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吸引高中畢業學生前往地方高校就讀,拉動當地少數民族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定期組織少數民族科學技術性人才到北上廣等地參觀學習,使其盡快融入現代科技發展的大潮中,以帶動少數民族地區的科教文衛事業建設。
少數民族大多地處偏遠,正因為如此,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對其經濟的發展就顯得至關重要。現如今文化交流的渠道可多種多樣,其一,對少數民族進行“輸血性”支援。例如為少數民族地區捐贈各式各類的圖書、樂器、實驗器材,豐富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教育方式,構建少數民族基層文化設施體系,成立基層文化中心,利用政策傾斜鼓勵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去西藏、新疆等地支教,把現代發展理念帶到少數民族偏遠地區。其二,少數民族自身“造血性”發展。少數民族只有自身加強“造血”功能,才能使得少數民族文化可持續發展。例如,當地可舉辦大型文藝比賽,選拔最具有當地民族特色的文藝隊伍到其他城市進行文化宣傳,為當地經濟建設拉取一定的外來投資,激發當地經濟增長內生力。另外,少數民族還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打通交通要道,使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形成良性互動,拉動欠發達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
但在民族間互相學習外來文化的同時,西夏對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全盤接收,而是在與本民族文化做調適整合的同時,批判性的吸收與自身文化相融相輔的方面。因此,我國在深入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鼓勵民族間相互學習的同時,要格外強調在與本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基礎上,為民族間交流鋪路搭橋。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偏遠的邊疆地帶,交通的不便使其與外界溝通甚少,甚至有的少數民族至今還保留著氏族部落“桃花源”式的生活方式。雖比起改革開放初期,高鐵、動車等便利的交通使得少數民族與外界經常性的來往,但由于經濟條件和距離的限制,目前少數民族與漢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交流仍然比較匱乏。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各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積淀的精華之處,因此,我們應該借鑒西夏文明發展中的經驗,加強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通共和,各民族博采眾長,吸收外來精華與本民族文化進行調適和整合,如此方能促進各民族的政治文明現代化,跟上時代的步伐。
(二)自治權行使的促進與加強
與西夏蕃漢合一的行政管理體制一脈相承的是,重禮尚樂,嚴格管理,西夏政權十分重視禮樂、典章制度的建設,這也是西夏統治者在充分尊重西夏人民非常喜歡音樂這個特色而形成的管理模式,與本民族了解地方特色,能夠自己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是分不開的[9]。自治權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核心,也和該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的經濟水平和文明程度息息相關。要真正實現民族平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保障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真正享有自治權。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有關規定,自治機關所享有的自治權主要涉及立法權、變通執行權和管理本地方經濟建設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以及發展本地方通用的語言文字、培養本地方的技術人才。《民族區域自治法》自1954年實施以來,在加快民族立法、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政治、文化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但在切實保障落實自治權的過程中,仍然需要進一步加以修整和完善。
首先,目前民族自治機關在運用自治權的過程中,存在部分上級國家機關影響自治地方自治權的行使的情況。其次,自治機關有時甚至不能正確處理與上級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如,少數民族在針對上級機關的決議、命令進行變通執行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對于變通程度的把握不夠成熟,而不能有效地做出對于民族自治地方最有利的判斷。再次,自治機關對于經濟自治權的運用不夠充分。民族自治地方大多地處偏遠,氣候環境惡劣,加之一些歷史的因素,導致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意識不高,自身發展意識薄弱,不能充分運用自治權來提高當地發展水平。最后,我國在擴大民族自治權的范圍尤其是基層自治、充分尊重少數民族自治權的行使、拉動少數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發展、構建合理規范的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關系方面仍存在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因此,我們應以史為鑒,充分借鑒西夏多民族并存的行政管理模式,加強少數民族自治權的行使,實現少數民族自身發展和時代進步的協調統一。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其一,加強基層自治。民族鄉由于不屬于自治地方,故而其自然不享有自治權。各民族歷史上大多創造了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村寨自治制度,但這種自治方式十分簡陋,大多以頭人、宗族、部落等形式存在,但村民由此也依然保留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習慣,權力行使的專門化程度也十分低下,因此,為了使基層自治權法制化,有必要對傳統自治形式加以整合。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特點,村民自治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在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維權意識的同時,更充分調動了其參與民主事務,行使民主權利的積極性,是我國基層自治的成功典范。故少數民族地區也可嘗試放開基層自治權,以民為本,加強少數民族基層民主和自治組織的開發與建設,通過借鑒村民自治為少數民族注入現代民主因素,實現少數民族村寨自治與現代民主的合理對接。其二,建立多元化的干部選用和培訓模式。在選用方面,可大膽結合少數民族實際特點,構建科學合理的測評任用機制,完善競爭上崗的組織領導系統,吸引人才回流,擴寬少數民族人才來源。在培訓方面,尊重少數民族特色,強調領導干部的主體地位,提高培訓者與勞動人民的互動頻率,開發適合少數民族的多元化干部培訓方式,可同時采取講授式培訓、案例式培訓、研究式培訓和互動式培訓相結合,還可深入少數民族人民群眾內部,總結心得,實現領導干部綜合實踐能力的提升,根據當地居民需求,創新服務形式和服務內容,為居民提供更加貼心的服務,提高少數民族人民的自制能力。
(三)反腐倡廉之風的規制與實行
在西夏職官制度中,職和官是分離的,官只是一種身份,職才是有實權的象征,西夏設置完善的官階制度用以強化官員的身份和等級,利用范圍廣泛的獎勵方式和嚴厲瀆職處罰來維護督促官員盡忠職守,維護行政體系的有效運轉。官吏在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的同時,同樣也會享受一定的特權待遇,例如,西夏官吏享有的教育特權、法律特權,以及授予官吏的禮遇等。西夏官吏的考課獎懲制是對官員進行監督的一種手段,因此,西夏對于反腐倡廉的重視和對官員的考課獎懲是其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國目前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民眾對廉政建設效果評價的數據表明,干部態度生冷、辦事拖拉不在少數,這在一定層面顯示出一些領導干部服務意識的薄弱和服務效能的低下。另外,少數民族地區漢族干部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僅大大影響同少數民族領導干部的團結,更因此可能會造成民族間關系的刻板和冷淡。為了確保各項政策執行不走樣、資源分配更公平、保障各族人民合法權益的實現,應當將少數民族的廉政建設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少數民族要更加重視培養黨政干部對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的轉變,正確處理好少數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主體少數民族干部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的關系,真正做到人民是主人當家作主,干部是公仆服務人民,真正達到廉潔高效,促進公平正義和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
現階段民族地區廉政建設的進路是建設外部性和內生型的監督制約機制,將廉政建設納入自治法規,從而促進社會穩定。其一,外部性監督制約機制是指隨著交通和網絡的日漸發達,漢族和少數民族聯系日益密切,在反腐倡廉興盛的今天,中央也應加大對少數民族反腐倡廉的隊伍建設,構建少數民族地區的反腐倡廉的政策體系,建立科學民主的少數民族地區干部選拔機制,向少數民族地區輸送優質資源,加強當地的反腐倡廉教育;其二,內生型監督機制即通過發揮自治地方人民群眾的作用和加強領導干部自身建設的方式來推動廉政工作。發揮民族自治地方少數民族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鼓勵人民群眾參與到監督領導干部工作的法制建設中,適時地進行普法宣傳,使得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群眾與國家大勢接軌,及時了解國家的法治動態,從而加強當地人民的法律意識,依靠自治地方內在的動力促進當地的廉政建設;其三,領導干部獎懲方式多元化。針對少數民族當地特色,為了提高領導干部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可采取競爭上崗和定期政績考核、口碑考核方式,對于自治地方民意評價不達標者,應下基層承擔一定時期的基層工作,融入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其四,自治地區應及時開展領導班子培訓,從源頭提升領導干部服務意識和業務能力,適時開展績效考核,堅決查處干部以權謀私等違法亂紀行為。社會公平廉政,才能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提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確保民族地區長治久安。
四、結語
當前,我國《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立法法》都對少數民族行政管理體制有所規定,對充分保障少數民族權益和多民族國家團結統一做出了重要貢獻。未來也要加強民族間經濟政治特別是文化的交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打通交通要道,使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形成良性互動,拉動欠發達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利用政策傾斜鼓勵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去西藏、新疆等地支教。加快促進少數民族地區基層自治權法制化,實現少數民族村寨自治與現代民主的合理對接。繼續推進少數民族地區廉政建設,實行領導干部獎懲方式多元化,加強當地人民的法律意識,依靠自治地方內在的動力促進當地的廉政建設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西夏的行政管理體系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現代少數民族行政法律體系的建設也需要立足國情,充分汲取傳統法律文化的精髓。博古才能通今,相信西夏行政法律體系的研究和當代少數民族行政法律體系的建設都將取得長遠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