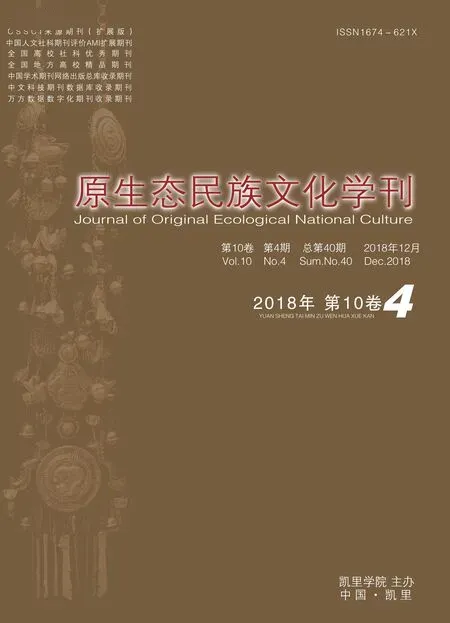現實之鏡:《在未知的中國》諾蘇形象疏論*
劉振寧,劉 騻
(1.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貴州 貴陽 550025; 2.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廣東 廣州 510275)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簽訂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向西方列強開放中國全境,傳教士們一則憑借條款的“法理依據”和強權庇護,再則受到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進軍中國內地“樹立十字架的旗幟”的鼓動,源源不斷涌入其間。族群高度重疊并生的中國西南,隨即成為了傳教士們心馳神往的逐夢場和筑夢園。英國循道會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及其教友,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語境而梯航東渡,輾轉奔赴西南邊陲,穿梭奔走在各族群山寨和村落,采用相遇、接觸、嵌入等漸進模式,在收獲東方靈魂的同時,記錄了宣教域內諸多族群的社會情狀和文化風貌。于是,各種記載墾拓事工、敘述人生際遇、報道異國風情的著述文本不斷涌現,共同匯集成了書寫和反映晚清民國時期中國西南圖像的心影文獻庫。《在未知的中國》[注]《在未知的中國》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上泛指經東人達與東旻翻譯注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七部英文漢譯著作的合稱,即出版時被統一冠于《在未知的中國》名下;狹義則特指上述英文著述中柏格理的專著《在未知的中國:一個傳教先驅在中國西部野蠻而未知的諾蘇部落中長時間游歷的觀察、體驗和探險記錄》(1921)。本文主要以后者為闡述立論依憑,同時又多少兼及并引用了前者所指著述中的相關論據。便是其中的翹楚之作。僅著作中川滇黔邊諾蘇[注]諾蘇亦稱亻羅亻羅,實指新中國成立后經民族識別統一以“彝”作為民族族稱前該民族的眾多舊稱之一。龍正清《彝族族稱演變概說》稱彝族的“彝”,是“根據秦漢以后所稱‘西南夷’的‘夷’改作鼎彝的‘彝’,謂之有飯吃也有衣穿”。在正式統稱彝族前,該族族稱歷經了從“諾蘇”“夷族”到“蜂族”三個重要文化積淀時期。(見龍正清著《彝族歷史文化研究文集》,貴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30-134頁。)晚清民國時期,由于地區和方言不同,彝族支系繁多,有許多不同的他稱和自稱,主要的他稱有“夷”“蠻子”“夷猓”“猓猓”“猓人”“猓玀”“玀玀”“亻羅亻羅”等;主要的自稱有“諾蘇”“納蘇”“聶蘇”等。為便于敘述和論證,本文自此處起將統一沿用文獻寫本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諾蘇(亻羅亻羅)舊稱。民眾形象書寫的知識言,大凡譜系、體貌、族性、服飾、語言、禮俗、信仰、傳說、經濟、階層等各種信息,可謂無所不包,涉及了文化相關的物態、制度、心態及行為各個層面。它們宛若一面鏡子,映照出了諾蘇普羅大眾的生活圖景和形象輪廓。為此,本文借助比較文學形象學原理,糅合“文化結構”解析進路,就寫本中的近代諾蘇眾生形象進行勾稽爬梳,就該西鏡東像形象特征進行初略詮解。
一、諾地與諾人
從弱冠東渡到捐軀苗嶺,柏格理宣教中土近29年,其中28載輾轉跋涉于崔嵬險峻的滇川黔邊,為傳教事業、民族教育和文化改良而不避艱險。《柏格理墓志銘》有載:“金沙江外,舉凡瘴雨蠻煙,察會荒冷之區,靡費足跡殆遍。”[1]作為西方首位深入并逗留“野蠻未知”的涼山腹地的傳教士,柏格理同其教友或通過在場體驗和親筆書寫,或借助后期轉述和回憶敘事,留下了大量事關諾蘇“大本營”民眾日常生活與整體形象的考察報告、見聞游記和研究著作。除了直接源自柏格理筆端和心田的著述文獻——《中國歷險記》(TightCornersinChina,1908)、《在未知的中國:一個傳教先驅在中國西部野蠻而未知的諾蘇部落中長時間游歷的觀察、體驗和探險記錄》(InUnknownChina:ARecordoftheobservations,adventuresandexperiencesofapioneermissionaryduringaprolongedsojournamongstthewildandunknownNosutribeofWesternChina,1921)及《柏格理日記》(EyesoftheEarth:thediaryofSamuelPollard,1954),還有追憶性寫本《柏格理傳記》(BeyondTheClouds:TheStoryofSamuelPollardofSouth-westChina,1947)。上述文獻寫本,既涉及到了自然物象、族群譜系、體貌特征等外在形態,又觸及到了族民性格、族群生態、宗教習俗等內在精神,對晚清民國時期涼山一帶的諾蘇社會歷史文化變遷和整體形貌,進行了勾勒、再現和構建。
就分布區域言,諾蘇族群主要以滇川黔邊為集聚區,其中涼山腹地尤為生息繁衍的大本營。“涼山自古為儸儸盤據之區,漢人蹤跡罕至其地。夷家的大本營在大涼山,……金沙江以南地帶,在云南省境之內,也是儸儸分布居留的區域”[2]。據1921年倫敦出版的《在未知的中國》載,諾蘇地域空間大致介于東經102-104度與北緯26-28度間,川滇交界的大小涼山地區則是其腹心地帶[3]。該地帶正是柏格理有關諾蘇形象書寫和構建的中心區域,1903年11月至12月間,柏格理曾不避艱險跋涉其間,零距離接觸了“大本營”中的蕓蕓眾生,深度體察并主動融入了諾蘇各家支的日常生活。
客觀上講,柏格理同西南諾蘇民眾的有情結緣,并非僅僅局限于涼山腹地一處,而是遍及滇川黔邊廣袤地區,時間幾近貫穿其宣教西南的28個春秋。因此,柏格理視閾下的諾蘇大眾形象書寫,歷經了一個長時段大空間轉換過程,大致包括起、承、轉、合四個時期。質言之,起于昆明城郊的意外相遇,承于昭通城外的深情北望與起心動念,轉于涼山腹地的體驗感知,合于黔西北安氏土目轄地苗疆長時段認知。
1889-1892年間,柏格理暫居時稱云南府的昆明,其間在走訪城西北一村寨途中初次遇見了他所稱的諾蘇人,并即刻注意到諾人不僅衣著上而且在體貌上均大別于漢人。這次不經意間的相遇,既在柏格理腦海中烙上了有關中國非主體民族形象的初始印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作了日后將傳教對象由主體民族轉向非主體民族的機緣。恰如《柏格理傳記》所言:“他對于土著族群的興趣日益濃厚。在置身于幾百萬反應冷淡的漢族人中時,他的頭腦中卻在設想贏得這個范圍之外的群體。”[4]510
待到從昆明經東川并會澤再返昭通后,城郊的一次隔岸北望,再次激發了柏格理決心涉江北上深入諾地的意志。終日置身于昭通城內漢民族及其儒釋道文化中的他,利用閑暇策馬登上城郊涼風臺高地,舉目遠眺金沙江北岸諾蘇腹地。遠方仙境般的自然風景和生息其間的神秘族群,仿若磁石般緊緊拽住了他的心,攝住了他的魂。“諾蘇地域對于我來說是一個遠在天邊的仙境,是我夢寐以求訪問的勝地”[4]34。當然,真正俘獲柏格理內心的,絕非諾區外在的自然風情,而是諾民內在的精神靈魂。這種渴求實地體察諾地的欲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愈益強烈。
回首十數年辛勤墾殖漢地,換來的卻是信眾寥若晨星、傳教人員傷亡過半、教會活動幾近停頓、母國民眾非議不斷的結果[5]。如此慘淡的結局,不僅引發了柏格理對內地會“立足城鎮”“面向漢人”傳教原則的質疑性反思,而且也堅定了他改弦更張該指導原則的決心,自此義無反顧地走出城墻環繞的漢族集聚區,將目光轉向了群山深處的諾蘇民眾。
1903年11月24日,力排萬千阻難后的柏格理,毅然決然地渡過金沙江,踏上了涼山諾蘇“這塊具有荒野般傳奇的迷人土地”[4]679,零距離接觸到了真實世界的諾蘇邊胞,深度參與諾蘇民眾的生產勞作、飲食起居、部族糾紛、族際交往、文化禮俗、宗教祭祀之中,實地見知和真切體察諾蘇人的外在物質生活與內在精神世界。然而,當諾地傳教活動和社會改良構想正沿著設計路徑順勢推進時,1904年7月12日黔西北石門坎地帶四位花苗的突然到訪,致使宣教對象和宣教地域再度更易。黔西北花苗的“突然造訪”和“皈依運動”,“使柏格理離開了他這項已經開始了的工作。由于無力顧及,它就再也沒有繼續下去”[4]665。盡管如此,大部分寫就于此后的著述文本——無論是柏格理自書的《柏格理日記》,還是合著的《苗族紀實》(TheStoryoftheMiao,1919),抑或是石門坎教會后繼傳教士撰述的《石門坎與花苗》(Stone-GatewayandtheFloweryMiao,1937),諾地與諾民都沒有離開過書寫者的視閾,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形象輪廓及其特征疏詮
如前所論,廣義上的《在未知的中國》函括了彼此關聯的七部著述文獻,撰述者都曾經長期在黔、滇、川毗鄰的多民族聚集區從事傳教、教育及改革活動,“既是歷史活動的實踐者,也是歷史事件的記錄者”[6]。毋容置疑,柏格理乃是其中的標志性人物。僅就近代諾蘇形象書寫的論著言,狹義上的《在未知的中國》堪稱集大成者,融游歷觀察與體驗探險于一體,是柏格理在諾蘇部族聚居點行走觀察和心靈感知的結晶,匯集了大量的考察日志和心路文獻,大凡族譜稱謂、體貌服飾、家支糾葛、部族結構、人生禮儀、民俗風情、宗教禁忌、民間傳說、經濟形態等知識,無所不包。既然任何異國形象的描寫與構建,都離不開建構者對異域觸感后的言說、記錄和書寫,那么,為了方便爬梳分類文獻,把握提煉基本精神,勾勒寫本含蘊的諾蘇族群形象,洞徹形象藏掖的思想義理,聚焦于諾蘇族群體質特征與文化面相寫本關鍵語匯的考察,將是疏詮形象外在輪廓與內在核質的有效進路。原因在于,關鍵語詞或核心術語既是把握一個時代精神運作眾多途徑中最重要的辦法之一[7],也是“構成形象最基本的元素,由此切入,卻有可能牽連出歷史、思想、精神等深層次問題”[8]168,揭示出“形象塑造者對他者的認知水平、對異文化的心態、‘我’與他者的種種關系”[8]171。
(一)繁復的稱謂
在正式走近一個陌生族群前,需大量涉獵和盡量儲備事關該族群族稱、族源及族系的知識,柏格理同諾民間的接觸也不例外。在冒險踏入諾蘇腹地前,借助“他族”的大量敘事和言說,在柏格理等輩的腦際和心間就已粗略地植下了事關諾蘇族群的印記,部分地形成了有關該族群的形象圖景和心理認知。當然,基于各種道聽途說之上的,往往是一些間接敘述類點滴知識甚至碎片信息,據此形成的印象既模糊不清也殘缺不全,難有真實公允可言。
就諾蘇言,姑且別論族支如何龐雜,階層如何森嚴,形貌如何酷似,單就族群稱謂言,繁復程度就令人瞠目。據《玀猓標本圖說》載,“玀猓 (Lolos)又作猓玀,玀玀,猓猓,盧盧,羅羅,狫狫,獠獠,盧鹿等;漢族賤之稱之為玀鬼,又常泛稱之為夷人或蠻子”[9]321。學者楊成志在通覽古今關于諾蘇記載的史籍和數十年來外國傳教士及旅行家著述后,對諾蘇復雜族稱作出了如下“正名定義”:除為數較多的國外名稱外,諾蘇族稱有自稱與他稱之別,單己稱就多達40個,另有漢稱族名九13個。考其繁復自稱與他稱成因,可歸結于“交通阻隔”“語言遞變”“慣俗殊異”“漢人誤解”與“土人心態”等五端[10]。
那么,以柏格理為代表的西方人士,又是如何稱呼和認識諾蘇族民的呢?柏格理《中國歷險記》的描述是,“有一大片尚未得到完全開發的土地,那里居住著一個勇敢的民族,他們稱自己為‘諾蘇’”[4]34。隨后面世的《在未知的中國》等著作中,柏格理又反復描寫到了同一地帶的諾民,并對其稱謂涵蘊的詞源學意指進行了大膽假設:“諾蘇或納蘇的讀音或許聽起來沒有倮倮的發音悅耳,但它不包含傷人的意思,并不對這個勇敢的民族造成侮辱,多少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尊嚴。”[4]347
不僅如此,在論及諾蘇族稱問題時,柏格理還將諾民同母國的威爾士人等量齊觀,并為二者間歷經的被驅趕、遭擠壓、受欺凌的相似命運鳴不平。認為當時的漢人對涼山深處的諾蘇部族并不友好,并在后者身上貼上了各種惡毒罵名和負面標簽。“稱他們為‘蠻子’和‘羅羅’,此類稱呼則最遭這些部族人的憎恨”[4]186。繼而指出,倮倮稱謂之所以被視為嚴重的忌諱和極度的輕蔑,根本原由在于“漢人所喊的‘倮倮’一詞,在書寫時經常要寫成一個‘犬字旁部首’”[4]347。
檢閱本土史料,如此現象在當時特殊歷史時期與特定文化語境下著實存在。無論是主體漢民族還是滿清統治者階層,都不時采用獦獠、蠻夷等貶義語匯,侮稱包括諾蘇在內的非主體族民。譬如,《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所輯奏折中,“猓地”“猓患”“猓夷”“生猓”“夷猓”“猓胥”和“猓人”等指代諾蘇之地、諾蘇之患及諾蘇之民的蔑稱,就大量存在。甚至在民國時期人類學家林惠祥和鳥居龍藏等中外學者的著作中,上述貶稱惡名仍頻頻出現。
為何如此?在柏格理看來,根本成因在于漢人對諾蘇的長期恐懼所致,借《在未知的中國》言就是“害怕蠻子”。“對于漢族人而言,中國西部自治的諾蘇地域是一片令他們感到非常可怕的土地。傳云這里居住著兇頑之徒”[4]175。如此的恐懼,在當時并非個別現象,而是“充斥于所有鄉村地方,并且延伸到三個省份”[4]185。
(二)壯碩的體格
人種體質特征往往是映入觀察者眼簾的第一表征和初始印象,也是造成視角沖擊的直觀內容。如前所論,柏格理同諾民的初次相遇是在昆明城外,僅匆匆一瞥,便在腦海中得出了諾人不僅體貌大別于漢人而且衣著迥異于后者的判斷。等到進入涼山諾地深處,通過近距離觀察后,對諾民體質形貌特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盡管諾蘇族群內部支系繁多,地域間語言反差性大,但是形體外貌差異性并不大。較之同時期同地域內的漢苗民眾,諾蘇人普遍有著彪悍的體質形貌,不僅面部輪廓差異明顯,而且體格上更為魁梧,體質上更為壯實。成書于民國時期的《中國西南民族分類》,乃是民族學家馬長壽深入涼山諾蘇腹地調查后的著述,在論及諾人體質形態時,曾以體格高大、胸膛聳厚、軀干直挺、膚色黃褐、發直微曲、面長而尖、眼平而直、鼻長而薄、唇薄而直、齒堅而齊等語匯進行輪廓描述。如是的體貌特征,同《玀猓標本圖說》中“玀猓之體質為身長,鼻高,頭形長,膚色淡褐,四肢細長而強健”[9]321-322描述相一致,也與法國漢學家亨利·高爾迪埃(Henri Cordier)稍早前的敘述基本吻合。在1907年版《儸儸人及其現狀》里,高爾迪埃稱大小涼山及周邊地帶的諾蘇人不僅“深目”“鷹鉤鼻”“膚黑”,而且“一般身材較高,在1.7米至1.8米之間,體型筆直,圓錐形的軀干,寬寬的肩膀,勻稱美觀,上肢和下肢的比例十分協調且肌肉發達,還有其它特點:額頭高、直,容貌端正,看不到額骨骨突的凸出,一張完美的橢圓形臉蛋;眼睛不斜,尤其明亮”[11]。概上所述,諾蘇人普遍具有身材高大、體格健碩的形貌體征。那么,柏格理等輩于其論著中又是怎樣述說諾蘇人體征的呢?
品讀相關著述文本即可感知,對于包括諾地諾民在內的西南各地物象及民眾,柏格理都有著精微的觀察和細膩的描寫。不僅對族群高度重疊并生的西南現狀有透徹洞察,而且由小及大對整個中國的民族多樣性與文化多元性情態有清楚把握。“旅行者不管取哪條道路進入中國,他立刻就會覺察身處于一個充滿新奇的國度里,就會發現身處于一個看起來在衣食住行諸方面與歐洲和美國均截然不同的人群中”[4]194。
客觀地講,柏格理筆下的近代諾蘇體貌描寫,好似一幅簡約人物畫,著墨不多但線條清晰,沒有五官和肢體寫實性表述。在他眼中,諾蘇人類似于藏族而不是漢人,身材高大,體格健碩。“這個民族的外觀好、健壯、高大”[4]396。如此的形貌特征,同國內民族學家和海外漢學家的判別高度吻合,彼此互印。
(三)別異的衣飾
概覽柏格理《在未知的中國》等著述,即可獲得如是印象,無論裝束服飾還是發型式樣,諾蘇人都有別于其他族群。論其著裝,他們日常“穿著獨特的粗布服裝,上面還有更為豐富的刺繡圖案。從他們的面部形象顯示出,這些人太與眾不同了”[4]509。
是耶非耶?比對當時國內本土文獻相關記載便可明了。上段引文出自《柏格理傳記》,是柏格理暫居昆明期間于城西北巧遇諾民時族民所著服飾的寫照。對照《中國西南民族分類》即可明見,引文所述衣著特征,與滇中時稱妙保亻羅的女性裝束相符,即“女衣胸背繡花紋,前不捲頸,厚長曳地;衣邊彎曲,無襟帶,著時,自頭籠罩而下”[12]21。
等到進入涼山諾地并零距離接觸到大量諾民后,柏格理即刻注意到了大山深處諾民衣著服飾的別異性。那就是,男子的典型衣服是一件寬大的山羊毛斗篷,斗篷里面穿著一件上衣和一條棉短褲,而女人也穿一件寬大的斗篷,里面穿一件棉的短上衣和一條襯裙。如此記述,通過《中國西南民族分類》“川南倮亻羅男女均著圓領大衣,長拖過膝。男子內著短衣與袴,腰束以帶”[12]21等語句得到了印證。
除衣著外,諾蘇男子的發型和婦女的妝飾也是柏格理等關注的重心所在。就發型言,男子“左耳上皆懸掛著長長的耳飾。每人緊緊包扎的頭飾左側,豎起角或椎狀的英雄髻,在火光的輝映下,他們的面容顯得更具光彩與歡快”[4]318。諾蘇婦女(女孩)一般戴著大型的傳統頭飾,“沒有成婚的姑娘只梳一條辮子,成婚的女子卻有兩條辮子”[4]245。
如此這般的細致描寫,在柏格理關于諾蘇民眾的文字中不時閃現,宛若一幅幅素描寫實圖,較為真切地刻畫出了此時此地此人的形貌特征與服飾特點。
不難發現,如果說柏格理在勾勒諾蘇民眾體質相貌時惜墨如金,頗似簡筆畫風格,那么在論及諾蘇人的服飾特別是諾蘇女性的衣著妝飾時,往往思如泉涌,走筆如飛。如對趕場天鄉村集市上不同種族服飾身影的描繪,可謂觀察入微,筆底生花。“身著膨脹似囊褲子的漢族小腳婦女縱然是鄉場里眾多女人中的一道風景線,但是她們跛來跛去的不自然的扭捏動作,與行走快當、徑直向前、身姿優美的山里婦女比起來就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山里的婦女根本不屑于纏起她們的雙足,她們真是邁出了婦女勝利的步伐。苗族婦女梳著兩條辮子,諾蘇婦女身著幾乎掃到地面的長裙”[4]196。
顯然,柏格理把開放自由的鄉村集市作為觀察諾蘇人衣著體態的空間場,將少數民族族民與主體漢民族民眾置于同一圖景下審視,意在借助見證敘事方式植入本位文化觀念和價值立場,在集中展現諾民衣飾體態相系的族群文化風情的同時,將漢民族及其主要依存的倫理制度文化做背景化處理,從而起到既諧戲和鞭撻漢民族陋俗又使自己處于隱性狀態的文化觀念和信仰價值得到表達的雙重功效。
(四)天然的族性
早在決意冒險渡江進入涼山腹地前,身居江南昭通城內中的柏格理,時刻置身于主體民族漢族中,而充塞其間的,往往是關于江北涼山諾蘇腹地族民的各種傳聞。那就是,腹心地帶乃罪惡淵藪之地,陰森恐怖,兇險莫測,冤家械斗,年復一年;腹地之民,蒙昧未化,茹毛飲血,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種種謠傳不絕于耳,源源不斷地被灌輸進柏格理腦海。“對于漢族人而言,中國西部自治的諾蘇地域是一片令他們感到非常可怕的土地。傳云這里居住著兇頑之徒,占領那些雄偉大山的人們具有強硬的秉性,有可能會做出任何種類的邪惡行徑”[4]175。
待到深入其間,尤其是隨著體驗時間的向前延伸,同諾蘇腹心地帶民眾的接觸日益頻繁,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嵌入愈益深入,柏格理的體察也呈現出了一種遞進增長態勢,書寫度也由開初的外在皮相淺表描述,轉入了對族民內在性格品質和精神氣度的觀照和雕琢。諾蘇那種略帶粗魯、強橫豪放的習氣,那種未經修飾雕琢的自然秉性,成為了柏格理不斷展現和述說的重要內容。而長篇書寫文本所折射出的諾民性格和精神,大致可以濃縮成“勇猛”和“蒙昧”兩個關鍵詞。
諾民勇猛驃悍的族民性格,無論是在柏格理自身的記述中還是在其他敘述者的寫本里,都是展現的重心所在。敘述者采用多重內聚焦型敘事視角,依憑在場體驗的感受和意識進行敘述,將入乎其內的在場體感,同出乎其外的心靈書寫,彼此貫通又互為補充。“這里的人們以高山為家,過著一種無拘無束、粗曠豪放的生活,為了保護高山里的家園,他們隨時準備同任何入侵者決戰,甚至不惜犧牲寶貴的生命”[4]52。其中惹黑部落族民尤為如此,他們“都是驍勇善戰的斗士,自尊心特別強,對于任何輕視都很敏感,且翻臉不認人”[4]56。
為能凸顯諾蘇民眾與眾不同的剽悍勇猛性情,柏格理還不時運用比較參照法則,在體察和揭示諾民習性的同時,對同時期相鄰空間內其他民族的性格特質進行了對比表達。譬如,諾蘇人“非常不同于苗族人。代之以后者膽怯和自我輕視性格的是,前者具有一種強烈的進攻傾向,一種隨時樂意利用最微小的時機選擇一場爭吵的習慣,一種原始人群更喜歡采取軍事行動的十分明顯的激情”[4]516。
憨厚而蒙昧,是諾蘇人的另一族性特征,主要表現在既崇巫尚鬼又不諳世情等面相上。大凡對未聞之事、初見之人、未睹之物,他們都極度好奇卻又無限恐懼。“他們或許不似印度人那樣崇信宗教,但他們又表現出深深的迷信色彩,并且害怕未知的事物,生活在對未知力量經久不衰的畏懼之中”[4]186。對此,柏格理傾注了大量心力,將融入諾蘇民眾日常生活中所捕捉到的點滴素材轉化為筆墨文字,對諾蘇人初見黑人的失魂落魄情狀,初睹望遠鏡和照相機時過度反應情緒,投擲石塊游戲中誤認柏格理身藏“魔法”后的膜拜心態,面對“折疊椅”機械原理不知所措時的尷尬窘態,對“洋娃娃”無比渴望與莫名惶恐,都進行了敘述和評說。
當然,上述性格特征的化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既承續了諾民本然的族性基因與性能,也映射出環境對生命種族遺傳與生命繁衍過程的影響信息。在深究諾蘇族民樸實無華的粗獷性格的成因時,柏格理把千百年來天荒未破、孤寂封閉的生存環境視為一個根本性要素。
在中國,地處偏僻的居民非常迷信,有時他們就很容易輕信類似的可怕傳聞,父母親會仔細地照看好小孩,生怕心愛的小寶寶被兇惡的洋鬼子殺死。尤其是在中國西部的絕大多數居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機會見過黑人。因此,當一位英國黑人到來時,便立刻引發了人們心中的迷信,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謠傳與誤解。喻之為天外妖孽的有之,言之為食人惡魔的有之,視之為地獄鬼怪的有之,各種流言蜚語不脛而走,以至于“許多諾蘇和苗族的少男少女看見他時,一定會被他嚇得發抖”[4]58。
同樣令敘述者驚愕不已的是,諾蘇人初次直面望遠鏡和照相機時所表現出的那種既無限恐懼又極度好奇的反常心理。“望遠鏡在漢語里被稱為‘千里鏡’,在此地被說成是‘千里槍’,用‘槍’代替了最后一個‘鏡’字。因此,它又被誤認為是一支神奇的槍,不論距離多遠,也不論有多少人,只要在其視野范圍之內,就能殺死通過它所看到的任何人”[4]36。又如,經反復勸說,四位諾蘇男人終于壯著膽走向了照相機。然而,“在我按下快門之前,他們就從‘洋人的新式槍’的槍口下溜走了,他們人人皆知,這種‘槍’可能具有攝人魂魄的效力。其后,另外一伙人被用好話哄騙過來,這些人帶著經受嚴峻考驗的大丈夫氣概站立著,但仍不免表露出相當害怕的神色,并在不斷地發抖”[4]191。
為何如此?《在未知的中國》給予了如是解答:“一個人實際上所持有的武器不見得在任何場合都是武器,但一個人被當地有充分想象力的人猜想所具有的武器才是有威力的武器。”[4]208這就是望遠鏡這支“槍”被杜撰成效用奇異、神力無限的根本成因。同理,照相機之所以被神化成具有機關槍相仿的攻擊力,相機操控者(柏格理)之所以被堅信魔力無邊,其形成機制與此同然。
更讓人匪夷所思地是,諾蘇人尤其是婦女,連對表的滴答聲都驚恐異常。“兩位歌手拿著我的表看了一看,表的滴答聲把他們嚇了一跳。身穿豪華長袍的寡婦對手表也深感興趣,并試著讓其他一些婦女吧它放到耳朵上聽一聽。 她們這樣做時顯得特別害怕。她們對魔法的恐懼感太強烈了”[4]283。
總之,在形象書寫者眼里,不管是奪命千里槍還是攝魂照相機,也無論是表的滴答聲還是紅色羊毛手套,它們被神秘魔化的真正推動力都源于蒙昧和迷信。易言之,是無知造就了如此威力強大的武器。
(五)化外的體制
尚未動身渡江前,通過比較觀察金沙江兩岸族際關系、生產方式和社會機制間的差異性,柏格理對江北諾蘇腹地社會經濟情狀有了大致了解,并作出了諾蘇領地好像一個中世紀時代的歐洲封建王國,諾蘇民眾實際上還處于自治狀態,保持著完整的封建體系的論斷。待到實地考查和參與式體驗階段,通過著力考察族民家居條件、生產生活方式、經濟運行模式、族內婚姻制度、家支部族關系、族內階層結構等面相,不僅基本上印證了柏格理當初對諾地社會經濟狀況的預判,而且對腹地諾民的生存狀態有了更為細致的觀察、更為準確的把握和更為深入的揭示。
涼山諾蘇領地的族民,“獨立自主地生活著,保持著他們自己的習俗,自己管理自己”[4]186。在該體制下,“諾蘇地主的統治,可謂該地域的一大特色,而無論在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的社會里,已經沒有高高在上擁有如此權力的領主了……他們承認中央政權的統治,可是由于他們在該地域內的特權,所謂中央統治是不完全的”[4]704。在柏格理看來,上述定論的得出,主要依據于如下兩個封建體制特征:一是“我們發現在中國這個未知部分保持著它自己的完整封建體系。位于這個體系頂端的是土目,或者土司,與歐洲封建體系的第一等男爵相當。往下是黑諾蘇,經常被不恰當地稱為黑骨頭。……低于他們的是白諾蘇,也被不盡恰當地稱為白骨頭。繼續往下的是奴隸”[4]255;二是諾蘇領地的每戶土目首領人家都有奴隸或奴仆。
論及該封建體制下的婚姻制度,柏格理曾以一言蔽之,“諾蘇一般都實行在諾蘇內部通婚”[4]230。這一經驗性判斷,與后來人類學家的論斷互為吻合。據林耀華《涼山夷家》載:“儸儸階級極嚴,黑夷白夷之間,絕無通婚的可能,此即所謂階級內婚制(Class endogamy)。黑夷男子只能在相同階級中擇女婚配。白夷奴隸自成階級,互相擇偶。……黑白不婚已成慣例。惟黑男與白女奸通者罪可寬容,所生子女通常稱之為‘黃骨頭’,即‘黑骨頭’之男與‘白骨頭’之女所生的雜種。……儸儸有氏族組織,氏族之內不許通婚,嫁娶必于族外求之,謂之族外婚制(Clan exogamy)。”[13]
那么,在這樣的社會組織結構下,諾蘇領地上存在著何種與之相應的生產模式與經濟狀況呢?對此,柏格理結合土地在部族社會組織構建中的相互關系,運用在場獲取的知識進行了表達。
就經濟運行模式言,土目們控制著諾蘇人居住區域的大多數土地。在留下部分領地自己經營后,“余下的土地就以十分輕微的租金分配給黑諾蘇們,除租金外,黑諾蘇必須為自己的領主提供各種役使,繳納微不足道的貢賦,經常為實物貢賦”[4]256。黑諾蘇們必須效忠于封建土目,以此作為賜予他們土地的回報。“黑諾蘇必須在人身與役使方面服從領主的支配,……差不多所有土目和黑諾蘇都占有一定數目的白血統侍從,侍從之中有一些人是奴隸,他們的財產、人身和家庭全處于自己主人的絕對控制之下”[4]257。精細的觀察、精到的體認和精妙的文字,較為客觀準確地表達和反映了諾區以土地為基礎的經濟關系。
在以第一人稱直接敘事方式對諾蘇領地的族內社會與經濟生態進行敘說的同時,柏格理還適時就其非合理性提出了批評,并旗幟鮮明地闡明了立場態度,那就是,這一陳舊而落后的體制應當徹底根除。“由諾蘇土目統治的土地,意味著一片充滿陰謀、法律不行、道德敗壞、劫掠、權奸、謀殺及大量其他類似行為的土地,它的恐怖氣氛不由令人沉思,若是貼近它去體驗一下,還將感知更大的恐怖氣氛。……現在,是中國政府徹底粉碎這些無法無天的土目的全部權力的時候了。它是中國文明中的一處污漬,如果中國還想自立于世界列強之中的話,就必須把它清除。”[4]278
(六)“蒙昧”古樸的意識
毋庸諱言,較之于對諾民外在體貌、生存環境、物質條件、經濟狀況等面相展開的敘事言,更讓柏格理等輩關注的,則是諾蘇族民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等事關心靈、靈覺、神明層面,如人生禮儀、宗教禁忌、巫術崇拜,等等。
禮儀是一種象征符號,一種身份認同,也是一種交流媒介。符號是人與文化邏輯相關的中介、橋梁和紐帶,恰如卡西爾所言,“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14]。
人生禮儀或生命禮儀,主要對生命個體在不同年齡階段或人生歷程關鍵節點上的典禮式紀念,通過象征性儀式活動或隱喻性符號彰顯出蘊含其間的文化概念和思想情感。婚嫁、生養、喪葬等重要禮儀莫不如是。
由于諾民歷來盛行崇巫尚鬼之風,因此作為民間信仰伴生物的宗教禁忌與巫術崇拜也自然彌漫著整個諾蘇領地。宗教禁忌本質上是人們信仰和崇拜神秘異己力量和神圣對象的一種宗教行為,而以降神驅鬼儀式和咒語為主要內容的巫術崇拜風俗更是盛極一時。
文化是人類知識、信仰和行為的整體。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將文化定義為行為化的符號化文獻,認為“文化有其內在的認知結構,有其‘文化語法’”,而“文化的語法不僅僅是以語言、認知寫成的,也是以神話、宗教、藝術、民俗乃至天文歷法、喪葬典儀等文化本文和文化話語寫成的”[15]。因此,諾蘇腹地存在的各種人生禮儀、宗教禁忌觀念、巫術崇拜習俗等,無不是族性文化和地域文化經久融合而成的地方性經驗。當然,從該時期的傳教士著述特別是柏格理撰寫的文獻字符中,映射出了諾蘇文化形象的基本輪廓,就其指涉喻義和特征言,可以濃縮成“迷信”與“原始”二詞。
客觀而論,對于諾蘇宗教禁忌及巫術符咒等事關自身宣教事業成敗與否的精神層面,柏格理觀察極為精細,體味尤為深切,記述相當完備,言辭十分尖銳,評價非常犀利。
在言及諾蘇人的宗教信仰時,柏格理得出的總體印象是,“他們或許不似印度人那樣崇信宗教,但他們又表現出深深的迷信色彩,并且害怕未知的事物,生活在對未知力量經久不衰的畏懼之中”[4]186。使柏格理頗感意外的是,盡管佛教文化遍及西藏各地,對藏民族精神世界的影響宛若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然而相對于毗鄰聚居的涼山地帶諾民言,佛教的影響結果迥異。用柏格理的話說就是,“在諾蘇地域我卻找不到佛教的絲毫蹤跡。在那里沒有寺廟,沒有和尚,沒有偶像與一妻多夫制”[4]287。
論其具象性表現,主要反映在房屋營造的“居”、文字運用的“言”與日常禁忌的“行”三方面。
言其“住”,諾蘇崇尚自然并對妖魔鬼怪無限恐懼的心態和觀念,體現在族民屋舍構造上就是“在任何地方我都沒有發現房屋上有瓦。他們所蓋的不是草就是樹皮。對精靈的恐懼,明顯地存在于他們之間”[4]682。
論其“言”,語言是標志對象世界的符號系統,更是對象世界存在的標志,加達默爾就此提出了“誰擁有語言,誰就‘擁有’世界”[16]的論斷。“諾蘇具有一種文字性語言和文學作品;但數量不多的書籍實際上為巫師和醫者所壟斷”[4]681。由于諾蘇人非常迷信,所有人都在巫師(畢摩)的統治之下。“畢摩是神圣的職業,享有極高的社會聲譽,故有‘畢摩在座,土司到來不起身’之說。畢摩是彝語的音譯,‘畢’指的是‘念經、誦經’之意,‘摩’指的是掌握一定知識文化的長者”[17]48。作為部落精神牧師、知識精英、文化代言人的畢摩,自然主宰著話語表達權,用柏格理的話就是“實際上巫師成為持有諾蘇語言文字知識的惟一社會階層”[4]340。
眾所周知,諾蘇傳統文化的中心是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的中心是畢摩文化。畢摩文化是依據彝族古代先民世界觀和認識觀,以早期的信仰和崇拜為基礎而一步步發展,并通過畢摩的傳承和開新所形成的道德觀和禁忌觀。據此不難理解,為何柏格理會抱怨道:“我得到的諾蘇文字書籍差不多都是對付疾病與魔鬼附身的。這些書中保存有巫師行當的全部符咒,用以驅逐鬼怪,及咒罵病魔。”[4]343
觀其“行”,諾蘇人對魔鬼的恐懼觀念,在忌諱言行上也有顯明的體現。譬如,“這個地方的男子竟沒有一個人長連鬢胡子或小胡子,發問后被告知,諾蘇男子認為長這些東西不吉利。他們的胡須在青少年時期就全被拔掉,并不許它再長出來,只有極少數人例外,是為防范某些特殊的令人討厭的魔鬼”[4]232。
正是基于上述形象和客觀事實,柏格理將涼山地帶諾蘇民眾判定“為鬼怪所支配”的族群,且對“巫術崇拜”在族民的人生禮儀、祖靈祭祀、風俗習慣、衣食住行中的浸潤度和影響力,進行了揭示和批駁。遍覽柏格理所有撰述文本,在事關諾蘇領地宗教禁忌、巫術符咒、喪葬習俗等內在精神的描寫論述上可謂獨運匠心,無論是取用的視角,選擇的面相,還是解釋的思路和揭示的本質,在挖掘力度和展現程度上,都非其它著作所能比擬。究其原因,入華傳教士常常視上述面相為妨礙其收獲東方靈魂的文化屏障。柏格理“恭承天命”弱冠東渡的目的,并非在于游歷華土以飽覽風情,而是志于引導所謂“異教徒”皈依上帝,“拯救世人擺脫罪惡,為基督征服中國”[18]。易言之,“基督教唯我獨尊的上帝觀和拯救全人類的使命感成為傳教運動的內在動力”[17]7。為了建立一個有利于基督教傳播的社會文化環境,讓基督信仰根植于華人心田,實現福音化中國的結果,就得對妨礙基督教傳播的民族心理和文化障礙的“異質性”“落后性”和“孽根性”進行改良、置換甚至根除。
三、現實之鏡
近代入華傳教士與西南諾蘇民眾互動關系,總體上存在著實地考查時間短暫,對領地牧場上的靈魂收獲有限,相互間文化影響未能持久深入等不足。但無法否認的是,以柏格理為代表的入華傳教士,借助相遇、接觸、嵌入等漸進形式,帶著溫情長期跋涉諾區高山峽谷,用異域人的眼光和心靈,打量和感覺了腹地深處蕓蕓眾生的外在生活常態和內在精神世界,從而留下了一批事關諾民歷史風貌和大眾形象書寫的著述文獻。基于諾蘇部落中長時間游歷觀察、探險體驗的《在未知的中國》,便是其中的翹楚之作,既具洞察力又懷獵奇心。它宛若一面現實之鏡,較為清晰地映照出了該特定歷史語境下西南諾蘇民眾的文化景象,勾勒出了普羅大眾的生活圖景和形象輪廓。就形象構成面相言,主要包括繁復的族群稱謂、彪悍的外貌體征、別異的衣著服飾、自然質樸的族群性格、化外的封建體制以及“蒙昧”古樸的文化意識等六個層面;就形象建構策略言,不僅潛藏著一個“見證敘事”“英雄敘事”“啟蒙敘事”三重遞進互動模式,而且化生于一個西方話語他者、國家政權他者和諾蘇本土他者交融互攝的文化語境體系;就形象同現實參照系間契合度言,盡管受到歷史場和文化場雙重影響,從而在視角切入、面相擇取、書寫模式上存在著明顯的本位痕跡,但是該西鏡東像總體上較為真實。比照《中國西南民族分類》的相關論述,便可了然。“獨立倮亻羅者,自古迄今,蓋未歸向于漢族,現其民族,憑山居險,割據一方,經濟自足,武力自衛,婚姻自通,其所行之階級制度與禁忌似專為區別‘我族’(We-Group)與‘汝族’(You-Group),以抵抗漢族之人口與文化推進而設”[12]1。
毋庸諱言,就文化義理言,《在未知的中國》所塑造的近代諾蘇形象及其各個層面,無不承載著相應的文化寓意,粘附著書寫者自身文化的生命氣息和評價標準,體現著“他觀”審視角度與認知心態。質言之,繁復的族稱隱含著沉重的社會認知心態,壯碩軀干下掩藏著一顆落拓不羈的心,奇異的衣著服飾喻示著族性身份焦慮意識,自然質樸的個性體載著化外無知的悲愴之情,化外的封建生態體制表達出差序格局與階層鴻溝的命運桎梏,“蒙昧”的族群文化凸顯著文化異質性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