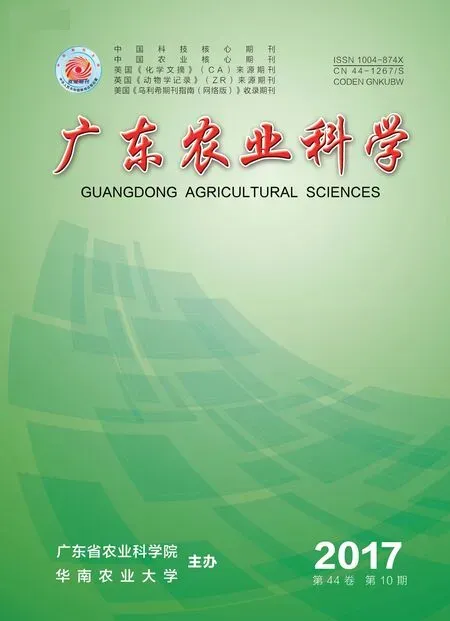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實(shí)施績效研究進(jìn)展及展望
楊冬梅,朱述斌,趙 馨
(1.江西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新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
為了進(jìn)一步激發(fā)林農(nóng)林業(yè)生產(chǎn)動力,2003年我國開始在福建、江西等省份實(shí)施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以下簡稱“林改”)試點(diǎn),2008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截至目前,實(shí)施了10多年,已經(jīng)在經(jīng)濟(jì)、生態(tài)和社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jǐn)?shù)據(jù)顯示,與2004年相比,2015年的林地用地面積增長了24.97萬hm2,增幅為2.39%,森林覆蓋率由59.0%提高到60.0%,森林儲蓄量由3.25億m3增加到4.08億m3。在這期間林業(yè)每年的增加值都處于上升狀態(tài),與2004年相比,林業(yè)產(chǎn)值增加值增長了246.9%。除了林業(yè)資源和產(chǎn)值發(fā)生很大變化外,新型林業(yè)經(jīng)營主體、林業(yè)收入來源、林權(quán)流轉(zhuǎn)等方面也發(fā)生了良好的轉(zhuǎn)變。但是在取得一些效果的時候,也出現(xiàn)一系列問題影響林改績效的持續(xù)提升。為此,我們首先要了解:目前對于林改的研究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在這些成果中哪些獲得共識,哪些還存在分歧,未來的研究又如何?這是我們研究的基礎(chǔ)。
為進(jìn)一步了解現(xiàn)狀,我們于2017年9月份在中國知網(wǎng)(CNKI)選擇2003—2016年,以“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為檢索對象的記錄共有6 406條,其中“中國學(xué)術(shù)期刊網(wǎng)絡(luò)出版總庫”有3 869條、“中國博士學(xué)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有54條、“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xué)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有356條。2008年林改在全國范圍內(nèi)展開,為了進(jìn)一步了解研究的變化情況,選擇2008—2016年的文獻(xiàn)數(shù)量加以對比,其中“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檢索結(jié)果如圖1所示。

圖 1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檢索結(jié)果
1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實(shí)施績效
一項(xiàng)政策的實(shí)施效果如何,可以從經(jīng)濟(jì)、社會和生態(tài)等方面來反映,劉濱等[1]認(rèn)為經(jīng)濟(jì)績效往往與制度變遷聯(lián)系在一起,它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的行為努力結(jié)果,以及制度變遷后體現(xiàn)出來的效率與效果。大致來講,可以將經(jīng)濟(jì)績效劃分為主觀績效(如社會公平程度的提高)和客觀績效(如收入增加、生產(chǎn)成本降低)兩大類。
1.1 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評價指標(biāo)體系分析
自新一輪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以來,很多專家學(xué)者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評價方法對林改實(shí)施績效評價指標(biāo)體系進(jìn)行了研究。主要集中于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其中橫向分析基本都是從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社會效應(yīng)以及生態(tài)效應(yīng)3個方面進(jìn)行構(gòu)建相關(guān)研究,縱向分析主要從國家、政府、企業(yè)以及農(nóng)戶視角著手。
在橫向分析的研究中,呂杰等[2]從宏觀角度評價了遼寧省林改初期在經(jīng)濟(jì)、社會和生態(tài)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楊培濤等[3]借鑒國內(nèi)外專家和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經(jīng)驗(yàn),在經(jīng)濟(jì)、社會、生態(tài)功能等方面建立9個評價指標(biāo)對廣西省2個林改試點(diǎn)的綜合績效進(jìn)行了研究;康媛[4]根據(jù)指標(biāo)選取原則,以目標(biāo)法和借鑒現(xiàn)有文獻(xiàn)研究中指標(biāo)體系并根據(jù)廣東省林改的實(shí)際情況,將廣東省林改績效評價指標(biāo)體系分為4個層次,每一層次分別選擇反映其主要特征的評價指標(biāo),共選取34個評價指標(biāo),分別對應(yīng)資源增長、農(nóng)民增收、生態(tài)良好、林區(qū)和諧四大準(zhǔn)則層;趙鋒泓等[5]從經(jīng)濟(jì)、社會和生態(tài)等3個層面構(gòu)建林業(yè)總產(chǎn)值等20個指標(biāo)的評價體系;聶應(yīng)德等[6]研究了林權(quán)制度改革對農(nóng)村治理帶來的積極社會效應(yīng)。
在縱向評價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從林農(nóng)的角度研究。例如,林琴琴[7]根據(jù)福建省10個縣的林改跟蹤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從林農(nóng)對林改政策的知情程度、林改政策了解程度、林改參與度、對林改政策的滿意程度等方面對林改績效評價進(jìn)行了定量分析;陳幸良等[8]同樣從林農(nóng)的角度研究了集體林產(chǎn)權(quán)安排是否對林農(nóng)收入產(chǎn)生影響,以及影響的正向和負(fù)向關(guān)系;榮慶嬌[9]從農(nóng)戶生產(chǎn)要素投入、生產(chǎn)效率以及農(nóng)戶收入及其結(jié)構(gòu)等方面來研究林改績效。除了從林農(nóng)角度來研究,還有學(xué)者從林區(qū)建設(shè)、林產(chǎn)品生產(chǎn)的角度研究林改績效,如廖靈芝等[10]利用實(shí)地調(diào)研數(shù)據(jù),從林區(qū)建設(shè)的視角分析林改的績效,主要采用客觀數(shù)據(jù)描述性統(tǒng)計方法,而他所選取的指標(biāo)是山林糾紛調(diào)處力度、基層林業(yè)隊伍建設(shè)、林業(yè)服務(wù)體系等3個方面,得出林權(quán)糾紛發(fā)生率逐年下降、基層林業(yè)隊伍建設(shè)逐步完善;鄭風(fēng)田等[11]對林改績效的研究主要從林產(chǎn)品視角進(jìn)行,采用實(shí)證分析方法研究林改對林農(nóng)林產(chǎn)品生產(chǎn)效率的影響。另外,也有從“結(jié)構(gòu)-行為-績效”縱向和橫向綜合分析框架結(jié)構(gòu),以廣東林改實(shí)踐來研究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
1.2 評價方法的應(yīng)用
在林改實(shí)施績效的評價方法選取時,不同學(xué)者采用的方法和數(shù)據(jù)類型不盡相同。林琴琴等[12]用截面數(shù)據(jù)分析林改實(shí)施的績效,鄭風(fēng)田等[11]采用分成地租模型分析林改對林產(chǎn)品生產(chǎn)效率是否有效,康媛[4]采用時間序列數(shù)并借鑒以往學(xué)者采用的林改績效的評價體系對廣東省的林改績效進(jìn)行分析。此外,還有學(xué)者采用福利經(jīng)濟(jì)學(xué)、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博弈論等理論分析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的限制性因素。陳幸良等[8]采用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分析了林改政策對林農(nóng)增收的影響因素;榮慶嬌[9]采用DEA—Malmquist生產(chǎn)指數(shù)方法對實(shí)施林改主體改革及配套改革后的樣本農(nóng)戶總收入和農(nóng)業(yè)收入全要素生產(chǎn)效率進(jìn)行了測算與分解,運(yùn)用SFA隨機(jī)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法測算了樣本農(nóng)戶總收入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技術(shù)效率變化和技術(shù)進(jìn)步變化等來研究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得出林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林農(nóng)增收;楊培濤等[3]、趙靜等[13]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相應(yīng)的評價體系對林改績效進(jìn)行相應(yīng)分析。
1.3 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評價結(jié)果分析
對于林改績效評價的實(shí)證研究,大部分研究結(jié)果都是滿意態(tài)度較高,認(rèn)為林權(quán)制度改革富有成效,具體體現(xiàn)在林改后農(nóng)民收入增加、森林資源增長、農(nóng)民營林活動增加等[2,14-16]。我們主要從經(jīng)濟(jì)、社會及生態(tài)效應(yīng)三大方面進(jìn)行綜述:
第一,林改的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林權(quán)制度改革的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主要是從農(nóng)民收入、投入生產(chǎn)效率方面展開論述,陳幸良等[8]認(rèn)為經(jīng)濟(jì)、社會、生態(tài)三大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應(yīng)分別占50%、30%、20%,顯然,在林改績效的評價中,首先要考慮其經(jīng)濟(jì)效益。大部分研究者證明林權(quán)制度改革對農(nóng)民增收、林業(yè)投入、生產(chǎn)效率產(chǎn)生了良好的作用,如王良桂等[16]認(rèn)為,集體林改增加了林業(yè)收入,使林業(yè)收入在農(nóng)戶家庭收入中的貢獻(xiàn)率得到了提高,較之非林業(yè)收入,林業(yè)收入增長幅度更加明顯;孔凡斌[17]根據(jù)林業(yè)統(tǒng)計年鑒數(shù)據(jù)分析得到自2003年林改以來,林業(yè)系統(tǒng)到位各類建設(shè)資金在逐年增加,到2007年林業(yè)系統(tǒng)到位各類建設(shè)資金達(dá)793億元,是林改前的兩倍多,可以看出林業(yè)資金的投入不斷增加;榮慶嬌[9]研究發(fā)現(xiàn)林權(quán)制度配套改革措施(林業(yè)稅費(fèi)、造林補(bǔ)貼及天保工程)對樣本農(nóng)戶的總收入和農(nóng)業(yè)收入全要素生產(chǎn)效率有顯著的影響。
第二,林改的社會效應(yīng)。社會效應(yīng)主要體現(xiàn)在林權(quán)糾紛得到妥善處理[10,16,18],林業(yè)基層隊伍建設(shè)增加、林業(yè)服務(wù)體系也在逐步完善[10],促進(jìn)農(nóng)村勞動力就業(yè)[18],還有學(xué)者分析了林改對村莊組織帶來了積極的影響[2,6]。
第三,林改的生態(tài)效應(yīng)。生態(tài)效益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森林面積、森林資源得到了增長,二是促進(jìn)森林資源的撫育和保護(hù)。據(jù)國家數(shù)據(jù)庫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6年1月,全國森林面積比2004年增長了18.74%,森林覆蓋率提高了3.4%,活立木總儲積量比2004年提高了20.67%。除了森林資源得到了增長,森林資源保護(hù)、森林火災(zāi)防護(hù)、森林資源培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18]。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林改所產(chǎn)生的生態(tài)效應(yīng)還不是特別明顯,這可能與林業(yè)生態(tài)恢復(fù)特性有關(guān),盡管林改給當(dāng)?shù)氐霓r(nóng)戶增加了家庭收入[3]。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當(dāng)前林改對森林資源配置及可持續(xù)利用、森林資源管理、森林資源安全等林業(yè)生態(tài)方面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負(fù)面影響[19]。
2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實(shí)施績效的影響因素
如前所述,到目前為止,林改政策在實(shí)施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社會效應(yīng)和生態(tài)效應(yīng),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因素影響到林改績效的提升,眾多學(xué)者對此進(jìn)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認(rèn)為影響林改績效的因素除了受農(nóng)戶家庭特征及林地資源特征外,還受林權(quán)糾紛、林地流轉(zhuǎn)問題等外界因素影響。具體來說,可以歸納為4個方面。
2.1 權(quán)屬糾紛
林改的目標(biāo)是建立產(chǎn)權(quán)歸屬清晰的現(xiàn)代林業(yè)產(chǎn)權(quán)制度[20],確權(quán)不到位、林地邊界不明確等都會導(dǎo)致林權(quán)糾紛。而集體林權(quán)糾紛則阻礙集體林的正常經(jīng)營,限制了集體林資源的有效配置,制約林農(nóng)增收,影響集體林所在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21]。林葦[22]研究發(fā)現(xiàn)貴州省9個林改試點(diǎn)縣中均存在權(quán)屬糾紛問題;康小蘭等[23]通過實(shí)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各地林權(quán)糾紛現(xiàn)象普遍存在,而且還有許多新的糾紛出現(xiàn),糾紛原因復(fù)雜且呈現(xiàn)動態(tài)性,沒有調(diào)處的林權(quán)糾紛占總比例的20%左右。眾多學(xué)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林權(quán)糾紛存在的原因,汪正球[24]以黃山區(qū)為例,指出由于某些歷史遺留問題造成部分村集體林地沒有確權(quán)到位,以致于引發(fā)林權(quán)糾紛;衛(wèi)望璽等[25]通過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林農(nóng)個體特征(戶主年齡)、家庭特征(家庭勞動力數(shù)量和家庭收入)、林地特征(林地面積、商品林面積、商品林地塊數(shù)、近十年是否開展過撫育活動)等變量對集體林權(quán)糾紛的產(chǎn)生具有影響,特別是林地塊數(shù)、林地面積和林權(quán)糾紛發(fā)生率呈顯著正比例關(guān)系。
2.2 林地流轉(zhuǎn)問題突出
林地流轉(zhuǎn)不僅直接關(guān)系到森林資產(chǎn)配置效率的高低,促進(jìn)林業(yè)規(guī)模化經(jīng)營和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還可以為林業(yè)的發(fā)展引進(jìn)社會資金,帶動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增加林農(nóng)收入。通過對相關(guān)文獻(xiàn)的研究發(fā)現(xiàn),林改過程中林地流轉(zhuǎn)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林地流轉(zhuǎn)欠規(guī)范、流轉(zhuǎn)市場發(fā)展滯后以及政府監(jiān)管不到位等問題的出現(xiàn)都會給林改績效帶來影響,最終影響林農(nóng)的利益。謝彥明等[26]以云南省500戶林農(nóng)為例進(jìn)行研究,指出30%的林農(nóng)在林地流轉(zhuǎn)的時候都存在登記遺漏問題,且林農(nóng)對林地流轉(zhuǎn)方式的了解程度較低;肖化順等[27]研究指出,由于在流轉(zhuǎn)過程中缺乏一些專業(yè)的林業(yè)服務(wù)機(jī)構(gòu),在林業(yè)資源評估的過程中易出現(xiàn)評估不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不科學(xué)的現(xiàn)象,直接損害了林農(nóng)的經(jīng)濟(jì)利益。有的學(xué)者通過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林農(nóng)對林地概念的了解程度較低,而且在流轉(zhuǎn)過程中流轉(zhuǎn)合同簽署率低[28]。林地流轉(zhuǎn)期限不同對林農(nóng)流轉(zhuǎn)意愿有重要影響,杜群等[29]指出在林地最短流轉(zhuǎn)期限中地方規(guī)范規(guī)定與國家立法相抵觸;夏瑞滿[30]指出流轉(zhuǎn)活動中存在法律體系建設(shè)滯后問題影響社會資金參與林業(yè)投資的積極性,造成一些林地資源得不到充分的開發(fā)利用。
2.3 林權(quán)抵押貸款難
林農(nóng)增加對林地的投入可以擴(kuò)大林業(yè)生產(chǎn)規(guī)模,以獲得更好的經(jīng)濟(jì)收益,而林農(nóng)對林地的投入主要包括勞動力、資金以及科學(xué)技術(shù)等,其中資金的來源渠道主要分為內(nèi)部渠道和外部渠道。劉浩等[20]利用9年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研究發(fā)現(xiàn),在所調(diào)查樣本數(shù)據(jù)中只有1%的農(nóng)戶獲得林權(quán)抵押貸款,獲得對象主要是一些林業(yè)經(jīng)營大戶,普通農(nóng)戶獲得林權(quán)抵押貸款服務(wù)相對困難;韓立達(dá)等[31]指出林權(quán)抵押貸款存在抵押對象限制嚴(yán)格、抵押期限短暫、抵押融資成本較高和抵押程序復(fù)雜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林農(nóng)獲得資金的及時性;謝彥明等[32]在對云南景谷縣197戶林農(nóng)的實(shí)地訪問基礎(chǔ)上發(fā)現(xiàn)75.8%的林農(nóng)不了解林權(quán)抵押貸款,此外,他還發(fā)現(xiàn)林權(quán)抵押貸款覆蓋率低,也存在貸款期限短和貸款利率高等問題,造成林農(nóng)不愿意貸款;劉延安[33]通過利用2012年獲得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在2060戶林農(nóng)中有1 518戶林農(nóng)不了解林權(quán)抵押貸款政策,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林權(quán)抵押貸款政策宣傳不到位;廖文梅等[34]指出金融機(jī)構(gòu)在選擇抵押物時條件要求較高,難以滿足林農(nóng)的實(shí)際發(fā)展需求。以上學(xué)者從抵押貸款角度探究了林權(quán)抵押貸款存在的一些問題,而王磊等[35]指出林農(nóng)自身的文化水平會對林權(quán)抵押貸款的需求存在影響,石道金等[36]認(rèn)為林農(nóng)年齡與林權(quán)抵押貸款需求呈負(fù)向關(guān)系。
2.4 生態(tài)公益林管理不合理
林改過程中林農(nóng)林地被劃入到生態(tài)公益林面積的都會獲得一定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張磊磊等[37]以玉龍縣為例,通過定量實(shí)證分析公益林補(bǔ)償對農(nóng)戶的生活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政策利于林農(nóng)收入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但是生態(tài)公益林管理不到位或者在實(shí)施過程中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偏低則會對林農(nóng)經(jīng)濟(jì)利益造成損失,劉璨等[38]指出在生態(tài)公益林經(jīng)營管理中存在生態(tài)公益林指令性分配、缺乏流轉(zhuǎn)退出機(jī)制以及補(bǔ)償資金被村或者村小組截留,未達(dá)到林農(nóng)手中等現(xiàn)象;劉濱等[1]指出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是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政策的核心,影響政策實(shí)施效果。如果林農(nóng)對森林資源具有很強(qiáng)的經(jīng)濟(jì)依賴性,加之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偏低,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林農(nóng)的收入,也影響農(nóng)村社會穩(wěn)定。田淑英等[39]、王雅敬等[40]、朱博旖等[41]分別用意愿調(diào)查法、條件價值評估法和二元Logit模型等方法分析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的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偏低,林農(nóng)對目前的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滿意度較低。
3 提升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對策
3.1 解決林權(quán)糾紛
林權(quán)糾紛對林改實(shí)施績效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如何解決林權(quán)糾紛,提升林改績效,衛(wèi)望璽等[25]從林權(quán)糾紛產(chǎn)生的客觀因素和外部環(huán)境兩個方面著手,例如,優(yōu)化林業(y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增加就業(yè)機(jī)會,降低林農(nóng)對林地的依賴程度,進(jìn)而達(dá)到降低林權(quán)糾紛發(fā)生率的效果;阮麗娟等[42]從法律的角度出發(fā),利用習(xí)慣法不僅可以從源頭上預(yù)防林權(quán)糾紛的發(fā)生,還可以利用調(diào)解的方式有效解決林權(quán)糾紛;康小蘭等[23]根據(jù)林權(quán)糾紛的特點(diǎn)提出地方政府應(yīng)該設(shè)置固定的林權(quán)糾紛機(jī)構(gòu),并對工作人員進(jìn)行法律培訓(xùn),提高解決林權(quán)糾紛的效率;陳鵬等[43]認(rèn)為林權(quán)證在解決林權(quán)糾紛中扮演重要作用,從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兩個方面出發(fā),首先在自然因素方面利用科學(xué)技術(shù)確定林地邊界權(quán)屬,其次在社會因素方面做好原始資料的保存,防止因人口變動引起的林權(quán)糾紛。
3.2 規(guī)范林地流轉(zhuǎn)
構(gòu)建林地流轉(zhuǎn)保障體系,謝彥明等[26]主要從以下方面考慮:(1)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出臺相關(guān)的林地流轉(zhuǎn)管理辦法;(2)建立林權(quán)流轉(zhuǎn)信息庫和信息共享平臺;(3)林權(quán)流轉(zhuǎn)及時備案。肖化順等[27]指出對于非規(guī)范林地流轉(zhuǎn)的遺留問題,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qū)別對待;此外,轉(zhuǎn)變傳統(tǒng)林業(yè)管理工作方式,特別是禁止管理干部參與林地流轉(zhuǎn);針對林地流轉(zhuǎn)市場混亂問題,他提出政府引導(dǎo),林業(yè)主管部門具體負(fù)責(zé),應(yīng)成立第三方中介組織,提高森林資源評估的科學(xué)性。
3.3 多角度解決林權(quán)抵押貸款問題
林權(quán)抵押貸款是林農(nóng)獲得生產(chǎn)資金、擴(kuò)大生產(chǎn)規(guī)模的一個渠道,如何保障林農(nóng)及時有效的獲取林權(quán)抵押貸款,可以從林農(nóng)、政府和金融部門等3個方面出發(fā)。從林農(nóng)角度,韓立達(dá)等[31]認(rèn)為林農(nóng)應(yīng)不斷加強(qiáng)學(xué)習(x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積極接受新事物;劉軒羽等[44]通過實(shí)證分析得出年齡較年輕和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較單一的林農(nóng)更適合小額林權(quán)抵押貸款,因此,對于這類林農(nóng)要重點(diǎn)宣傳和推廣小額林權(quán)抵押貸款業(yè)務(wù)。從政府角度,謝彥明等[26]認(rèn)為政府要積極鼓勵和支持民間金融機(jī)構(gòu)發(fā)展,將民間資本引入林業(yè)生產(chǎn),拓寬林農(nóng)融資渠道;廖文梅等[34]認(rèn)為政府應(yīng)完善森林評估市場,建立獨(dú)立的評估機(jī)構(gòu),同時,政府應(yīng)該健全行政協(xié)助機(jī)制,確保林業(yè)部門與金融機(jī)構(gòu)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實(shí)現(xiàn)信息共享。從金融機(jī)構(gòu)角度,金融機(jī)構(gòu)根據(jù)林農(nóng)林業(yè)經(jīng)營水平和還款能力適度延長抵押貸款期限[44],石道金等[36]同樣認(rèn)為抵押貸款期限設(shè)置不合理,金融機(jī)構(gòu)應(yīng)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jù)林業(yè)生產(chǎn)特點(diǎn)設(shè)置不同的貸款期限。此外,金融機(jī)構(gòu)應(yīng)該放寬抵押貸款對象,支持林業(yè)企業(yè)和林業(yè)大戶的同時,不應(yīng)忽略具有生產(chǎn)積極性的個體林農(nóng)。
3.4 完善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政策
生態(tài)公益林在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實(shí)際情況中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依照連片原則,優(yōu)化生態(tài)公益林布局,杜絕人為操作的現(xiàn)象;其次,依靠林農(nóng)與護(hù)林員相結(jié)合的管理制度,加強(qiáng)對生態(tài)公益林的管理。王雅敬等[40]通過實(shí)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林農(nóng)研究區(qū)林農(nóng)期待的補(bǔ)償方式有現(xiàn)金補(bǔ)償、技術(shù)補(bǔ)償、實(shí)物補(bǔ)償和混合補(bǔ)償?shù)龋洲r(nóng)更傾向于現(xiàn)金補(bǔ)償和技術(shù)補(bǔ)償,他們認(rèn)為現(xiàn)金使用方便、靈活,可以補(bǔ)貼家用,技術(shù)補(bǔ)償可以為他們提供創(chuàng)業(yè)及就業(yè)機(jī)會。對于生態(tài)公益林林區(qū)的林農(nóng)來說,林業(yè)經(jīng)營活動的減少嚴(yán)重影響其經(jīng)濟(jì)收益,進(jìn)而影響對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的滿意度,因此,可以實(shí)施靈活的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對于原來較多以生態(tài)公益林作為主要經(jīng)濟(jì)來源的家庭,在原有基礎(chǔ)上提高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雖然生態(tài)公益林禁止砍伐,但是可以充分利用生態(tài)公益林資源,發(fā)展林下經(jīng)濟(jì)。
4 展望
綜上所述,國內(nèi)學(xué)者關(guān)于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而對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實(shí)施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評價指標(biāo)體系、評價方法、評價結(jié)果分析和林改實(shí)施績效的影響因素等方面,同時,運(yùn)用多種評價方法建立了林改績效的評價體系,最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多種思路,如通過通過習(xí)慣法解決林權(quán)糾紛,通過林農(nóng)、政府和金融機(jī)構(gòu)3個方面解決林權(quán)抵押貸款,確定靈活的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等。
4.1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對林農(nóng)收入的影響
分析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對林農(nóng)收入的影響,一般情況下要分兩個角度考察:一是要比較林改政策實(shí)施前后林農(nóng)收入的變化情況,二是要比較獲得林改政策的林農(nóng)與未獲得林改政策的林農(nóng)的收入差異。因此,首先要構(gòu)建林改政策政策對林農(nóng)收入的影響模型,然后運(yùn)用分位數(shù)回歸經(jīng)濟(jì)計量模型實(shí)證考察影響大小。
模型構(gòu)建:

式中,t代表時期;Yt為林農(nóng)在t時期的收入水平;D為虛擬變量,衡量林農(nóng)是否獲得林改政策;Tt代表樣本是否來自林改政策實(shí)施后的那個時期,為虛擬變量;N表示林農(nóng)的能力稟賦;H表示林農(nóng)的區(qū)位稟賦;C表示林農(nóng)的社會資本稟賦;Z表示林農(nóng)的經(jīng)濟(jì)資源稟賦,εt為隨機(jī)干擾項(xiàng)[1]。
4.2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對林農(nóng)林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影響
重點(diǎn)考察林改政策對林農(nóng)林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影響方向、程度及作用機(jī)理。首先,利用DEA方法測算林農(nóng)林業(yè)生產(chǎn)效率;然后,構(gòu)建經(jīng)濟(jì)計量模型,探討影響生產(chǎn)效率的關(guān)鍵因素;最后,利用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實(shí)證分析林改政策對林農(nóng)林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影響大小。
模型回歸方程:

式中,Yij為林業(yè)收入,X1ij、X2ij分別為控制變量(包括戶主特征、家庭特征、林地特征、林地投入等)、林改政策變量,α為變量系數(shù),ε為隨即干擾項(xiàng),i= 1、2、3…n為樣本農(nóng)戶,j= 1、2…7為時間(2010、2011…2016年)。
[1] 劉濱,雷顯凱,張升,等. 生態(tài)公益林補(bǔ)償政策實(shí)施績效研究進(jìn)展[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7,39(7):84-90.
[2] 呂杰,黃利. 遼寧省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宏觀績效評價[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2010(7):40-42.
[3] 楊培濤,奉欽亮,覃凡丁. 廣西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綜合評價計量分析[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1(8):20-23,37.
[4] 康媛. 廣東省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的績效分析[D]. 北京: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2011.
[5] 趙鋒泓,奉欽亮,覃凡丁.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對廣西林業(yè)發(fā)展水平影響的評價研究[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5,37(12):43-47.
[6] 聶應(yīng)德,王敏,李瑩瑾. 新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下村莊治理的成效、問題與思考—— 基于十年林改社會效應(yīng)的探究[J]. 晉陽學(xué)刊,2016(1):92-98.
[7] 林琴琴. 福建省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的響應(yīng)與評價研究[D]. 福州:福建農(nóng)林大學(xué),2013.
[8] 陳幸良,邵永同. 集體林產(chǎn)權(quán)安排與林農(nóng)增收關(guān)系研究—— 基于江西武寧縣的調(diào)查分析[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3,33(2):97-103.
[9] 榮慶嬌. 基于農(nóng)戶視角的集體林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研究[D]. 楊凌: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2015.
[10] 廖靈芝,王見. 林區(qū)建設(shè)視角的集體林改績效評價—— 基于云南省2012年10個樣本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4(1):27-30,37.
[11] 鄭風(fēng)田,阮榮平,孔祥智. 南方集體林區(qū)林權(quán)制度改革回顧與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09(1):25-32.
[12] 林琴琴,吳承禎,劉標(biāo). 福建省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評價[J]. 林業(yè)資源管理,2011(3):28-32.
[13] 趙靜,李婷婷,申津羽,等.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評價及其對林農(nóng)森林經(jīng)營意愿影響分析—— 基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農(nóng)戶調(diào)查數(shù)據(jù)[J]. 林業(yè)科學(xué),2014(6):138-146.
[14] 朱冬亮,肖佳.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制度實(shí)施與成效反思—— 以福建為例[J]. 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7(3):81-91.
[15] 李婭,姜春前,嚴(yán)成,等. 江西省集體林區(qū)林權(quán)制度改革效果及農(nóng)戶意愿分析—— 以江西省永豐村、上芫村、龍歸村為例[J].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7(12):54-61.
[16] 王良桂,董微熙,沈文星.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分析[J]. 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2010(5):133-136.
[17] 孔凡斌.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績效評價理論與實(shí)證研究—— 基于江西省2484戶林農(nóng)收入增長的視角[J]. 林業(yè)科學(xué),2008(10):132-141.
[18] 孔凡斌,杜麗. 新時期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政策進(jìn)程與綜合績效評價—— 基于福建、江西、浙江和遼寧四省的改革實(shí)踐[J]. 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jì),172 2009(6):96-105.
[19] 李小華,佘生斌,李海俊,等.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下的生態(tài)保護(hù)與林農(nóng)經(jīng)濟(jì)[J]. 中國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0(5):4-6,50.
[20] 劉浩,劉璨. 我國集體林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及配套改革相關(guān)政策問題研究[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6,38(9):3-12.
[21] 衛(wèi)望璽,謝屹,余尚鴻. 集體林權(quán)糾紛解決的制度現(xiàn)狀與對策研究—— 基于江西省某縣個案的分析[J]. 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6,15(2):48-53.
[22] 林葦. 貴州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的困難與對策研究—— 基于物權(quán)理論的分析視角[J]. 貴州社會科學(xué),2008(8):105-110.
[23] 康小蘭,曾解放,朱述斌.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中林權(quán)確權(quán)的監(jiān)測報告—— 以江西省為例[J].江西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3,12(3):295-299.
[24] 汪正球.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成效、問題及對策—— 以安徽省黃山區(qū)為例[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2(1):30-34.
[25] 衛(wèi)望璽,謝屹. 農(nóng)戶層面的集體林權(quán)糾紛現(xiàn)狀及成因分析—— 基于江西省銅鼓縣426個農(nóng)戶樣本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6,38(6):34-38.
[26] 謝彥明,曹超學(xué),文冰,等. 云南省集體林改配套政策現(xiàn)狀、問題與對策分析—— 基于500農(nóng)戶的調(diào)查[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2(10):35-39.
[27] 肖化順,曾思齊. 淺談湖南省林地流轉(zhuǎn)的沖突與制度建設(shè)[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09,29(4):305-309.
[28] 張文婷,呂杰,寧金萍. 集體林權(quán)改革背景下農(nóng)戶林地流轉(zhuǎn)影響因素分析[J]. 沈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1,13(1):23-27.
[29] 杜群,王兆平. 集體林權(quán)改革中林地流轉(zhuǎn)規(guī)范的沖突與協(xié)調(diào)[J]. 江西社會科學(xué),2010(10):158-167.
[30] 夏瑞滿,吳子文,周華,等. 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工作存在問題與探討—— 以浙江省慶元縣為例[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0(2):59-62.
[31] 韓立達(dá),王靜,李華. 中國林權(quán)抵押貸款制度中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09,29(3):196-200,205.
[32] 謝彥明,劉德欽. 云南景谷林權(quán)抵押貸款問題分析[J]. 西南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11,31(2):54-57,69.
[33] 劉延安,劉芳. 我國集體林權(quán)抵押貸款相關(guān)問題研究—— 基于2060個樣本農(nóng)戶訪談數(shù)據(jù)[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3(4):24-31.
[34] 廖文梅,孔凡斌,高雪萍. 集體林權(quán)抵押貸款政策問題及完善對策研究—— 基于江西南方林權(quán)交易中心數(shù)據(jù)分析[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2,32(3):221-225.
[35] 王磊,蒲玥成,蘇婷,等. 農(nóng)戶林權(quán)抵押貸款潛在需求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四川3個試點(diǎn)縣的實(shí)證分析[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1,31(5):464-467,470.
[36] 石道金,許宇鵬,高鑫. 農(nóng)戶林權(quán)抵押貸款行為及影響因素分析—— 來自浙江麗水的樣本農(nóng)戶數(shù)據(jù)[J]. 林業(yè)科學(xué),2011,47(8):159-167.
[37] 張磊磊,支玲. 生態(tài)補(bǔ)償對農(nóng)戶生計資本影響的定量分析—— 以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縣為例[J]. 森林工程,2014(5):175-180.
[38] 劉璨,張永亮,劉浩. 我國集體林權(quán)制度改革現(xiàn)狀、問題及對策—— 中國集體林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相關(guān)政策問題研究報告[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5,37(4):3-11.
[39] 田淑英,白燕. 森林生態(tài)效益補(bǔ)償:現(xiàn)實(shí)依據(jù)及政策探討[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09(11):42-45,77.
[40] 王雅敬,謝炳庚,李曉青,等. 公益林保護(hù)區(qū)生態(tài)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與補(bǔ)償方式[J]. 應(yīng)用生態(tài)學(xué)報,2016(6):1893-1900.
[41] 朱博旖,王團(tuán)真,陳治琪,等. 農(nóng)戶生態(tài)公益林保護(hù)影響因素的實(shí)證研究—— 以福建省為例[J]. 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2016(1):22-26,36.
[42] 阮麗娟,李小明. 習(xí)慣法視角下的湘西民族地區(qū)林權(quán)糾紛解決研究[J]. 資源開發(fā)與市場,2013,29(9):955-960.
[43] 陳鵬,謝屹,衛(wèi)望璽,等. 集體林權(quán)糾紛解決的制度困境與對策研究[J]. 林業(yè)經(jīng)濟(jì),2015,37(6):52-56.
[44] 劉軒羽,夏秀芳,周莉. 林農(nóng)小額林權(quán)抵押貸款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對福建省、浙江省和陜西省的調(diào)研[J]. 西北林學(xué)院學(xué)報,2014,29(6):288-292.
- 廣東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精準(zhǔn)扶貧視角下貧困村測度研究
——以廣東省連州市為例(內(nèi)文第 156 ~ 165 頁)圖版 - 近15年佛山市基塘系統(tǒng)多時相遙感分析(內(nèi)文第 116 ~ 120 頁)圖版
- 黃鱔和泥鰍感染顎口線蟲的分類鑒定研究(內(nèi)文第 102 ~ 108 頁)圖版
- 過表達(dá)H3K9me3去甲基化酶對豬克隆胚胎體外發(fā)育效率的影響(內(nèi)文第 96 ~ 101 頁)圖版
- 羅非魚皮多肽的制備及其對燙傷修復(fù)的應(yīng)用(內(nèi)文第 88 ~ 95 頁)圖版
- 油菜莖基潰瘍病菌LAMP-HNB檢測方法的建立(內(nèi)文第 66 ~ 69 頁)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