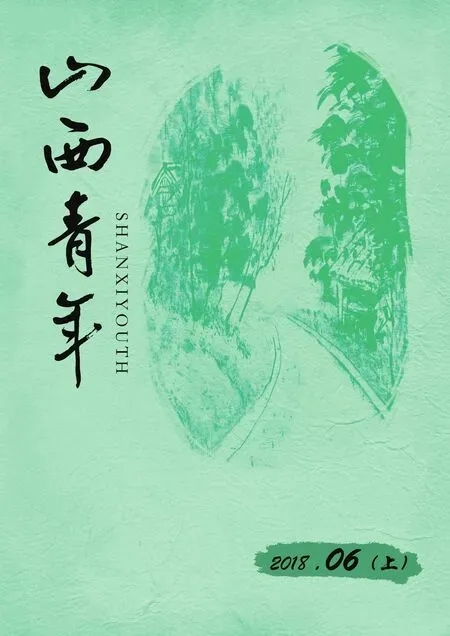社會轉型下的貧困農民增收困境研究
熊詩夢
(華中農業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0)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升,絕對貧困較少,而更多的是滿足溫飽線之后的相對貧困。我國從古至今都是農業大國,“臉朝黃土背朝天”、“泥腿子”是傳統農民的代名詞。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民增收,是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其意義重大深遠。促進貧困農民脫貧致富,解決“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增收。[1]
一、農民貧困原因國內研究
我國著名的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晏陽初認為中國的大患是民眾的貧、愚、弱、私“四大病”,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對民眾首先是農民,先教識字,再實施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溫鐵軍強調如果不調整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打破流通和金融壟斷,通過擴大農業的外部規模來維持小農村社經濟,那么農民將沒有出路,農村也不得發展,農業也將難成為獨立產業。[2]還有些學者深切關心農民,認為農民貧困是因為農民負擔沉重、農民看不起病、農民“離土不離鄉”和“背井離鄉”。社會轉型期間農民的處境從各個方面衡量都不容樂觀。有的學者認為農民貧困與思想觀念上的貧困相關,表現在愚昧落后的思量束縛和對現代觀念的無知和抵抗,以及政治上的農民被動地位,農業為工業提供了大量資本積累而沒有給農民以同等的國民待遇,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仍然在擴大,不消除這三大差別,農民的貧困問題很難解決。國內研究主要注重從我國農民生存處境入手,而不是單一論述某一方面的致貧原因。
二、影響貧困農民增收的因素
(一)內部因素
李敬認為農村金融資資本極度缺乏,大多數農民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吃飯而不能用資本來掙錢,金融因素是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之一。吳敬璉認為“三農”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均資源太少,我國每個農村居民只占有一畝多耕地,即使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幾倍,農民的收入也很難提高,同時農民的受教育程度低是重要影響因素。
(二)外部因素分析
不少學者認為,我國特殊的土地制度是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有的學者從勞動力供給視角出發,認為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初始財富水平較低的農村居民無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從而制約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低質量的勞動力只能在傳統部門從事生產,不利于農民收入的增長。
三、社會轉型下增加農民收入的策略分析
有些學者通過總結我國某些地區農民增收的發展經驗來分析策略。如改革小生產,通過農業產業現代化走向農業現代化增收,創新農業招商引資機制,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完善的市場營銷體系。其實質就是要提高農業投資發展產業,提高農民收入。有的學者通過具體增收措施來提供思路,如在新的經濟形勢下,發展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發展鄉村旅游、鄉村養老、鄉村養生,發展農村電商,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等手段為農民增收,發展農村經濟。社會轉型下的農民增收途徑還得通過對增收影響因素的針對性來解決。方桂堂以北京昌平農村地區為例,采用多種方式促進農民增收并取得明顯效果:一是抓主導產業,二是抓曾策引導扶持,三是抓農業科技支撐,四是抓服務體系建設,五是抓農民培訓就業,六是抓產業融合促動,七是抓溝域經濟開發。王敏、潘勇輝認為短期內致遠農村生產指出和農林水利氣象事業費以及農村基本設施建設投入增長對于農民純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沒有長期的明顯,因此農民增收需要提高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支出,促進財政農業投入。總之,農民增收主要圍繞制度性和農民自身等方面的策略展開。
四、總結
我國本身是個農業大國,農民群體的利益保障和社會地位卻不太理想,社會轉型下的部分農民已經尋找到田野之外的生存方式可以摘掉貧困的帽子,但仍有不少農民仍然屬于絕對貧困,更多的是滿足溫飽后的相對貧困。國家和社會不是不關心農民,但是仍然存在看不起病、寒門難出貴子等現象,其中的原因已在上文中說明。學者們對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研究這一問題。事實上,隨著我國經濟的騰飛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均一畝多的耕地收入已經不能滿足絕大部分的農民在當前社會的消費支出,農民群體已經分化,1990年陸學藝就提出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確立和人民公社的解體后農民就由單一的農業勞動者逐步變成了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經營者,開始分化為若干個利益不同的階層。農民之所以分化,是因為手頭的土地已經無法滿足經濟要求,也有個人的因素。總之,正如某些學者所言:憲法確定了農民的特殊地位,但在現實中,農民的境況確實處于社會的底層,我們的貧困農民、農村、農業問題還需要更有力的關注和支持。
[1]任中玉.貧困地區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分析[J].改革與開放,2011(18):148-149.
[2]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J].讀書,1999(12):3-11.
[3]周怡.社會情境理論:貧困現象的另一種解釋[J].社會科學,2007(10):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