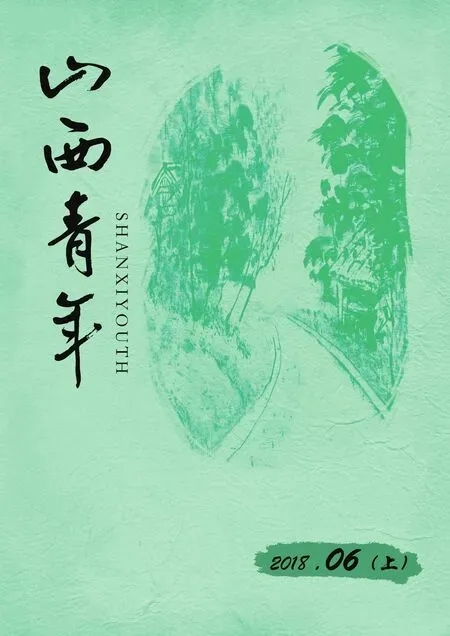論語言文化的不可譯性及其轉化策略
梁鵬輝
(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一、前言
在現代翻譯學理論基礎構建中,語言、文化和翻譯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文化與翻譯的關系研究應基于文化與語言關系的研究之上。[1]所以本文以探究何為文化,文化和語言以及翻譯之間又有什么樣的關系開頭,由此引出翻譯不可譯。
二、語言、文化與翻譯
1989年版《辭海》指出:文化,“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對于文化與語言,文化與翻譯來講,我們多偏向于精神文化層面上的研究。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發展和沉積的結晶,如果不了解一種文化所運用的語言,那么想要了解這種文化是不可能。每一種語言都是該民族對周圍環境和世界的普遍認知和現實反映,體現著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并隨著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發展而發展。
翻譯按照一定的技巧和理論,將一種語言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表達,但是“翻譯者不僅僅是在單純處理產生于某個特定時間或社會環境下的文字信息,而是在兩種文化、甚至多種文化間進行動態的協調,以期能夠通過對文化因素的綜合分析來最終形成合理有效的譯文。”[2]所以翻譯是一種在譯者完全理解原文文本,并且結合時代背景和原作者寫作風格的前提下,考慮原作風格和目的以及讀者因素的再創作性活動。
三、翻譯不可譯性
人類認識和思維方式具有普遍性,不同語言之間的相互翻譯是可能的。但是基于語言所發展的地理環境,歷史發展、文化宗教、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千差萬別,完全對等的翻譯是不存在的。
“如果在英漢互譯中,有時無法將原語或源語(source languages)翻譯成譯入語或目的語(target languages)而造成一定程度上意義的損失,即稱為‘不可譯性’。”[3]民族、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和開放性都影響著翻譯的不可譯,具體來講歷史文化因素和語言學因素是造就翻譯不可譯性的兩大原因。
(一)歷史文化原因
英漢兩種語言在各自的歷史發展和演變過程中,都積累了豐富的歷史典故,蘊含著大量的風土人情。如果這些故事或者典故并沒有在譯入語的國家出現過,或者出現的事物并沒有被賦予與源語國家同樣的意義,那么在翻譯中就會出現因為歷史文化因素不同造成的不可譯,或者是造成源語中文化的流失。
清明節這一傳統習俗是中國人祭奠祖先、緬懷先烈的節日,氣氛總是凄涼哀傷的。楊憲益譯“清明節”為the Clear and Bright Festival,意為“清掃”和“明朗”的節日,沒有體現這一節中包含的哀思。霍克斯譯為the day of the Spring Cleaning Festival部分表達出“掃墓”這一蘊含。雖然這兩種翻譯都照顧到了譯入語讀者的理解,但并不能完全讓譯入語讀者感受到中國這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與情感基調。
(二)語言學原因
漢語作為音、形、義結合的象形文字,其獨特的圖象性、會意性和聯想性等往往在漢譯英時難以轉換,甚至不可譯。修辭手法便是漢英翻譯時的一大難題,頂真、雙關、諧音等等在翻譯時候幾乎是不可譯的。比如,民國萬稅、天下太貧。其中“稅”與“歲”,“貧”與“平”諧音,在翻譯過程中如果既要保持形,又要保持意,還有體現本局的諧音,完全是不可能。
四、不可譯的相對性和轉化策略
“一種語言在向另一種語言進行轉換的過程中,由于不同語言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背景的差異,會形成語言的不可譯現象。”[4]但人類的生理特征基本相同,生存的環境和所認識的對象也是客觀存在的,有著一定的客觀相同性和相通性。
在具體的翻譯操作中,歸化和異化是最常見,最有效的轉化手法。
(一)利用歸化,發揮語言優勢
翻譯中的歸化,是指將源語納入譯入語。歸化可以有效消除文化隔閡,使源語的文化特征基本消失不見,讓譯作以譯入語的特征和習慣以自然、貼切的語言表達出來。
杜甫《新安吏》有這樣一句話:“府貼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這一說法是唐天寶年間的一種兵役制度,具體指十八歲至二十三歲的男性。對于本句的翻譯,孫版本為:Ordaining the middle class be listed,the draughting order yesternight came down.而許的版本為:Last night came order for hands green,draft age is lowered to eighteen.孫譯本對這一歷史信息進行了注釋:According to Tang statute from the third year of the Tian-bao Period,a male person over eighteen years old was regarded a middle youth and one over twenty-three to be adult.
而許譯本只在翻譯中沒有直接對應的名詞,只有解釋為十八歲以上男性,并且利用be lowered一詞表示可能年齡更大的男性已經不在村中了。
由此看來,第一個版本的歸化意味要明顯于第二個譯本。對讀者來說,第一種版本就更加容易理解和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對我們語言文化走出去更加具有意義。
(二)采用異化,保存源語特色
“異化就是要在翻譯的過程中,把原語的詞匯、句式、語法、文化等特點原封不動地引入目的語中,從而保留原語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5]
韓邦慶所著《海上花列傳》是我國第一部方言小說。原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王阿二道:‘呸!人要有了良心是狗也不吃屎了!’”張愛玲將這一段譯為:“Pei !”Second Wong made a spitting noise.“If he has a conscience,dogs don't eat shit.”[6]本段來自鄉下青年張小村到一處青樓和店內女子調情的場面。為了突出其中人物鮮明的個性,張愛玲采取了異化翻譯策略,進行直譯,保存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和口語特色。
由此可見,歸化和異化都有其特點和優點,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歸化和異化并不能對立運用,在具體的情況下,需要相互結合,才能相輔相成,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五、結語
文本的不可譯性研究在翻譯理論發展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要研究翻譯的不可譯性就必然要探討翻譯與文化的關系,而要探究這一問題就必然要求以文化和語言的研究為基礎。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翻譯的不可譯性,但基于人類思維的相似性和生存環境的客觀性,文化又是可譯的,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翻譯的不可譯成分逐漸通過人類不停的探究、轉化以及文化的相互融合逐漸變為一定程度上的可譯性。在這種背景下,譯者的根本任務在于在譯文中再現原文內容風格,傳達源語文化。因此譯者要謹慎選擇歸化或異化,絕不應該搞單一化或者對立,要有機利用這一轉化策略,使其相輔相成。同時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盡量將不可譯性轉化為可譯性。
[1]余意夢婷.論語言文化的不可譯性及其轉化策略——以《紅樓夢》的兩個英譯本比較分析為例[D].廣西師范大學,2008.
[2]潘文國.大變局下的語言與翻譯研究[J].外語界,2016(1).
[3]王瑛.論英漢互譯中絕對的可能性與相對的不可譯性[J].內蒙古: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8(6).
[4]羅潔.文化、語言、不可譯性[J].南昌:南昌航空工業學院學報,2003(1).
[5]黃勤.歸化與異化相得益彰—評張愛玲譯《海上花列傳》[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7(8).
[6]Chang Eileen.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M].Renditions,1982: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