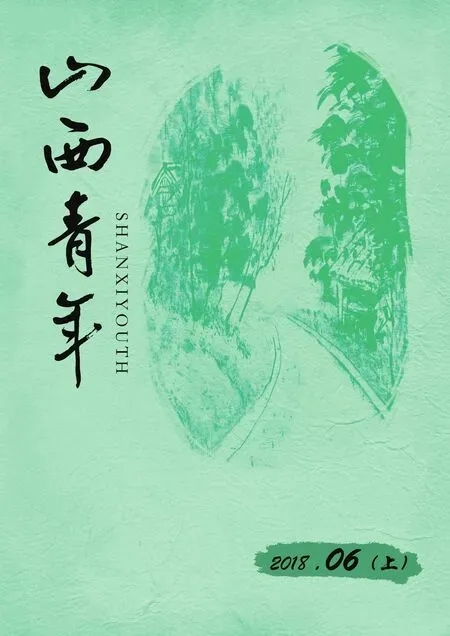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探究
高 歌 崔曉田
(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刑罰制度能夠當作對一國立法者對本國民關鍵法益的重視程度與執政理念進行考察的根本視角。目前,《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已對先前修正案重定罪輕刑罰修訂趨勢進行扭轉,并進一步完善了刑罰制度調整、刑罰結構完善這些層面。
一、刑法修正案對刑罰結構調整的發展趨勢進行了體現
首先,對死刑的廢除獲得了實質進展,然而加重死刑存在一定的遺憾;在1997年我國刑法法典中對68種死刑罪名進行了規定,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廢止了13種經濟類、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量刑,這一情況呈現了我國在立法上嚴格限制死刑取得了極大的進步;《刑法修正案(九)》堅持一個大的方向,即對9個罪名的死刑進行了廢除,這一行為的意義在于:讓我國初步完成了取消純粹經濟類犯罪死刑的工作目標,這在我國死刑控制上是一個關鍵的里程碑。這兩次的刑法修正案促進了死刑罪名的廢除,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刑罰輕緩的趨勢。然而,這兩次刑法修正案中大多是對司法適用上備而少用、不用的虛置條款進行廢除,且遏制并矯正死刑的擴大適用。同時,修正案在廢除死刑罪名的法定刑調整時,加重了一些罪名的法定刑,使得廢除思想的刑罰輕緩化逐漸轉變為加重加刑的立法。
在今后的刑法修訂中,必需對刑罰制度進行不斷的創新。同時,刑法修正案應該盡可能的呈現我國刑罰結構加以整體調整的意圖,以便于配合死刑的削減,強化對假釋、減刑的監督,如此一來,司法腐敗對司法公信力所產生的沖擊就能夠得以預防。對于是否提高“生刑”的問題,修正案中采納的觀點是“死刑太重、生刑太輕”,這不僅對死刑有所削減,還對提高生刑的規定進行了提出,這一情況十分顯然的體現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同時,《刑法修正案(八)》中對無期徒刑的具體執行期限進行了延長,并對這一刑法的嚴厲性進行增加,讓我國刑罰結構缺陷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更加嚴格的執行了管制刑,對人民法院可結合犯罪情況對管制犯實行“禁止令”進行規定,附加條件中將有期徒刑數罪并罰的刑期進行了提高。對于貪污賄賂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在其中增設了終身監禁的刑罰,對貪污罪中的無期徒刑和死緩做出了法律補充,屬于立法人員對無期徒刑刑期延長及協調自由刑體系進行的一種嘗試性的探索[1]。
二、修正案中呈現了刑罰結構調整展望
一方面,進一步確定刑罰輕緩化的發展趨勢。現如今,在世界刑罰實踐中最受歡迎的理論為“重重輕輕”,該理論中有關的刑事政策及刑罰結構主要是區別評價輕微犯罪和嚴重犯罪所帶來的不同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相應的人身危險性,應用完全不同的處遇理念,并對預防犯罪的社會功利價值、社會大眾善惡報應的樸素情感加以一定的兼顧,所以早期人類社會對重刑主義蒙昧枷鎖加以擺脫后,西方國家較快的接納了“重重輕輕”理論。但是,相較于英美法系的國家來說,我國刑罰體系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的。我國大部分犯罪的認定具有“量”的要求及“質”的標準,所以我國刑法中的“犯罪圈”在極大程度上小于僅以行為性質規范劃分非罪與罪的國家,這使得我國被認為是“輕罪”的犯罪行為,在其他國家可能被認為屬于“重罪”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現如今,廢除死刑屬于世界刑法的主流,因此死刑應有序地、堅定地進行廢除;《刑法修正案(八)》及《刑法修正案(九)》已經取消了22項死刑罪名,這說明我國刑法已開始由盲目到目的、由機械到能動、由不理性到理性,逐步走向了廢除死刑之路,讓刑罰制度更進一步合理化;但是死刑至今依然存在,那么其必要存在獨特的價值與作用;同時,在對死刑進行逐漸廢除的過程中,應對死刑的替代刑問題加以考慮;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提出:對于重大及特大貪污賄賂案件中的犯罪人,人民法院結合一系列情況對犯罪人在死刑緩期實施二年期滿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減成無期徒刑后進行決定,終身監禁,無法進行減刑、假釋;此外,若對死刑進行取消時,需對終身監禁刑加以大面積的設置,并具有一定的問題,站在嚴苛性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終身監禁刑的殘酷性等同于死刑,死刑屬于對犯罪人的自然屬性進行消滅,終身監禁刑屬于對犯罪人的社會屬性進行消除。另一方面,當前,社會進一步發展,世界刑罰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我國刑罰逐漸向輕緩化合理發展時,應側重于對輕刑的配置策略及適用方式加以調整,以便于能夠讓宣告刑結構更加的多樣化,且刑罰趨輕時刑罰結構會變得更加的合理化[2]。
三、結語
總之,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廢除死刑已成為當今世界上刑法的主流,通過刑法修正從而對刑罰結構加以合理調整。
[1]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04):125-134.
[2]王志祥,敦寧.我國刑罰結構的調整及其反思[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