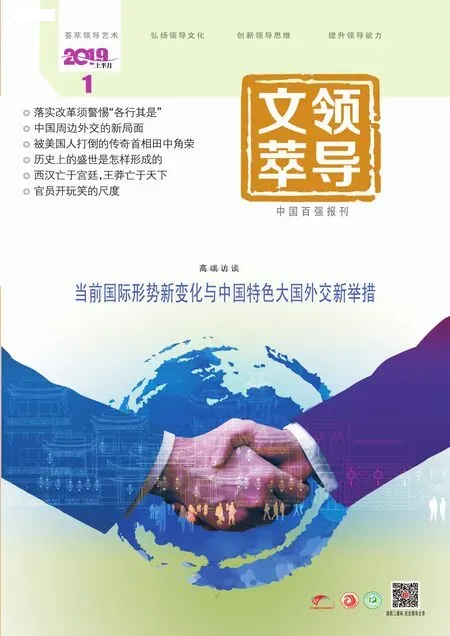溥儀作證表演精彩
阿諾德·C.布拉克曼+梅小侃++余燕明
1946年8月,法庭被現代歷史上最不尋常人物的出現主導了11天之久。8月9日,這位檢方證人在斯大林秘密警察小分隊的陪同下在東京著陸。他身穿廉價、做工粗糙的藍色毛嗶嘰西裝,頭戴一頂俄國勞動人民的黑帽子(這是20世紀20年代因列寧而流行起來的風格),腳蹬白襪子。他就是中國的末代皇帝。他為世人熟知的名字是亨利·溥儀,一度成為日本人征服中國滿洲數省后所扶植的傀儡“滿洲國”皇帝。
表演式地進場
盟國檢方把溥儀帶到東京指證日本人在滿洲的獸行。他是一位關鍵證人,而且他待在證人席上的時間的確比任何其他檢方證人都要長。斯大林批準把前“滿洲國”皇帝送到日本,莫斯科的唯一條件是作證之后美軍要把他歸還蘇聯拘押。對此麥克阿瑟欣然同意。最高統帥被溥儀的現身弄得很尷尬,希望這位前皇帝越早離開日本越好,因為他擔心,溥儀出現在證人席上可能會引起人們再一次要求也將裕仁傳喚出庭。能讓中國皇帝做的事情,肯定也能讓日本皇帝去做。
在溥儀8月份到達東京的時候,檢方已經向法庭提交了大量證據,證明“滿洲國”是日本的衛星國。最重要的文件中有投降后未被焚毀的外務省檔案,題為“有關滿洲事務的秘密記錄”。只要對這份檔案瞥一眼,對任何獨立的觀察家來說已經足夠表明,當時是日本統治“滿洲國”,并統治溥儀。
當溥儀在8月16日第一次進入法庭大廳時,媒體席和旁聽席都擁擠不堪。溥儀對迸發的閃光燈和呆看他的人群習以為常。他表演式地進場,右手拿著一把精致的象牙扇(此時空調已再次關閉了),以一種深思熟慮、權威式的儀態走上證人席。他戴著黑框眼鏡,由于1920、30、40年代他在星期日增刊上頻繁露面,立刻就能被人認出來。在許多方面,除非天皇裕仁本人被帶上證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沒有一位證人能夠像前滿洲皇帝一樣,與被告們有如此密切的關系。28個被告中有24個跟他有過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在那個炎熱潮濕的8月天,每個被告都注視著溥儀穿過靜下來的法庭大廳。他們一臉愁容,像是預測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唯有板垣大將莫名其妙地顯得很天真。他開心地微笑著,好像在歡迎一位熟識的生意伙伴參加派對。
以進為退的中國謀略
溥儀在證人席的表演堪稱精彩。在這個首次公開亮相之前,他被觀察家嘲笑為遲鈍,認為他即便不是弱智,也像個紙板做的假人。然而,溥儀在證人席證明了自己詭計多端,是個狡詐、奸猾、徹頭徹尾欺騙的大師。他擺平了韋伯、季南以及日本和美國的辯護律師,時而激怒他們,時而嘲弄他們,最終搞得他們互相攻訐。倘若溥儀是一個自由人,他的表演也算不俗。而考慮到他身處的特定情勢,他的表演就實在令人驚嘆了。法官席上坐著蘇聯的柴揚諾夫將軍,蘇聯把溥儀作為政治犯囚禁。柴揚諾夫的右邊是梅法官,他所代表的中國已經把溥儀定性為叛國者。與此同時還有第三位法官——美國的克拉默,溥儀正處于美國的軍事管轄權之下。也許溥儀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日本宿敵成為被告了。
從作證一開始,溥儀就采取以進為退的中國謀略。他講述板垣大將如何提出給他滿洲的皇位。他說:“如果我拒絕,我的生命就受到威脅。”然后,他玩了一個花招責備同盟國,狡猾地說:“當時民主國家并沒有試圖反擊日本軍國主義者。我一個人單槍匹馬是很難抗拒他們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聲稱,自1931年以來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別人的挾持之下,并且由于他一直不是一個自由的人,所以不應為此承擔責任。
在溥儀這種態度持續幾天之后,強硬的韋伯轉而感到惱怒,并作了不必要的評論。韋伯說:“我們當然不是在審問證人,但是,我們關注他的可信度。有性命危險、對死亡恐懼,在戰場上不能成為原諒怯懦或逃跑的理由,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成為原諒叛國的理由。一上午我們都在聽這個人說他為何與日本人勾結的各種借口。我想我們已經聽夠了。”
嫻熟而巧妙地攪出騷動
溥儀嫻熟而巧妙地在法庭攪出周期性騷動,在這個過程中把注意力從他自己身上移開。有一次辯方向他出示一封蓋著他的圖章,或者說鈐印的信件,據說是他在1931年發給板垣的,表達了接受日本庇護的滿洲皇位的愿望。溥儀掃了一眼那封信,用了一個戲劇性的開場動作跳將起來。美國憲兵急忙起立,蘇聯便衣警察小分隊也站了起來,樓座里緊接著響起一陣嘈雜聲。韋伯爵士在法官席上大喊一聲:“坐下!”聲音高過所有的人。溥儀滿不在乎地回喊:“法官大人,這是假的!”又溜回椅子上坐下了。
韋伯說:“只管回答問題。你發過那封信嗎?”“沒有”,溥儀回答,并指責辯方“應當被判偽造文件罪”。
對他冗長的交叉盤問接近尾聲時,被激怒的布萊克尼告訴法庭:“我想提請法庭注意,從這個證人作證的開頭直到現在的結尾……他明顯而蓄意地對法庭撒謊。”溥儀聳聳肩:“我不怪你,你是辯方的律師嘛。”他傲慢而饒有分寸地說,“當然,你是想要我歪曲事實。”
韋伯終止了這場辯論:“證人已經表明了某種立場,即他當時完全處于日本人的指導之下。這是一個簡單的立場。再多的交叉盤問也不會使他改口,這是顯而易見的。”
回首往事,當我重溫溥儀在證人席的證詞,其中有一句話,從歷史潮流的沉渣中凸現出來。那就是:“除了哭泣,我什么也做不了。”這一簡單事實概括了中國皇帝的生活和時代。對裕仁也能講同樣的話嗎?
(摘自《另一個紐倫堡:東京審判未曾述說的故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