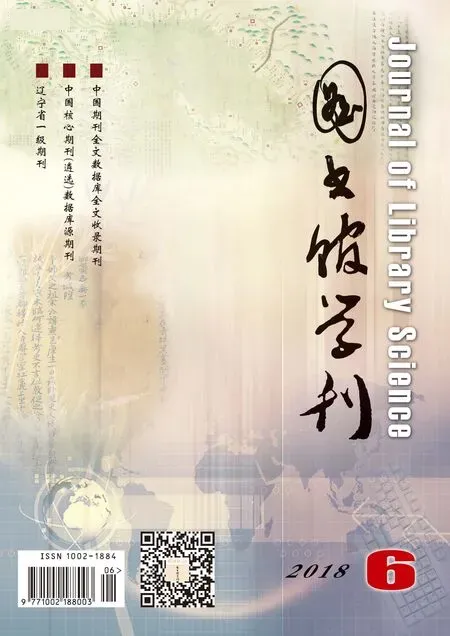黃仲昭《八閩通志》之編纂及文獻價值*
葉建金
(黎明職業大學圖書館,福建 泉州 362000)
1 引言
黃仲昭,明代著名文學家、方志學家和經學家,自幼熟習經史,博覽群書,學識宏富,尤長于地方志的修纂,所纂《八閩通志》八十七卷,是福建省第一部省志,被譽為“閩省方志之本”,影響深遠。該志不僅具有始創價值更具文獻價值,其征引、載述、保存了大量隋唐、宋元、明初時期的文獻資料,對后人研究福建歷史沿革、農工商業、人物事跡、物產風俗、科技文教、地理交通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然而,目前學術界對其研究甚少,筆者通過介紹《八閩通志》的纂修背景、作者生平、編纂始末、版本流傳和文獻價值,拋磚引玉,以期能引起學者對善本志書的關注,深入挖掘善本的價值,服務于當下經濟與文化。
2 《八閩通志》的編纂
2.1 編纂背景
我國方志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歷經秦漢魏晉的初步發展,隋唐的進一步發展,兩宋的逐步定型和元朝的普及,方志種類增加、志書取材范圍擴大、內容擴充,體例也進一步發展。元代創立一統志的形式,掀起了官修一統志的風氣。然明代以前閩省地方志中記述內容涉及全閩的志書數量較少,僅《閩中記》《福建路圖經》頗具省志雛形,可惜均已散佚。福建省志的成熟完善,并進行大規模的編修是從明代開始的。明代統治者的重視及《大明一統志》和《修志凡例》的頒布掀起了各省修志熱潮,并為各地修纂方志提供了范本。福建省受此影響,全省府、州、縣志等官修志書和私撰志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豐碩的志書為黃仲昭博采眾長纂成《八閩通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2 作者生平
黃仲昭,明宣德十年(1435)生于福建莆田一官宦世家,“名潛,以字行,”號未軒,又號退巖居士,“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1]成化二年(1466)黃仲昭登進士二甲,入翰林院,以士節與史著名世。后調至大理寺任職,在任期間,清正廉潔,秉公執法,平反冤獄,深得百姓擁戴。成化十一年至十四年,黃仲昭返鄉丁憂守制,成化十六年(1480),托病乞歸。回歸故里后,黃仲昭于城南皋山買田筑屋,躬耕隴畝,讀書著述。弘治元年(1488),孝宗朱祐樘即位,禮請黃仲昭出山,當起復文書到時,《八閩通志》尚未完成,黃仲昭遂遲遲不肯起程,直至志書完稿、付印才安心動身進京。弘治三年(1490),黃仲昭授命出任江西提學僉事,頗有業績。弘治八年(1495),乞休返鄉,著書講學。弘治十四年(1501),應邀纂修《興化府志》;弘治十八年(1505),應邀赴邵修纂《邵武府志》。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病逝,終年七十四歲。黃仲昭一生,為官清廉,學識淵博,博覽廣涉,理學、詩文、農藝、園藝、醫學、卜巫等,無不涉獵,并在經史、地理、詩文等領域均有較深造詣。黃仲昭平生勤于著書立說,成果頗豐,有《未軒文集》《讀〈尚書〉》《讀〈春秋〉》《讀〈毛詩〉》《晦蓭朱先生文集》《通鑒證異》《綱目書法》《八閩通志》《興化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延平府志》等著述傳世。黃仲昭說:“我力不勝衣,而心欲負九鼎;我官不踰七品,而視金、張①為無物。性癖情知與世殊,只應歸臥故山廬。山中一有經綸事,朝課耕桑夕校書。”[2]正是這樣的高貴品質助其成就了不朽的《八閩通志》。
2.3 《八閩通志》的編纂始末
成化十六年(1480),太監陳道奉命鎮閩,欲觀福建風土習尚,尋找八郡方志,因為八郡志書“事多迭出,文無統紀,搜考之余,令人厭倦”,[3]故有意重新纂修,并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聘請黃仲昭編纂福建地志。黃仲昭在博考各府、郡縣舊志及其他史料的基礎上,增補、辯正、考訂、刪次、潤色,歷經六年,于弘治二年(1489)成書,命名為《八閩通志》,這種以福建別稱“八閩”來命名省志的做法,在地方志中別具一格,后來明萬歷年間,王應山編纂《閩大記》《閩都記》,何喬遠編纂《閩書》,也都承襲此法。弘治三年(1490),《八閩通志》付梓刊行,全志共87卷,24冊,首有黃仲昭序、彭韶序,末有陳道跋。該志的纂修體例,仿照《大明一統志》,根據“隨事分類”的原則,將書分為地理、食貨、秩官、學校、選舉、壇遺、祠廟、恤政、人物、宮室、寺觀、丘墓、古跡、祥異、詞翰、抬遺十八大類,各類之下再分細目,共四十二,“每類則合八府一州之事,以次列之。”[3]《八閩通志》統屬得法,載述詳備,尤為注重地理和人物的記載,為福建現存最早、最完備的古代省志。清《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地理類《三山志》條目贊曰:“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記輿地者不下數十家,惟黃仲昭《八閩通志》頗稱善本。”
2.4 《八閩通志》的版本流傳
弘治三年,《八閩通志》首次刊印流通,稱“原刊本”,亦稱“庚戌本”;翌年進行修改的稱“遞修本”。萬歷二十四年(1954),“原刊本”突遇火災受損,福建巡按監察御史陸夢祖發布檄令對“原刊本”重加修鋟,于萬歷三十九年(1611)完成,稱為“修鋟本”。“原刊本”、“遞修本”和“修鋟本”此3種版本當時印數均不多,流傳不廣,現已非常稀有罕見。目前國內外的“原刊本”,僅北京圖書館和中科院有藏完整刊本,而復旦大學圖書館、天一閣、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日本尊經閣文庫所藏均殘缺不全。“遞修本”,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日本宮內藏書寮有藏殘存卷,而國內尚未發現。“修鋟本”,天津圖書館藏87卷40冊完整刊本;臺灣“中央圖書館”殘存79卷,日本內閣文庫殘存23冊,美國國會圖書館殘存36冊,解放前福建省政府圖書室曾藏有十多冊殘卷,建國后移交福建省文史館卻不幸在“文革”中全被銷毀。70年代初,福建省圖書館派專員前往北京圖書館將其所藏的“原刊本”攝制成“膠卷本”,1963年并據此抄錄87冊,后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廈門大學圖書館、福建省博物館、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圖書館亦據此各傳抄一部。1988年,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縮印其館藏的“原刊本”,列為《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33-35冊,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0年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和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以“原刊本”為底本進行標點和校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兩冊精裝問世。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正編》收載影印天津圖書館館藏“修鋟本”,列為史部第177-178冊。2016年福建省方志委、海峽書局以日本內閣文庫的萬歷“修鋟本”為底本,參照其各館藏版本進行點校后出版。
3 《八閩通志》的文獻價值
《八閩通志》內容豐富,記述翔實,記述范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它以福建地情為載體,涉及福建的政治、沿革、地理、經濟、文化、戶口、風俗、田賦、科舉、人物、藝文、山川、物產、橋梁、水利、坊市、學校、遺跡、藥局、潮汐、自然災害等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3.1 輯佚價值
《八閩通志》在史志上的輯佚方面有較大的價值,其所征引的福建舊志,尤其是唐、宋、元時期各地的《圖經》《州志》《府志》《縣志》等,幾乎已不再傳世,幸在《八閩通志》的征引中可窺一斑。例如,唐大中五年(851),郡人林谞撰《閩中記》十卷,原書已佚,從《八閩通志》中輯得佚文15條,涉及地理、山川、風俗、物產、土產、名宦、士行、拾遺等內容,而《輿地紀勝》僅存佚文4條,且僅涉及景色和地名。北宋《南劍州志》,具體修纂時間及修纂者無考,已佚,僅《八閩通志》存佚文1條。宋《莆陽舊志》,具體修纂時間及纂修者無考,已佚,原書結構已不可知,《輿地紀勝》存佚文1條,《大明一統志》存佚文1條,而《八閩通志》存佚文23條,可知《莆陽舊志》大致含有地理、山川、食貨、秩官、公署、選舉、祠廟、恤政、人物、寺觀、拾遺等11門內容。宋元豐五年(1082),吳與纂《漳州圖經》,已佚,《輿地紀勝》僅輯得佚文1條,《八閩通志》輯得3條。元《建寧舊志》,具體修纂時間及纂修者無考,已佚,《大明一統志》存佚文3條,《八閩通志》輯得較完整佚文10條,可知《漳州圖經》大致含有地理、秩官、公署、選舉、祠廟、恤政、寺觀7門內容。元致和元年(1328)《三山續志》,撰人不詳,已佚,《八閩通志》輯得佚文26條,可知其大致含有地理、食貨、秩官、公署、學校、人物、古跡7門內容,而《永樂大典》僅存佚文3條,且僅限公署1門內容。可見《八閩通志》對明之前的史料有較好的保存,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八閩通志》對這些現今已佚的古志文獻進行輯佚。
3.2 勘正史誤的價值
地方志與史書向來有互補相校的關系,為此利用《八閩通志》可以糾正史書上的某些明顯錯誤之處。例如,《大明一統志》記載“高蓋山前日影微,黃昏歸鳥傍林飛;墳前滴酒空垂淚,不見丁寧道早歸。”一詩乃唐代歐陽詹生前所作的《祭母詩》。而《八閩通志》卷七《地理·山川·泉州府·南安縣·高蓋山》曰:“按韓愈《歐陽生哀辭》,詹歿時其父母俱在,而志載詹哀母詩,殊不合。竊詳愈與詹為友,而哀辭作于詹初歿時,其言必可信無疑也。哀母之詩豈好事者假托而為之歟?”[3]黃仲昭認為該詩實非詹所作。對此,明代史學家何喬遠在其所著的《閩書》中言:“考之《永福志》,陳嵩詩也。”故《大明一統志》記《祭母詩》出自歐陽詹,誤。又如南宋大臣、理學家詹體仁,明《寰宇通志》作“張體仁”,且載為建安人,明《崇安縣志》記為崇安人,而《八閩通志》卷之四十九《選舉》及卷六十四卷《人物》記載“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朱文公游,第進士為太常少卿。”[3]考之《宋史·詹體仁傳》,“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4]可見《寰宇通志》及《崇安縣志》所載有誤。
3.3 博考群書,取材廣泛,保存了大量文獻典籍
黃仲昭在《八閩通志》凡例中言:“《大明一統志》備載天下之事,其采輯不得不從簡約,今之所輯者,特一方之事而已,宜加詳焉。”[3]為此,他非常注重博集群書,最大限度地征引相關文獻,用以提高志書的質量。由于《八閩通志》篇幅巨大,尚無人整理出《八閩通志》所征引的全部書目,因而在此不可能一一列舉。下面僅就卷三《地理·風俗》一門進行整理以作說明。在這半卷中,《八閩通志》征引的重要文獻典籍有“晉郭璞《遷城銘》;南北朝宗懔《荊楚歲時記》;《隋書·地理志》;唐《閩中記》《南史》;宋《方輿勝覽》《圖經》《宋史·地理志》、林耕《貢士莊記》、劉克莊《陳公生祠記》、陳昌期《學記》、黃子埋《玩芳亭記》、林岊《虛心堂記》、常挺《貢土莊增田記》、蔡襄《立春寄福州郡守燕受》、晁氏《家語》、蔡襄《寒食游西湖》、《開花園》、程師孟《春風亭》《寒食游九仙烏石山》、王逵《上巳游東禪》、李彤《四序總要》、韓元吉《建安志》《建安集》、王十朋《止訟文》、曹修睦《建學表》、陳知柔《修學記》、陳安國《儒學記》、傅自得《道院記》、陳淳《北溪集》、郭祥正《凈眾寺法堂記》《綦崇禮傳》、《龍溪記》、卓遵《為趙師縉蠲役記》、朱熹《學記》、陳一新《跋贍學田碑》、葉祖洽《改縣名記》《譙樓記》、黃公度《學記》、陳俊卿《貢院記》、游酢《通判題名記》、陳讜《仙游縣道慶堂記》、陳堯通《楊公堂記》;元貢師泰《送李尚書序》、吳海《送鄭訓導序》、黃垚《修廟學記》、泉生《大同書院記》《元志》《劍浦記》《順昌記》、黃鎮成《真率約序》;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陳叔剛《重建夫子廟記》”[3]等達53種之多。有關明初以前福建各地風俗的資料本就稀缺,黃仲昭以一己之力,千百尋一,旁征博引,集而成章,其文獻價值是相當高的。
3.4 重視對歷史人物業績的記敘
人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南宋著名學者張栻曾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作為碩儒,黃仲昭深知其理,在其《八閩通志》自序中言:“人物乃典刑所系而可以有補于世教……至于人物一類,志或有未載及載而未盡者,必旁搜博考,尤致其意焉。”[3]《八閩通志》中的人物列傳,篇幅從卷六十二至七十二,多達十卷,共輯入1998人,其中,名臣274人,良吏400人,道學36人,儒林233人,文苑198人,士行64人,風節55人,忠烈83人,孝義106人,宦跡66人,武功11人,隱逸97人,寓賢51人,藝術23人,仙釋33人,列女268人,基本涵括了明初之前福建歷代先賢在政治、經濟、文化、交通、藝術、教育、軍事、醫學、氣節等方面的業績。如唐代“八閩文化先驅”、文學家、詩人歐陽詹,福建晉江人,貞元八年舉進士,與韓愈、賈稜聯第,時稱“龍虎榜”。“閩人遞進士自詹始”,[5]開八閩文教之先,福建文士紛紛開始向慕讀書,儒學風氣開始振興。又如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福建武夷山人,“永景祐中第進士,累官屯田員外郎。工于詞章,尤擅樂府。”[3]唐五代至宋初,詞人創詞用的體式皆以“小令”為主,不擅“慢詞”,柳永不僅是第一個大量創作“慢詞”的人,還是兩宋詞壇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改變了小令一統詞壇的格局,對宋詞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北宋政治家、書法家、茶學專家蔡襄,“字君漠,福建仙游人,天圣中第進士甲科。與歐陽修、余靖、王素號‘四諫’。”[3]在福建為官時,廣施惠政。“知福州,整頓吏治、勸學興教、育民遵法、教習舟船,防備海寇。知泉州,興修水利,植松建橋,復古五塘以溉民田,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知建州,創北苑貢茶小龍團、撰《茶錄》、著《荔枝譜》[3],有力地促進了福建地區農業和教育的發展。《八閩通志》通過人物傳記的記載,多元化地展示了福建在科舉、文教、社會、恤政、教化、軍事、海防、水利、交通、農業等方面的發展,這也是《八閩通志》的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體現。
4 結語
黃仲昭編纂的《八閩通志》是福建的第一部省志,具有開創之功,其文獻價值亦非常珍貴,志書中不僅保存了大量寶貴的一手文獻資料,還彌補和勘正了一些前史之疏誤。此外,《八閩通志》尤為重視凸顯八閩地域的特色,對我們研究福建區域史、經濟史、方志史、閩文化、閩省人物及鄉賢文獻等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
注釋:
① 金指金日殫,張指張安世,二人皆為漢代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