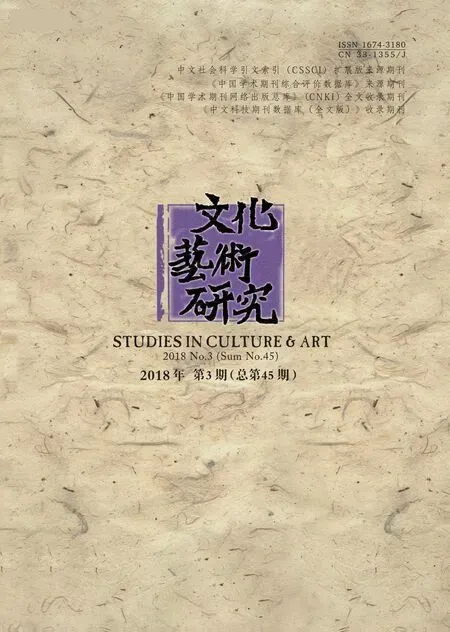論中國當代鄉村電影的詩意空間呈現
——以霍建起電影作品為例
余月秋
(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杭州 310007)
鄉村電影,即以鄉村生活為表現空間,以鄉民為活動主體,既包括“與時代政治結合較緊密的農村題材電影,也包括將鄉村作為文化分析和批判對象的鄉土題材電影”[1]。鄉村電影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與藝術思潮變化中,含有復雜的政治文化因素。電影敘事對鄉村空間的多重想象,形成了對鄉村的多維空間表達。在百年中國電影的鄉村鏡像中,鄉村或淪為政治宣傳的傳聲筒、階級斗爭的演練場,或寓言化為封建的鐵屋子,或理想化為盡善盡美的桃花源。與之對應的是,在空間呈現上,分別表現為革命話語主導下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政治空間,啟蒙話語主導下具有反思性的文化空間,烏托邦話語主導下具有唯美化傾向的詩意空間。
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集中出現了一批唯美詩意的鄉村電影,如《那山 那人 那狗》(1998)、《我的父親母親》(1999)、《草房子》(2000)、《天上草原》(2002)、《天上的戀人》(2002)、《暖》(2003)等,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90年代末的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快速過渡的時期,在市場化的浪潮沖擊下,社會轉型期原有價值的重估、漂泊身份的焦慮及都市生活的功利喧囂均導致了精神家園的失落。另外,中國人上千年的鄉土情結,也使世紀末的都市人渴望重返人情素樸的鄉村,渴求在詩化的鄉土中尋求認同感與歸屬感,以療治時代的精神病痛。詩意唯美的鄉村電影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其鄉村空間不僅呈現出物質空間層面的詩意自然美,還傳達出社會空間層面的和諧人情美。其中,霍建起的詩意鄉村電影尤為突出。美工出身的霍建起善于營造唯美詩意空間,其鄉村影像畫面精致、唯美,音樂舒緩、悠長,鏡頭細膩、含蓄,重內心情感描繪而淡化情節敘述,都使鄉村影像蘊含深厚綿長的韻味。本文主要以霍建起的兩部代表性電影《那山 那人 那狗》(后文簡稱《那》)、《暖》為分析文本,探討當代鄉村電影詩意空間的建構。具體而言,其鄉村電影中的詩意空間呈現為開放空間的遠境、封閉空間的幽境、回憶空間的虛境等三種空間。
一、遠境——開放空間的游觀
宗白華在談到中國畫的空間意識時說:“中國畫的透視法是提神太虛,從世外鳥瞰的立場觀照全整的律動的大自然,他的空間立場是在時間中徘徊移動,游目周覽,集合數層與多方的視點譜成一幅超象虛靈的詩情畫境。所以它的境界偏向遠景。”[2]133霍建起在鄉土空間的營造上借鑒了中國古典繪畫散點透視的空間意識,在《那》中使用了大量橫移長鏡頭、廣角鏡頭和俯仰運動鏡頭,以觀照自然之景及景中之人。在時間的流動中延展出連綿、動態的空間,極大擴展了電影空間的張力與內蘊,呈現出不同于逼仄、喧囂之城市空間的開放與空曠。如《那》伊始,在舒緩低沉的音樂中,先是山村的大全景俯拍鏡頭,爾后是水平的橫移鏡頭,最后,鏡頭定格在一處窗戶透出暖光的村舍上。晨霧彌漫的屋舍,泥濘彎曲的鄉路,安寧空闊的田野,裊裊炊煙,點點燈光,一串串直觀的詩意化田園意象,均喚起都市人的濃濃鄉愁。
霍建起借鑒了古典繪畫中的“游觀”技法。“游觀”,即對自然的“仰觀俯察、遠望近察”,是游動的時空一體的美學觀照方式,其視線上下流動、遠近推移。《那》以橫移長鏡頭呈現一派自由游動的廣闊空間,影片中鏡頭跟隨父子的腳步,以游目式的觀看方式在一趟漫長的郵路行旅中攝入自然景觀,小橋流水、山間小道、蔥蘢綠樹、古樸民居、金黃稻田……將湘西風光徐徐展開,如一幅橫幅長卷的中國畫。鏡頭或遠望如黛群山,或俯視潺潺溪流,或仰視蒼天古樹,游走鏡頭伴隨俯仰鏡頭,構成一組組流動的、節奏化的詩意空間。這與中國畫中“采取數層視點以構成節奏化的空間……視線是流動的,轉折的詩意的創造性的藝術空間”[2]107不謀而合。這種節奏化的流動空間通過移動的長鏡頭,遠景、全景得以呈現,橫移長鏡頭由對群山的靜默凝視緩緩移動到并肩行走中的父子,人物渺小如點,山水為主,人物次之,人與景融于廣袤自然中,將群山萬象盡納入鏡,創造出遼闊空曠的空間感和人景合一的意境感。
“中國畫的散點移動空間和‘三遠’論在本質上就是電影空間的基本內核,觀者隨鏡頭的運動視點進入畫內空間,運動中,時間和空間融為一體。鏡頭的運動視點是以‘我’觀物,‘我’在運動之中仿佛進入時間與空間的隧道,游移之間,物‘我’兩忘, 合而為一。”[3]因而,以運動鏡頭攝取的景物不再是客觀自然的物,而是沾染了觀者——即“我”的主觀色彩的物。影片中的山、水、橋、路等環境造型,不再以講述父子情的自然背景出現,它們也成為角色的一部分,呈現抒情表意的主體性。山與路作為故事的敘述者而存在,父子間由隔閡到消融的情感變化,隨著一段崎嶇而漫長的山路鋪展開來。兒子在潺潺流水中背起父親,水拉近了父子的距離,也消弭了彼此的隔閡。仰視鏡頭中的山是山里人對神圣自然的敬畏,遠景中,山成為父親幾十年不變的郵路歷程的靜默觀照,恰如父親的脊梁,承載了山間普通郵遞員對職業的堅守。正如霍建起所說:“山作為這部影片的重要部分,它沒有多少奇崛,沒有多少荒涼,沒有多少寂寞,它是美的。在兒子的眼里,山是新奇的美,神秘的美;在父親眼里,山是深情的美,難舍難分的美。”[4]在鏡頭的自由流動中,自然人化了,流動鏡頭傳達出情景交融的連綿意境。
在一趟對父子郵路的游觀中,電影用流動的鏡頭將父子深情與自然景象兩相對照,恰如傳統長卷畫,給予觀者連綿不絕的詩意審美體驗,《那》以詩的意境建構起傳統“鄉土中國”。在信息高度發達、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淳樸鄉民、傳統送信的方式,建構起人們對鄉土社會的傳統懷舊及道德懷想,如父親對郵遞事業的忠誠職守、對鄉親的仁愛以及兒子對父親事業的繼承等,表征了霍建起對儒家道德秩序和傳統人倫的肯定與守望。
二、幽境——封閉空間的靜照
如果說《那》是在開放式山路空間的行走中構筑開闊遼遠的詩意空間,《暖》就是在相對封閉的鄉村空間中呈現靜謐幽深的詩意空間。《暖》將原著中發生于北方山東鄉村的故事移植到南方的婺源水鄉,導演對于選景有這樣的解釋:“影片拍攝時已是秋天,秋天的北方是很難看的,因此我就把故事發生地挪到了南方。選擇了江西古徽州的一部分,是一個文化氛圍和自然景觀都特別好的地方。那里的感覺像世外桃源,人特干凈,在那里,你會產生一種離現實很遠的感覺,是一種只有在中國古詩句中才有的境界。”[5]如畫的江南美景和古村落彌漫著的古意與滄桑感,更契合東方美學韻味。古巷的曲折回環這種幽深的空間特性更宜創造電影的詩意,在對青瓦白墻、薄霧輕煙、秋千、蘆葦等意象的靜照中,營造出空蒙的水墨畫般韻致雋永的幽境,今昔交叉的回旋敘事中彌漫著淡淡的愁緒和感傷。不同于《那》中遼遠空間的線條流動,《暖》的鏡頭圍繞封閉鄉間的此情此景此人,營造了一種回旋往復、曲徑通幽的深邃空間,一種千回百轉的纏綿感傷和“近鄉情更怯”的鄉愁。
這種相對封閉狹小的空間,可以通過物與鏡頭的巧妙運用得以延伸并達到幽深,進而引向幽微的心理空間。影片中,窗、鏡子等道具的使用拓展了空間:窗以其通透性連接起內外空間,鏡子可以通過反射拓展空間。如在暖逼仄的家中,影片通過窗、鏡子等物象的運用而產生畫中畫、鏡中鏡的縱深感。影片中一個景深鏡頭讓觀眾透過古舊的雕窗看到站立的暖和井河,及窗內活動的啞巴,暗示出三人隱約的情感糾葛。同時,隔窗取景也與影片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方式互相契合,如家中啞巴與暖的沖突(當暖知道井河寄來的信被啞巴撕掉了以后),是通過女兒丫丫的視線在貼著大白兔糖紙的鏡子看到的。狹窄空間通過鏡子的反射被深化拓展了,激烈的沖突也因鏡子的過濾而溫情化了,這與影片溫情主義的表述相契合。
畫家吳冠中這樣描述江南水鄉:“小橋流水人家之所以誘人,乃由于其結構之完美,小橋——大弧線,流水——長長的細曲線,人家——黑與白的塊面。這樣,塊面、弧線與曲線的搭配組合,構成了多樣變化的畫面。畫不盡江南人家,正由于塊面大小與曲線長短的對歌間譜出無窮的譜。”[6]電影則可以通過鏡頭、場面調度等,將這種畫面結構之美空間化,使之形成深邃可感的詩意空間,如《暖》有一個鏡頭,遠景中透過拱橋下的半圓形橋孔,可以看到露出半身的水牛和趕鴨子的啞巴,鏡頭緩緩移向橋上村口拱形門前站著等待井河回信的暖,景深處淅淅瀝瀝的雨如同珠簾,與曲線橋孔、拱形門交相輝映,構成一組縱深的詩意空間,仿佛一組流動的水墨畫,在暖的失落等待、啞巴的執著守候中,這細雨浸滿了濃濃愁緒。“無邊絲雨細如愁”,《暖》中連綿不斷的細雨給影片蒙上了一層朦朧美、凄迷感。“雨是創造畫意的妙手,蒙蒙細雨會使影調變得十分柔和,使色彩變得格外清新,使景觀變得更加幽遠,因而使畫面呈現令人神迷的詩情畫意。”[7]如啞巴頭戴斗笠盤坐在雨中的青綠草坪上,鴨群嬉戲、水牛吃草,雨聲、鴨聲與靜默的背影引向一個幽遠的意境。再如,濕漉漉的暖的家占據了現在時空的大部分,井河懷著對暖的愧疚來到暖的家,在雨中,回憶過往,微妙互動中衍生出命運的不可捉摸,游子的悔與悟,暖對愛的執著與尊嚴等。雨將兩人引向幽微的心理空間,又在雨中消解過往的傷痛,坦然接受現實。
“靜照的起點在于空諸一切”[2]25,這種幽深空間的營造還仰賴空鏡頭的運用,“空鏡頭在影片中的作用,顯然絕不止于說明人物在什么環境中活動,那僅是空鏡頭最基本、最原始的用法。景最好和人結合起來,寫景是為了寫人。影片中的景物是一定的人眼中的景物,這不單指所謂主觀鏡頭,而是說,景物如果和人的心情相呼應,它給予觀眾的感受跟人物的動作、遭遇給予觀眾的感受就可能相輔相成,融成一體。這樣的鏡頭才是有生命的”[8]。《暖》的空鏡頭不止銜接起現在和過去及對自然的靜默凝視,還是人的心緒的寫照,這更使影片凸顯出形而上的禪境。斷了繩的秋千靜止佇立于空蒙的曉霧中,空氣近乎凝滯,秋千是暖的化身,啞巴曾推著空蕩的秋千,在仿佛推著暖的幻象中露出幸福的笑容。在對殘損的秋千的沉默凝視中,我們仿佛看到暖未來命運的坎坷與苦難。屋檐滴落雨水、風吹蘆葦、遠山空蒙,這些空鏡頭讓畫面近乎“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的禪境。空不是真空,空的形式內蘊著充沛的情感,是“無畫處皆成妙境”,這與中國水墨畫中講究“留白”之法相契合。對空的元素的巧妙處理使影片巧妙地賦予了一種寫意畫的韻味,而且在靜照之中引向更加幽深的心境。
三、虛境——回憶空間的閃現
談起鄉愁回憶,塔可夫斯基說:“無可置疑地,記憶是人類非常重要的資產。它們之所以充滿詩的色彩實非偶然。最美的回憶常常是屬于童年的。當然,回憶必須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家重建過去的基礎;最重要的是,不要遺失了那種特殊的情緒氣氛,沒有它,再精準的回憶也只會喚起失望的苦澀。”[9]《那》和《暖》在懷舊中追尋過往,帶著溫情的感傷,以幽微的情緒、朦朧夢幻的結構和唯美的畫面復現想象中的鄉土空間,構筑出想象的鄉愁烏托邦。兩部電影均采取過往與現在的交叉敘事,大量的回憶空間在旁白的深情敘述中得以建構,回憶空間在柔光鏡、暖色調、舒緩音樂中呈現出如夢似幻般的虛境。向后看的回溯敘事表征著導演對往昔單純歲月的留戀,抑或對傳統人倫道德的回歸,在回歸式的懷舊想象中構筑出美與真的心靈家園。
這種懷舊記憶帶有強烈的抒情意味。為營造回憶空間的情緒氛圍,在表現上則需避實就虛,虛實相生則境出,在電影中則通過柔光鏡和光線的使用來改造粗糲的物質現實,使影像呈現出柔和、夢幻、朦朧之光暈,營造出迥異于現實的具有強烈主觀色彩的銀幕空間。同樣,色彩在表達回憶空間的情緒氛圍中起著重要作用,它有助于情感的渲染與升華,以及懷舊氛圍的營造。在《暖》中,現實的色調是冷青灰蒙的,青色天空、青色石板、灰色房屋、濕冷色調加重了現實的苦澀與無奈;而在暖色調和明亮色彩貫穿于回憶空間的前半段,金黃的稻田、淺黃的蘆葦,紅色絲巾是青春記憶中理想愛情的物化顯現,夕陽透過遠處的屋頂斜灑在坐在稻草堆上的井河與暖,無不讓人勾起對遙遠年代的美好愛情想象。小武生給暖上妝的場景,更將這種詩意虛境推向極致,屋內幾盞燈同雕窗外瀉進的陽光透過柔光鏡營造出一種朦朧美,暖黃色調、柔和光線、特寫鏡頭及輕緩低沉的音樂將人引入一種浪漫溫馨的回憶空間,既營造了一種曖昧情愫,又呈現出一種不真實的虛幻感,而這種虛幻空間的營造和暖的夢想最終破滅兩相對照,凸顯出現實的殘酷與命運的無常。
另外,南方偏遠鄉村濕潤的空氣和長年彌漫的霧氣更加深了影片的朦朧感。彌漫的霧若隱若現,加深了空間的層次感和朦朧感;霧濾掉實景,將畫面提純,且弱化了色彩,而使畫面趨向黑白,造就出水墨畫般的虛境,這也是一種化實為虛之法。《那》隱約出現的被霧氣掩蓋的湘西民居恰如仙境;《暖》中,暖放棄小武生而接受井河這一場景中,兩人在霧中蕩秋千,霧仿佛濾掉了外在的干擾,畫面中純凈得仿佛世界上只有這兩個人的存在,霧不僅為兩人的親近提供契機,而且提升了畫面的意境。
《暖》是根據莫言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而成的,小說講述的是一個現實殘酷的鄉村故事,電影則濾去了現實的堅硬底色,在略帶感傷的過往回溯中使之溫情化。電影更著力于挖掘人性的善與美,這使整部電影具有了超越塵世的純凈和夢幻的基調,這正與身處喧囂都市的人們對心靈家園的向往相契合。正如蘇珊·朗格所言:“電影像夢,則在于它的表現方式。它創造了虛幻的現在,一種直接的幻象出現的秩序。這是夢的方式。”[10]通過這種對時空與記憶的過濾,霍建起在《暖》的歸鄉之旅中構筑了一處夢中的精神家園,而鄉村將成為游子永遠的鄉愁烏托邦,安撫著遠方游子的疲憊靈魂。
結 語
在對鄉村電影開放空間、封閉空間以及回憶空間的審美建構中,霍建起的電影通過借鑒中國傳統美學精神,以含蓄內斂的鏡頭語言營造出詩意空間。其影像的開放空間通過借鑒中國畫的散點透視的空間意識,以及游觀技法創造出連綿流動的詩意意境。封閉空間則是通過窗、鏡子等道具的使用和空鏡頭的運用,以及雨等意象引向幽微的心理空間。回憶空間則以光線、色彩、音樂等手段構筑夢幻般的虛境,這三種空間形式包蘊的情感結構是對鄉土的濃濃鄉愁。霍建起的鄉村電影無疑提升了中國電影的意境之美,展現出濃厚的東方美學意蘊,這是對費穆、吳貽弓等導演的傳承,也是對孫瑜、胡柄榴等將鄉土詩意化、浪漫化的鄉村電影的接應。
對鄉村的田園想象既是傳統原鄉情結的延續,也是從城市視角反思現代性的想象性表達,是對現代人城市病的拯救性策略和對靈魂棲居的詩意追求。然而,過于唯美化的詩意觀照視角,或許會對鄉村的生存本相造成一定程度的遮蔽,如霍建起的近作《1980年代的愛情》(2015)則因過于粉飾與美化鄉村失卻了現實痛感與敘事的厚重感,這是對鄉村田園意象的消費及城市對鄉村的殖民想象,從而過濾掉了鄉村真實生存的苦與痛。因此,在對鄉村電影詩意空間的營造中,在美的呈現中應該有深思的痛感,既要堅守詩意之美,又要以理性燭照人性,或許,這樣一種鄉村電影才能重建人的精神家園與靈魂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