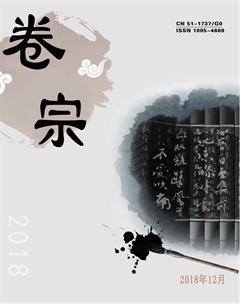關聯理論指導下通俗小說的翻譯
陳曉玲 田翠蕓
摘 要: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西方文化上的聯系變得日益緊密。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一直以來深受歡迎,因此,小說翻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目前,很多小說翻譯或對其研究的關注點始終都在一些經典名著上,往往忽視了通俗小說這一部分,而現有通俗小說的翻譯質量參差不齊,有待提高。本文以小說The Girl With No Name為例,嘗試用關聯理論去指導通俗小說的翻譯,旨在提升翻譯質量,推動和促進通俗小說翻譯的發展。
關鍵詞:關聯理論;小說翻譯;最佳關聯
1 關聯理論
關聯理論是丹·斯珀伯與迪爾德麗·威爾遜于1986年提出的語用學相關原則上發展起來的,見于1986年他倆合著的《關聯:交際與認知》一書(林克難,1994)。之后,丹·斯珀伯與迪爾德麗·威爾遜的學生恩斯特·奧古斯特·格特根據關聯理論對翻譯進行研究,于1991年發表了《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一書,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關聯翻譯理論,進一步發展了關聯理論,闡述了他對翻譯研究的啟示,為翻譯研究帶來了新的角度(王田竹格,2014)。
關聯理論認為,交際是一種有目的、有意圖的人類活動。整個會話過程中,說話人會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以達到自己的交際意圖。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作者的交際意圖,認識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的認知環境,采取各種措施讓譯文讀者通過最小的處理努力獲取最大的語境效果,從而實現最佳關聯。一般情況下,語境效果越大,關聯性越強;語境效果的獲得需要付出努力,處理話語的努力越小,關聯性越強。
要實現最佳關聯,具體來說,首先,譯者必須要從原文語境中體會出作者的交際意圖,也就是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文字傳遞給讀者什么樣的假設,這些假設肯定需要譯者進行反復的推敲和琢磨,單靠簡單的解碼是不夠的。解碼只能告訴我們這些文字表層的語義,而無法傳達作者真正的意圖,語境信息不同、交際對象不同等都會影響交際的成功與否,因此譯者在這一過程中對原文語境的推理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譯者還必須了解譯文讀者的認知環境。原文作者要傳達給讀者的語境假設是否也存在于譯文讀者的語境中,如果存在,譯者需要付出什么樣的努力才能讓讀者理解起來毫不費力。格特認為,一個信息不管聽眾的認知環境而直接傳達給讀者是絕對荒謬的。那些認為翻譯理所當然的是傳遞信息,認為問題的實質是為信息尋找恰當的語言形式的觀點,其根本錯誤在于此(格特,2004)。由此可以看出,譯者對于目的語讀者認知語境的了解和認識也是相當重要的。
2 The Girl With No Name 文本分析
小說 The Girl With No Name 的作者是英國小說家Diney Costeloe,她的父親是是一名出版商,從小她熱愛閱讀,五歲時寫了第一本書,之后還出版了多部系列作品。這部 The Girl With No Name 講述的是納粹時期,大批猶太人遭受迫害并被驅逐出德國,一個名叫Lisa的女孩為避免迫害離開親人和家園,逃到英國被人收養的故事。書中的人物形象生動,故事曲折動人,和大多數通俗小說一樣,整個文本的語言并不晦澀難懂,用詞簡單,幾乎沒有什么生僻詞匯,但用詞簡單并不意味著翻譯就簡單,有些詞匯的詞義紛繁復雜,運用非常靈活,如果直接按照字面意思來譯,由于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差異,并不能準確地表達出原文三言兩語就能表達的深層或多層含義,所以譯者需要根據上下文的語境反復推敲,最終選擇其中最準確的一個。另外,在這部小說中,存在大量的人物對話,這種對話比較瑣碎,句子雖然不長也很簡單,但是對話通常帶有人物內心的感受和思考,如何在漢譯時保留對話的形式,而又能完整地將人物的不同情緒傳達給目的語讀者,這就給譯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難,需要譯者深入地了解兩種語言認知語境,結合翻譯理論,靈活地處理了。
3 實例分析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在小說The Girl With No Name 中詞匯的運用相對簡單,短句和人物對話較多,在源語英語的認知環境下,讀者理解起來并不困難,但如果翻譯成中文,就必須做出一些適當的調整,否則,譯文將無法成功實現交際的目的。當然,在保證交際成功的前提下,譯文應盡可能地向原文靠近:使話語本身具有最佳關聯性,使譯文和原文最大程度地契合,達到逼真境界(趙彥春,1999)。因此,在這一部分,本文將從詞匯意義的選擇、人物對話的翻譯和句法特征一致三個方面,結合實例用關聯理論對譯文做出分析和研究。
3.1 詞匯意義的選擇
這部小說行文流暢,用詞簡單,但是越是簡單的詞匯,翻譯時就越需要不斷地揣摩,因為在小說具體的語境中,譯者不能直接選用詞匯的表面含義,而需要注意對原文的理解,挖掘詞匯的深層含義,充分了解源語和目的語讀者的認知環境,實現作者的交際意圖。
例1:
Gradually they left the hall, foster mothers leading their new charges by the hand, foster fathers carrying suitcases, out into the sprawl of London to begin their new lives.
大廳里的養父母們逐漸散去,養母手挽著孩子,養父提著手提箱,走出火車站,走入倫敦的大街小巷,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原文中的charge一詞的字面意思是“收費,要價;控告,指控”,但是,根據這個例句的上下文語境,大廳里的很多養父母一個個都離開了,然后作者向我們描繪了他們帶著收養的孩子離開車站時的情景,父親大多都幫忙拎著手提箱,而母親應該是手挽著或者牽著孩子,這應該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因此,這里的charges應該選用其延伸義,即“被照管的人,所負責的人”,但是,這里不能采用直譯,否則會讓譯文生澀難懂,也會讓目的語讀者摸不著頭腦。根據句意,這里的“被照管的人,所負責的人”指的就是這些養父母剛剛收養的孩子,所以charge譯為“孩子”,簡單明了。另外,原文中的sprawl字面意思是“延伸和拓展”,在這里作者想要傳達的意思是養父母們帶著孩子從火車站離開了,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譯者可以通過推理得知,他們各自的家是處于倫敦各個地方的,因此譯者把sprawl譯成“大街小巷”而不是“延伸”,體現其語境意義,更加到位。
3.2 人物對話的翻譯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日常對話,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人物對話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都不盡相同。關聯理論認為,翻譯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推理(劉葆花,2008)。所以譯者必須要了解兩種語言的差異,找到作者的交際意圖,然后用符合目的語讀者的表達方式,將完整準確的語義傳遞給讀者。
例2:
Naomi put the suitcase on the bed. ‘Why dont you unpack your things and then come down to the kitchen. And when Lisa looked at her uncomprehendingly, she pulled open the drawers and then pointed to the suitcase, miming unpacking.
娜奧米將手提箱放在床上,對她說:“要不你整理一下你的衣物,然后去廚房吧。”麗薩一臉疑惑地看著她,娜奧米就打開柜子,又指指行李箱,做出打開箱子的手勢。
原文中的語境是麗薩隨著養父母剛剛到自己的新家,娜奧米帶著麗薩來到她的房間參觀,然告訴麗薩,她可以收拾整理一下自己的行李,但是麗薩聽不懂英語,所以娜奧米就打開柜子又指指她的行李箱,讓她明白。娜奧米對麗薩說的原話是why don't you unpack your things and then come down to the kitchen。如果直譯的話就變成“你為什么不收拾你的行李,然后到廚房來呢?”這樣的話,這句話就變成了反問句,語氣上不是那么柔和,而文中麗薩背井離鄉第一次來到她的新家,娜奧米作為她的媽媽,說話一定不會那么強硬,而應該是一種給出建議的語氣,所以譯者翻譯成“要不你收拾一下東西,然后下樓到廚房來?”,這種建議的語氣更容易讓人接受,更符合語境。
例3:
Uncle Dan had waited for them on the corner and when they caught up with him he pointed at a street name, high up on a wall. ‘Kemble Street, he said. ‘Kemble Street. We live in Kemble Street. He looked expectantly at Lisa and when she didnt say anything he said, ‘Kemble Street, and touched her with his pointed finger. ‘You, he said, ‘you say, “I live in Kemble Street.”
丹尼爾叔叔等在拐角處,他們剛到那兒,他就指著墻上高高寫著的街道名字,“肯布爾街,肯-布-爾-街,我們住在肯布爾街。”他充滿期待地看著麗薩,當麗薩還是一言不發,他又重復了一遍“肯布爾街”,并用手指碰了她一下,指著她說:“你,你說,我住在肯布爾街。”
在小說中,麗薩是從德國坐火車來到英國的,所以她不會說英語,丹尼爾和娜奧米帶著她回家,走到他們所住的肯布爾街,丹尼爾想讓麗薩記住街道的名字,所以接連說了幾遍“肯布爾街”,但是如果在翻譯成中文時直譯成“肯布爾街,肯布爾街,我們住在肯布爾街”,譯文就非常蒼白無力,沒有感染力,所以譯者通過推理認為,丹尼爾先是讀了一遍全名“肯布爾街”,因為麗薩聽不懂英語,所以第二遍就一字一頓地讀給麗薩聽,譯文就變成了“肯-布-爾-街”,最后再說“我們住在肯布爾街”,這樣就更加符合原文的邏輯,更具說服力了。
3.3 句法特征一致
句式是原文的一項重要的交際線索,要想再現原文文體風格,適當地保留句式是一個有效方法。在保證譯文通順明了的情況下,保留原文的句式可能是實現最佳關聯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例4:
Tears flooded her eyes as she looked at the clothes so carefully mended and folded by Mutti. What was Mutti doing now? Where was Papa, had he come home yet? How was Martin coping living in an unfamiliar, cramped apartment? Had he learned his way around the furniture?She picked up the photo of them, taken in happier days, all smiling at the camera. Her family. It was the only photograph she had of them.
她看著媽媽給她修補整理好的衣服,眼里滿是淚水。媽媽現在在做什么呢?爸爸又在哪里,他回來了嗎?馬丁在陌生的、狹小的住所該如何生活?他是否弄清楚了家里陳設的位置?麗薩拿出了他們一家四口的照片,這張全家福攝于一個曾經幸福的日子,所有人都微笑著面對鏡頭。這才是她的家。這也是她擁有的唯一一張家人的照片。
麗薩在收拾行李時,看到了她的全家福,于是就有了原文中的連續四個問句,這四個問句關于她的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其實她是想念她的家人了,作者想用這四個問句,表達這個小女孩對家人的思念之情,表達她的傷心和難過。譯者在翻譯時深刻地理解了作者的意圖,因此,保留了原文的句式,譯成中文還是四個問句,用麗薩對家人的擔心表達她對家人的想念和她獨在異鄉的悲傷,增強了語境效果。
4 結語
本文以The Girl With No Name 為例,在關聯理論的指導下,結合在這部小說中遇到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嘗試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研究通俗小說的翻譯。在翻譯的整個過程中,譯者先通讀了全文,了解了整個故事的背景和感情基調,并分析了小說的語言特點,由此把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分成了詞匯意義的選擇、人物對話的翻譯和句式特征一致三個部分,再進行逐一分析,譯者發現中西方讀者的認知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在翻譯時,如果不作出適當的處理,譯文讀者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很難通過推理獲得與源語讀者相同的語境效果,也就無法獲得最佳關聯。因此,雖然通俗小說的語言簡單、清晰,但是在翻譯時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而關聯理論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能夠幫助譯者處理好不同認知環境之間的差異,讓讀者付出最小的努力,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形成最佳關聯。
參考文獻
[1]Ernst-AugustGutt, Gutt.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2]林克難.關聯翻譯理論簡介[J].中國翻譯,1994(4):8-11.
[3]劉葆花.關聯理論視角下漢語歇后語的英譯研究[D].青島科技大學,2008.
[4]王田竹格.關聯理論指導下小說翻譯的風格再現[D].北京外國語大學,2014.
[5]趙彥春.關聯理論對翻譯的解釋力[J].現代外語,1999(3):276-295.
作者簡介
陳曉玲(1993-),女,漢族,江蘇,在讀研究生,華北理工大學,研究方向:英語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