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壞更需要愛嗎
文/街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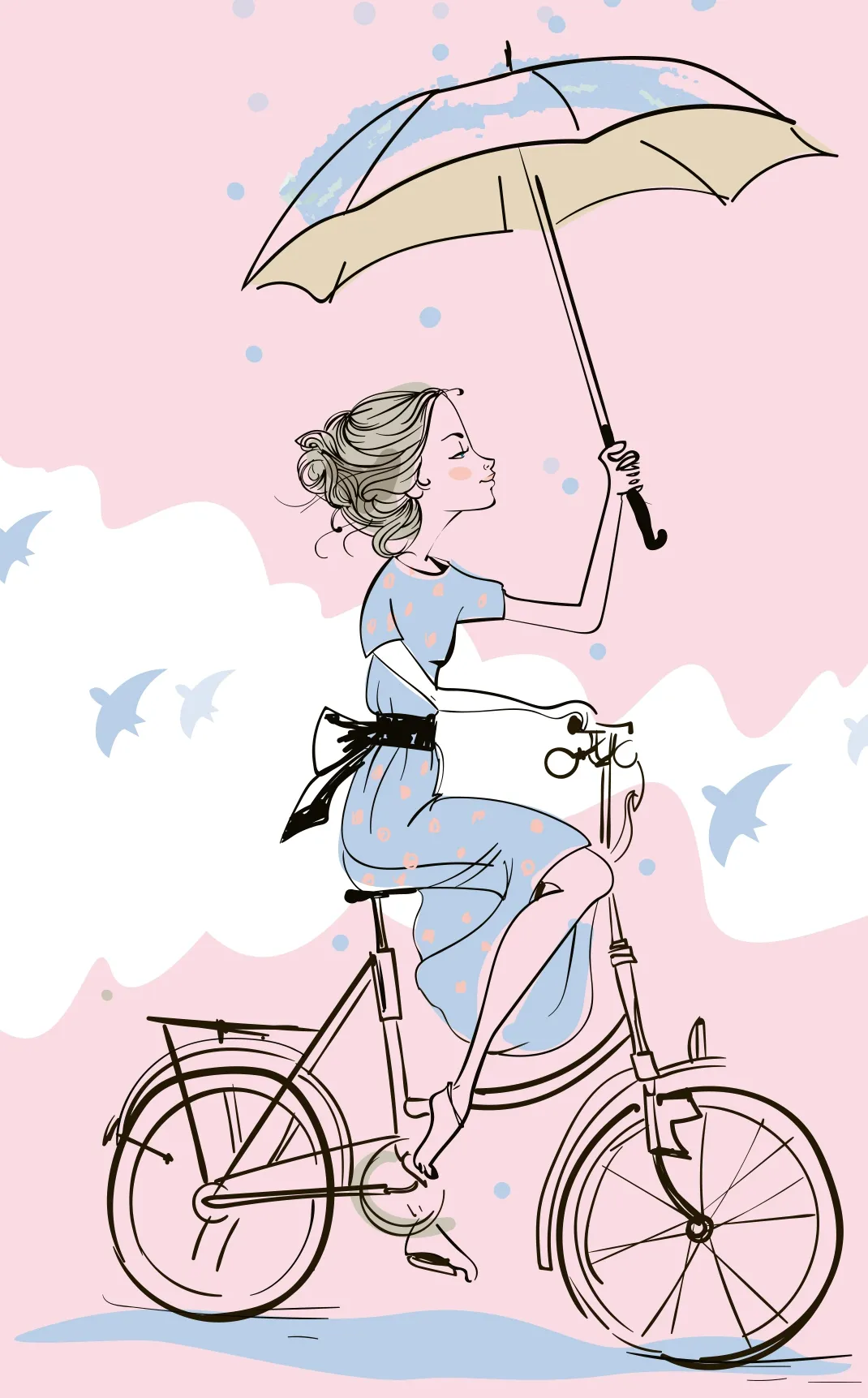
陰郁的冬天摧毀了我生存的意志。我辭掉了工作,從旅途中歸來,鉆進被窩里拒絕再出來,終日掛著兩行鼻涕。大家都說,今年的上海比往年更加冷,因此我也比往年更加撲街。常常一覺睡醒天已經黑了,我坐在漫長的黑夜里,重溫那些氣質陰郁的老電影,一個人的房間越來越空。當我把自己從床里拽起來,想重新觸碰紙質的溫暖,書桌上的圓框眼鏡卻起霧了。我越來越難過,馬上就不行了,打開手機刻不容緩跟50個人say hi,然而其實我對誰都無話可說。是我吃得不夠飽嗎?是我穿得不夠暖嗎?南方的冬天就是這副德性,無論你吃什么穿什么,都覺得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強烈要求政府給每個公民分配10個情人以度過寒冬。
我人生中最慘烈的一次分手發生在去年冬天,不是我跟對方愛得多么刻骨銘心,而是在冬天分手實在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我建議國家出臺新法律嚴禁所有情侶在冬天提出分手,否則提分手者要向被分手者提供足夠的酒精和安眠藥。寒冷還失寵,太慘了真的。本來冬天唯一讓人有點盼頭的就是在那幾個洋節日變著花樣折磨男朋友,突然男朋友沒了,圣誕節沒了,情人節沒了,巧克力沒了,玫瑰花沒了,什么都沒了。沒有人牽你的手,沒有人擁你入懷,沒有人吻你的臉。只剩下手腳冰涼的日復一日,我記得自己在床上昏睡了很長一段時間,突然有一個晚上突發奇想,跑去超市買了一大堆食材和一瓶紅酒,房間里我只開了一盞小臺燈,一個人涮火鍋到零點,醬是用老干媽油辣椒和老抽調的,我覺得特別美味,撐得幾乎反胃,最后抱著瓶紅酒躺在沙發上,肚子快要爆炸了,卻有種奇異的快感,生活是由我自己一手毀掉的,而不是因為誰的缺席。
消沉過后我開始亢奮,年末天后王菲在上海開演唱會。我每天都在打電話訂了一大堆貨,在跨年那個晚上跑到王菲的演唱會賣熒光棒和棒棒糖。這是一件漫無目的的事情:有人愛我,我就撒嬌。沒人愛我,我就吹風。熒光棒沒賣出幾根,賣到最后,街上只剩下買不到演唱會票的粉絲,垂著頭往外走。我把熒光棒和棒棒糖送給那些和我一樣有點失落的人。從里面傳出來的歌聲,剛好我們都會唱,最后匯成一個有點傷心又有點溫情的跨年夜。
一年過去了,我好像還是無法抵抗這寒冬。前幾天收到前任的信息,他突然跟我說:喂,我最近認識個人跟你好像。要說我們之間還剩什么默契,就是這句話透露的信息是這個混蛋又要開始發情了。我心想,哼,似我者死。當然表面上還是得好好端著:哦。像我啥?
像你一樣喜歡冬天啊,喜歡大半夜出來溜達吃燒烤。怕冷又穿得少,然后聳著肩膀一直抖,有夠蠢的。
我才發現,他對我的認識在一年前就停止更新了。他不知道,我現在怕冬天怕得要死,一陣風就能把我撂倒。我嚇得恨不得把自己鎖在衣柜里,哪里還敢大半夜出去吃燒烤。再說我現在比較喜歡吃牛排,有什么好烤的?
“你離開我之后,我就不喜歡冬天了”這種酸不拉幾的話是無論如何我也說不出口的,我能說出口的是:“那過兩天圣誕你把她約出來,脫下你的大外套給她披上,把氣氛搞曖昧點,趁她抬頭看你的時候迅速吻住她的嘴。”
“好主意。”他說。
夜幕降臨了,我從箱子把去年的熒光棒全部翻出來掛在房間里的各個角落。
然后發了同一條信息給所有朋友:帶一瓶酒來我家找我,不然我就去跳樓。
圣誕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