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界定與儒學的復興
張榮生
儒學的界定
國學即國故之學,1904年(光緒三十年),劉師培等人組成了“國學保存會”,次年創辦《國粹學報》,其宗旨為“研究國學,保存國粹”,所謂“國粹”即國之精粹、把千百年來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一概作為國之精華,馬瀛認為這一觀點是錯誤的,寫道:“光緒中葉,海內學者,慮中國固有學術,因西學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國粹之名,容有不當,批評劉師培等人頑固守舊,不符合時代發展之需要。”此時,章太炎也指出國粹之不妥,“以國學為國故,較之以國學為國文、國粹,當妥帖多矣。”胡適同樣認為:“‘國故的名詞比‘國粹好得多。……如果有人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國渣。‘國故(National Past)這個名詞是中立的。”1923年,北京大學成立研究所國學門并創立《國學季刊》,在發刊宣言里,胡適決絕地寫道:“國學在我們的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
現代科學分門別類十分嚴謹,比如哲學、經濟學、人類學、生物學、考古學等,而哲學又分為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倫理學等,國學包括文、史、哲、政經、法多個方面成為綜合學科,因此很難用近代科學分類法加以區分。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以傳統小學作為國學的基礎、小學作為中國古代文學、音韻、訓之詁學是閱讀古籍,進入傳統學術文化入門之鎖鑰。從小學入手,再讀經、史、子、集,章太炎認為這些就是國學的整體。
1938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聘馬一浮講國學,馬一浮認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統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他說:“今楷定國學之名義,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馬一浮還認為:“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乎自專。今言楷定,仁智楷定,則仁智各見,不妨各人自定范圍,疑則一任別參,不能強人必信。”馬一浮的意思是說,用“確定”則是確切無疑之意,不能更改,只能定于一尊;而用“楷定”則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馬一浮對國學的界定,自有其精到之處。
2005年,季羨林與馮其庸提出了“大國學”的觀點,季羨林認為,國學不是單一的“漢學”也不是單一的“儒學”或道家文化,而應該是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馮其庸在《大國學即新國學》一文中指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國學,甲骨文、簡帛文書、敦煌遺書的發現,乃至西學東漸的過程,都極大擴展了國學的領域。國學有新拓展,新進步,就是大國學、新國學。國學的研究對象不能畫地為牢,凡有利于學術問題解決的方法都是國學的研究方法,國學應該堅持中國的學術立場。”這一界定極大的豐富了國學的內涵,符合我們國家、我們民族、新時代的要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就是在這一觀點指導下建立的,“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設立則是這一觀點的體現。
國學的復興
借國學熱的東風,作為國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學也開始成為熱點。1988年在新加坡儒學國際會議上杜維明慨嘆道:現在儒門淡薄,花果飄零。余英時認為儒學現在是一個游魂,東游西蕩,沒有一個附著制度和實體,這么多年過去了,隨著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儒學從花果飄零也走向了復興之路。浙江社會科學院吳光教授認為,儒學復興是跟我們中國的發展緊密相連的,隨著我們國家的和平崛起,我們與國際上的交流,尤其是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拿什么去跟人家對話?習近平在黨的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宏揚”應該成為對話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應該是儒學復興的一個背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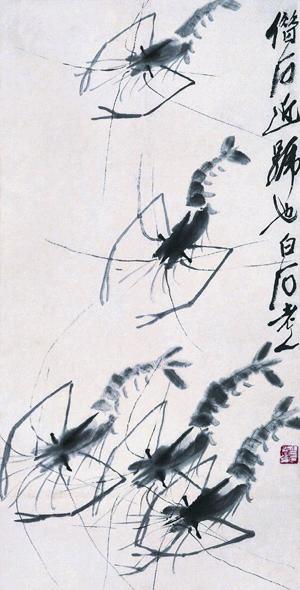
以治國方針而言,一般公認西學重法制而儒學重道德。西方的法治奠基于正義原則之上。古希臘的柏拉圖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把正義看成是確定個體權利的原則,亞里士多德指出,體現和維護正義的法律,作為“毫不偏私的權衡”就是保證“人們互不侵犯對方的權利”的一種“合同”,西方以權利契約關系的法制傳統作為發端,而“法律是全沒有感情的”,這樣的法制導致了人際關系情感的淡漠,社會成為自我的冷冰冰的世界。儒家的德治以“仁者愛人”和“舍生取義”的仁義原則為主旨,人與人之間應該通過仁義的道德情感加以溝通,這是治理社會,建立和諧秩序的保證,因此用教化作為手段喚醒潛含的仁義之情的良心,比之單純的立法、執法更重要。
“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正是這一思想指導下,習近平指出:“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因而我們堅決屏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利益,這才是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準則。
職是之故,儒學復興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1.根據最新資料,目前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共有516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已成為世界范圍規模最大的教學合作項目。美國有110所孔子學院,秘魯是只有2000多萬人口,居然籌建了四所孔子學院,居然籌建有四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一開始是國家漢辦為推廣漢語在國外建立的,由于中國的崛起,不少外國人想通過孔子學院來了解中國文化。
特朗普的外孫女6歲的阿拉貝拉已不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秀中文,在剛結束的特朗普首次訪華行程中,阿拉貝拉在超萌視頻中,扎著丸子頭,笑容十分甜美,流利的用漢語向“習爺爺”“彭奶奶”問好之后,她便唱起了《美麗的田野》,還背誦了《三字經》、唐詩,甚至聲情并茂地表演了一段中國兒歌《我的好媽媽》。阿拉貝拉在網絡上走紅,折射出學習中文已成為美國家庭的一大風尚。紐約Lifestyle Resources職業介紹所的工作人員羅什表示,不少家庭要找“能說中文尤其是普通話的保姆”,中文保姆十分搶手,年薪比其他保姆多拿2萬美元。英國倫敦開辦的中英雙語小學,半天教授孩子學中文,半天英文,盡管這所學校一年收費1.7萬英鎊,已吸引了來自美國、俄羅斯、新加坡的學生被家長送來就讀。除特朗普家外,英國小王子、亞馬遜和臉譜的創始人的孩子都在學中文,中國文化在全球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正在與日俱增。endprint
2.在世界范圍內,以儒學為主旨的會議連續不斷,比如在山東召開的世界儒學大會是由文化部、山東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山東省文化廳、中國孔子基金會、國際儒學聯合會、孔子研究共同承辦,其宗旨是在世界范圍內組織、舉辦儒學研究活動,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增強各個國、各個民族人民之間的理解和信任。
3.以儒學為主旨的協會、研究院、研究中心遍布全國。比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國學院或儒學高等研究院。規模最大的國際儒學聯合會召開過多次學術會議和高峰論壇。
4.蒙學館遍布全國,比如山東的“尼山圣源書院”是民間的,“尼山”論壇則是官方支持的。
5.國內外許多地方都有了孔子塑像,比如國家博物館北廣場就樹立了著名雕塑家吳為山的孔子青銅像,美國現代都市廣場、英國菲茨威廉博物館雕塑廣場中心都有孔子雕像。著名學者匡亞明曾說:“世界歷史三大名人,耶穌、釋迦牟尼、孔子,前兩者搞宗教,而孔子一生為人類,我看孔子更偉大。”英國皇家肖像雕塑家協會主席看過孔子塑像后寫道:“現在我坐在這里看孔夫子,覺得他就是那樣,越看越覺得是那樣,那么久遠,就像我國的莎士比亞,他像一條河流的源泉,像中國文化長河的源頭,放在中心是非常好的設計,似乎所有這些雕像都源于孔夫子。”
6.官方意識形態融入了儒學因素。漢代王充《論衡》提出了“實事嫉妄”的思想。他的師弟班固在《漢書》進一步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概念,以后王船山、曾國藩也非常重視,這又影響到毛澤東,毛澤東把實事求是融入到了馬克思主義系統中,延安整風時對實事求是作出了新的解說。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求”就是去研究;“是”就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性。“實事求是”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我們提出的“以人為本”“以德治國”“和諧社會”“小康社會”這些理念無不滲透了儒學思想。“遵紀守法”古代叫“禮”,即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尊重科學”即是“智”;“誠實守信”“以信為本”那是“信”;“公平正義”那是“義”,“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關。
陳寅恪曾經指出:“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的儒家學說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和生活方面”,盡管歷史上曾經有過非儒反儒的波折,儒學的影響是股巨大的力量,比如孝心文化就是源自儒家思想。鄉規、族規、家規、家訓以至人情往來都滲透了千百年來形成的儒家思想。
作為意識形態,儒學是時代產物,反映了時代的政治、經濟、生活多個方面的要求,從原始儒家孔子開始,儒學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又添加了不同朝代、不同階級的價值取向,比如西周時期的六藝、禮樂是指導思想作風的,書、數是對自然科學知識和文化技能的掌握,射御則是軍事技能及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孔子之后的“六藝”則變成了純粹書本的知識。再比如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就不是孔子提出的。五常作為傳統社會處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人際關系的具體內容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必然有其糟粕部分,因此我們必須分別對待,不能全盤接收。
在儒學復興過程中也有一股逆流,比如蔣慶認為儒學必須成為一種宗教,一種國教,殊不知宗教必須具有敢冒天下大不韙、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領袖,有一整套莊嚴的儀式,有純正神圣的信仰,尤其是有死后世界的設想和安排,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關注的是彼岸世界,而儒學關注的是現實世界。孔子主張“未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分明與宗教風馬牛不相及。蔣慶還有具體的政治設計:設立“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院”,庶民院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通儒院”是儒家人物推舉出來的,國體院則是歷代貴族包括圣人后裔組成的,這一切只能是與時代背道而馳的幻想,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