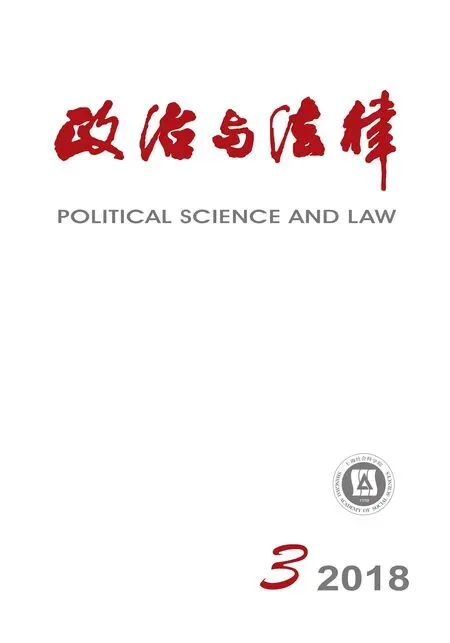論罪名生成的方法
(南開大學法學院,天津300350)
罪名是刑法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通常對罪名的研究多是討論刑法修正案條款應生成什么罪名,或者就是研究罪名分類、罪名生成原則等問題,雖然這或多或少都會涉及罪名生成的方法,但專門探討罪名生成方法的理論還很欠缺。罪名生成的方法應以刑法規定為前提,以概括、準確為首要價值,旨在為罪名生成提供具體的操作指南,實現罪名生成的標準化作業。我國最高審判機關通過司法解釋命名的468個罪名(以下簡稱:司法罪名)提供了犯罪的統一性名稱,解決了群罪無名、一罪多名的混亂,但是司法罪名也存在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關于‘兩高’解釋所存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三不’:不統一、不一致、不盡合適。”①艾小樂、王耀忠:《論真正的罪名法定化》,《當代法學》2003年第6期。“盡管,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權威機關統一了罪名,這些林林總總的罪名絕大部分同刑法的精神和內涵相一致,也同人們的理解與習慣相吻合,但仔細推敲,卻發現錯誤不少。有些罪名,或曲解刑法的意圖,或語意不清,或錯用、濫用標點。比如,‘過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過失’,何來‘以’?又如,‘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封建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這一罪名由于錯用了標點,語意變得混亂不清。再如,‘傳播性病罪’這一罪名,同刑法規定的明知自己患有性病,仍然賣淫嫖娼的構成要件相去甚遠。再看,‘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這一罪名,僅僅因為標點符號有誤,‘珍貴’也成了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的對象。”②陳浩然:《應用刑法學分論》,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3頁。
我國刑法的整體性修改迫在眉睫,隨著罪名法定化呼聲的高漲,司法罪名需要系統性修正的迫切性也日益顯現,借此契機,罪名寫入刑法也具有了可能性。“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罪名應在刑法中明文規定。因此,立法罪名是必由之路,是理想模式。遺憾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刑法典的誕生,從舊刑法典到新刑法典,從刑法修正案一到刑法修正案七,均忽視罪名的法定化工作。”*張繼鋼:《罪名分類新論》,《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不論是司法罪名的自我修正與完善,還是罪名法定化的實施,都需要有一套可行的操作方案,從而實現罪名的標準化、可控化。本文從罪名單位的形式基準、行為類型是罪名數量的實質標準、罪名寄居于罪狀之內、保障罪名的體系性等四個方面探討罪名生成的方法。
一、分則條(款)是罪名個數的基本單位(罪名個數的形式標準)
直觀上,罪刑法條是罪名的載體,罪名在法條中若隱若現,罪名的個數取決于法律的規定,當然也受對行為類型認識的制約。以一條文一罪名的原則、一罪名一罪狀的立法模式取代純粹的罪狀描述的立法模式在短期內尚難實現的情況下,即使罪名沒能法定化,罪名也應遵循一條(款)一罪名的立法規則,多條(款)一罪名和一條(款)多罪名是極少數例外。
(一)“條”的含義
條是成文法中標明了“條”字樣的記載文字的單位,在法律中“條”有特定的含義,我國《立法法》明確規定了法律的邏輯層次,該法第61條規定:“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目。編、章、節、條的序號用中文數字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序號用中文數字加括號依次表述,目的序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法律標題的題注應當載明制定機關、通過日期。經過修改的法律,應當依次載明修改機關、修改日期。”“在中國幾千年的法律發展史上,成文法的編制體例相對穩定也有所變化,但條是其中重要的且恒定的結構單位。在現行法律文本中,條仍居于重要位置,它形式獨特、作用突出。”*劉風景:《法條標題設置的理據與技術》,《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1期。條是法律的最基本單位,是組成法律的主體和框架。法律可以沒有編、章、節、款、項,但不能沒有條,一些小型的法律就只有條。如《反分裂國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等法律就只有條,沒有編、章、節等劃分。
刑法中的法條可以劃分為罪刑法條和非罪刑法條,非罪刑法條又分為規定性法條、說明性法條和擬制性法條。罪名來自于罪刑法條,罪名并不取材于提示法條與擬制法條,但與它們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擬定罪名時,有學者誤解了罪名與提示法條與擬制法條之間的關系,在這兩種法條中擬定出新的罪名,導致罪名的徒勞增加。例如,“對于《刑法》第183條的規定,理論上有人認為這是刑法規定的一個獨立的犯罪,罪名為‘虛假理賠罪’”。*劉憲權、楊興培:《刑法學專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頁。這是對提示性法條(注意規定)的性質誤讀,它雖與罪名相關但不創設新罪名。
一條一罪名限于在條之下沒有規定數款的情況,或者雖有多個款,但其他款并不涉及新罪狀。一款一罪名是條內有多款,不同的款規定了不同的罪狀、顯示出不同的行為類型。
(二)以條(款)為單位作為罪名個數的形式基準
一個罪刑條文通常是對一個犯罪類型(犯罪構成)的規定,一個犯罪類型(犯罪構成)應該配有一個罪名。“每一條文只能規定一項內容,不能將幾項不同的內容包括在同一條文之內;同一項內容最好規定在同一個條文中,通常不能將其分割在幾個不同的法條中。”*同前注④,劉風景文。我國刑法典起草者使用法條表述犯罪時,已預設了一個犯罪構成觀念,立法者不會把不相干的行為放在一個法條里。起草者的潛意識里就是用一個法條塑造一個犯罪,這也符合基本的認知心理。作為一種形式上的判斷,一法條一罪名是立法和生成罪名應堅持的基本邏輯,在沒有優勢理由的情況下,不應打破一條一罪名的準則。在學理罪名和司法罪名的擬定實踐中,存在大量違反一法條一罪名的錯誤做法,應引起我們的警惕和反思。
司法罪名未能理清我國《刑法》第114條和第115條的關系,沒有清晰認識到一條一罪名(一款一罪名)在擬定罪名時的價值,將這兩條的規定擬制為放火罪、失火罪、決水罪、過失決水罪、爆炸罪、過失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0個罪名。我國《刑法》第114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過失犯前款罪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對比這兩條規定可知,第114條規定的是犯罪未遂、第115條是對犯罪既遂的規定,二者的犯罪構成并不相同,根據一條一罪名的準則和法條中“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第114條應擬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未遂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5條第1款應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嚴重后果罪),第2款應為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樣第114條、第115條的10個罪實則應為3個罪名。
我國《刑法》第188條也是一個條款被司法解釋擬定了兩個罪名,遭到了學者的質疑。“刑法第118條,在本罪中,電力設備也屬于易燃易爆設備,而且是與燃氣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設備并列的、可選擇的對象,即只要行為人故意破壞其中一種對象并危害公共安全的,便成立本條犯罪。司法解釋將118條規定的罪狀確定為兩個罪名的合理性,還是值得懷疑的。”*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77頁。
我國《刑法》第280條之一只有一個罪刑條款,即“使用偽造、變造的或者盜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社會保障卡、駕駛證等依法可以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有學者主張本罪“應確定為‘使用偽造、變造的身份證件罪’和‘盜用他人身份證件罪’”。*趙秉志、劉志偉、袁彬:《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及修改罪名的意見》,《法學雜志》2015年第10期。司法罪名也將其擬定為兩個罪名,但只要對“使用偽造、變造的或者盜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社會保障卡、駕駛證等依法可以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進行概括,會發現不管是“使用偽造、變造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還是“盜用他人的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都屬于使用虛假的身份證件。將本條擬定為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盜用身份證件罪兩個罪名,增加了罪名數量,也制造了兩者之間的對立,本罪應擬定為使用虛假的身份證件罪。可見,在罪名生成的實踐中,司法罪名并沒有嚴格堅持一條(款)一罪名的基本準則,導致本該擬定為一個罪名的情況被割裂擬定為了數個罪名。不合理的罪名增加,不僅僅是增加了罪名數量,還帶來了罪與罪之間關系認定的復雜性,影響到認識錯誤理論及數罪認定規則等的適用。
二、行為類型是罪名數量的實質標準(罪名個數的實質標準)
對行為類型的判斷一方面取決于立法規定,另一方面還取決于我們對犯罪的規范性理解,行為類型是一個被構建的觀念,其類型數量受制于刑法的具體規定,也受教義學知識的制約,是一個被解讀、被構建的類型學形態。行為類型的構建是罪數理論的一塊重要內容,在罪名生成中具有重要價值。罪名個數應與行為類型相吻合,否則就會導致罪名與真實的犯罪類型錯位。
(一)行為類型制約罪名個數
一條(款)一罪名是從形式上審視罪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內容。另外,對罪名個數和罪名確定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法律規定的行為類型。如何判定一個犯罪構成還是數個犯罪構成,有“犯意說(意思說)、法益說(結果說)、行為說、構成要件說”。*參見[日]板倉宏:《刑法縂論》(第1版補訂版),勁草書房2007年版,第342-343頁。“構成要件標準說雖說與形式的構成要件論相類似,但并非僅在形式上評價構成要件的該當性,而是將構成要件連同犯意、被害法益、行為等綜合的判斷,作為構成要件該當數的判斷。那意味著,可以說構成要件標準說包含綜合說。此外,脫離構成要件,討論罪數的標準很可能欠缺明確性。”*同上注,板倉宏文,第343頁。行為類型是被構建的行為框架,類型的結構最終取決于立法規定。即便如此,即使立法設定了行為類型,我們能否準確識別,也是一個問題。識別行為類型存在基本的共識,那就是明顯具有類型邊際和類型標志的應視為不同的類型,是不同的罪名。例如,故意與過失、實害犯與危險犯是不同的犯罪類型,應視為不同的犯罪。由于我國刑法的立法處理技術的粗糙,從行為類型來看,即使規定在同一法條中也仍屬于不同的犯罪,對罪名司法解釋時需要正確解讀出它們屬于不同犯罪,對它們分別擬定罪名。
第一,抽象危險犯和具體危險犯是兩種不同的犯罪類型,即使處在同一法條中,也應當將其理解為不同的行為類型。但在司法罪名中,卻存在這種遺憾。“前者,明文要求惹起‘危險’的犯罪是具體的危險犯,后者,法律規定通常具有危險的行為的犯罪是抽象危險犯,無論如何實質的危險的發生作為構成要件要素不變,只不過前者是高度的危險,后者包含比較緩和(危險)的情況。”*[日]山口厚:《刑法縂論》(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46頁。“它們的區別在于如果一定的危險作為必要就是‘具體的危險犯’,如果一般的危險已經足夠就是‘抽象的危險犯’。”*[日]中山研一:《口述刑法縂論》(補訂版),成文堂2005年版,第76頁。我國《刑法》第127條針對危險物質和槍支、彈藥、爆炸物,分別規定了具體的危險犯和抽象的危險犯。我國《刑法》第127條規定:“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的,或者盜竊、搶奪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的,或者搶劫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或者盜竊、搶奪國家機關、軍警人員、民兵的槍支、彈藥、爆炸物的,……”司法罪名將它們擬定為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第127條第1款),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第127條第2款)。這顯然沒有認識到“槍支、彈藥、爆炸物與危險物質”構成要件的不同,前者是抽象危險犯,后者是具體危險犯,它們是不同的犯罪類型。因此,該條應擬定為盜竊、搶奪、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罪和盜竊、搶奪、搶劫危險物質罪。
第二,漢語有其自己的表意系統和語法規則,一般來說應該嚴格按照法條使用的表述文字理解行為類型,但是立法語言有時也會出現表述錯誤,在刑法發生了表述錯誤的情況下,司法解釋就要采用補正解釋的方法還原其本來意義。在立法語言錯誤的情況下,可以拋開錯誤用語的“虛假”束縛,依據立法原意和刑法教義學知識“主動”還原出真正的行為類型。我國《刑法》第251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情節嚴重的,……”“和”的意義表示并列,從立法用語來看,“非法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必須同時具備才能成立犯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發布的《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第13條第1款規定:“‘和’連接的并列句子成分,其前后成分無主次之分,互換位置后在語法意義上不會發生意思變化,但是在法律表述中應當根據句子成分的重要性、邏輯關系或者用語習慣排序。”根據該規定,這里的“和”屬于刑法用語使用錯誤,“和”應解釋為“或者”才符合立法原意。“第251條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第256條規定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該兩條使用了‘和’字分別連接其不同的犯罪對象,這里應該說是立法中對連接詞的誤用。以第251條規定為例,如果使用‘和’字連接,則表示兩種對象,即宗教信仰自由與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累加,行為只有同時侵害這兩種犯罪對象才構成犯罪。然而從兩種對象來看并無內在的聯系,分析立法原意也并不會要求行為必須侵害兩對象才構成犯罪,而應該是列舉性對象,侵害其中一個對象就構成該條犯罪,因而,這里的‘和’是‘或者’的誤用,應該認為上述兩條亦為列舉并列式條文。”*陳興良主編:《刑法各論的一般理論》(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頁。由此,司法罪名中的非法剝奪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罪完全尊重了行為類型,避免了盲目依據刑法文字所帶來的風險。
第三,在同一法條里,如果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行為,就應當視為不同的行為類型,司法解釋中確定罪名時應將它們規定為不同的罪名。我國《刑法》第358條第1款規定:“組織、強迫他人賣淫的,……”很顯然本條規定的是簡單罪狀,這個簡單罪狀其實不簡單,因為組織賣淫與強迫賣淫并不屬于一個類型。組織賣淫屬于侵害性風俗的犯罪,其以被賣淫人的同意為前提。強迫賣淫雖然也侵犯了性風俗,但那是本罪的附屬法益,真正法益是他人的性自主權。“從犯罪構成的角度,強迫婦女賣淫的行為完全符合強奸罪的犯罪構成,行為人實際上構成強奸罪的間接正犯,或者至少是強奸罪的共犯。”*勞東燕:《強奸罪與嫖宿幼女罪的關系新論》,《清華法學》2011年第2期。強迫他人賣淫與強奸罪、強制猥褻、侮辱罪是競合關系,正因為與組織賣淫罪屬于一類犯罪,所以司法罪名將它們分別擬定為獨立罪名,正確反映了我國《刑法》第358條第1款的規定。
(二)以條(款)作為罪名個數單位的例外
“刑法也有其內在的科學性,其邏輯、結構、內容、體系乃至立法技術的發展、變化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尤其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受社會觀念、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刑法的這種內在規律更是無法逆轉,必須在刑法立法中加以考慮。”*趙秉志:《中國刑法的百年變革》,《政法論壇》2012年第1期。刑法規定了非常龐雜的內容,特別是我國采用統一的刑法典編纂體例,原來的單行刑法和行政刑法的內容都融入了刑法典。由于規制的內容多、范圍廣,刑法出于表述精煉、歸類清晰、強化對比等方面的考慮,將類型相近的犯罪構成放在同一條款中也很普遍。此外,為了強化認知,也會在一個犯罪構成內部對某個行為類型做了獨立規定,乃至在一條內部存有多個行為類型。為了保證刑法典的多元性和明確性,一條(款)一罪名作為通例的同時,一條(款)數罪名和數條一罪名的存在有其客觀性。
1.一條(款)數罪名
刑法未對罪名法定化,一個條文規定了一罪名還是數罪名,往往爭議激烈,但可以肯定的是,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結果犯和危險犯是不同的行為類型,即使在同一條文中也應成立獨立的犯罪。故意和過失在刑法中一條(款)數罪名并不少見,司法罪名也將它們擬定為不同的罪名。例如,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第168條),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第398條)、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第397條),執行判決、裁定失職罪、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第399條第3款),故意泄露軍事秘密罪、過失泄露軍事秘密罪(第432條)。有些司法罪名并沒有重視條文中故意和過失類型的并存,錯誤的將它們擬定為了一個罪名。據此,交通事故罪(第133條)應為交通事故罪、交通肇事逃逸罪;食品監管瀆職罪(第408條之一)應為食品監管濫用職權罪、食品監管玩忽職守罪;擅離、玩忽軍事職守罪(第425條)應為擅離軍事職守罪、玩忽軍事職守罪。
2.數條(款)一罪名
我國刑法典制定時刻意強調某一類型或者對某種情況進行了擬制,就對某一類型在其他條款中另外做了再次或者特別規定。數條一罪名在罪刑條款中并不多見,這種情況多存在于擬制條款。刑法中存在大量的法律擬制,這些罪刑擬制條款與原罪名法條之間存在著數條(款)一罪名的關系,除了法律擬制之外的數條一罪名應盡量避免。擬制之外的數條(款)一罪名存在諸多弊端,諸如罪名的辨別成本增加、數個條文之間的實質關系難以分解、數條規定的必要性存疑等等。例如我國《刑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第385條規定了受賄罪,第388條規定的是斡旋受賄行為,也是一種受賄行為,立法者擔心法律適用者不能辨別翰旋受賄行為的受賄性質,便于第388條做了特別規定,這樣,第385條與第388條共同規定了受賄罪。同樣,我國《刑法》第394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國內公務活動或者對外交往中接受禮物,依照國家規定應當交公而不交公,數額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394條是對第382條貪污罪類型的擴展,這兩條共同規定了貪污罪。
(三)司法罪名對行為類型的違反
司法罪名中存在將數個行為類型當作一個類型或者將一個類型當作數個類型,沒有準確識別出行為類型的情況并不鮮見。諸如,我國《刑法》第133條之所以存在解釋論上的諸多困惑,就是將過失犯罪和故意犯罪錯誤地當成了一個過失犯罪所導致。該條理解為交通事故罪和交通逃逸罪兩個罪名或者交通事故罪、交通逃逸罪和交通逃逸致死罪三個罪名,諸多問題就迎刃而解。“將交通事故罪定位于過失犯罪,將交通逃逸罪和交通逃逸致死罪定位于故意犯罪,還有利于與司法解釋的協調。把‘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作一個獨立的罪名,符合該種行為的主客觀特征,與這種行為的客觀實際相符,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對這種行為作出的司法解釋。同時,可以解決理論上關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觀罪過的爭論,防止出現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定相同罪名的邏輯矛盾,解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行為的共同犯罪問題,不至于出現共同過失犯罪這一與法律規定相悖的結論。”*朱建華、都龍元:《“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應為獨立罪名》,《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換言之,“從理論上講,完全應該將肇事逃逸和逃逸致死命名為單獨的罪名,不僅指使他人逃逸而致人死亡的能成立共犯,指使他人肇事逃逸的也能成立共犯,從而避免受到過失犯不能成立共犯的指責”。*陳洪兵:《公共危險犯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頁。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第114條原本只規定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未遂罪,卻被司法解釋分別擬定為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國《刑法》第115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被司法解釋分別擬定為5個罪名。
以下司法解釋對我國《刑法》的規定所擬定的罪名中也存在罪名個數錯誤:第116條應為破壞交通工具罪,第117條應為破壞交通設施罪,第118條應為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第119條第1款應為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易燃易爆設備罪,第119條第2款應為過失損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易燃易爆設備罪,第124條應為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過失損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第128條第2款應為公務用槍人員出租、出借槍支罪,第128條第3款應為配置槍支人員出租、出借槍支罪,第151條第1款應為走私武器、彈藥、核材料、偽造的貨幣罪,第151條第2款應為走私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及其制品罪,第237條應為強制猥褻罪,第270條第1款應為侵占罪,第270條第2款應為侵占脫離占有物罪,第277條第1款應為妨害公務罪,第277條第2款應為阻礙人大代表執行職務罪,第277條第3款應為阻礙紅十字會人員履行職責罪,第277條第4款應為阻礙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罪,第291條之一第1款應為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第320條應為提供偽造的出入境證件、出售出入境證件罪,第323條應為破壞界碑、界樁、永久性測量標志罪,第375條第1款應為偽造、變造、買賣、盜竊、搶奪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第396條應為私分國有資產罪,第408條之一應為食品監管濫用職權罪、食品監管玩忽職守罪,第425條應為擅離軍事職守罪、玩忽軍事職守罪。
三、罪名寄居于罪狀之內(罪名生成的素材)
罪名的最顯著特征是概括性,這在簡單罪狀中表現的更為直觀。罪名是對罪狀的概括,立法罪名、司法罪名或者學理罪名都是對罪狀的壓縮提取(當然,極個別簡單罪狀足夠簡練,已無需壓縮)。出現罪名比罪狀還長的情況是極端例外,這樣的罪名也不符合概括性的要求。“例如,《刑法》341條描述的罪狀是:‘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或者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后半段規定的犯罪稱為‘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這一罪名不但沒有對罪狀進行概括,反而其字數增加了,罪狀的字數是30個(包括標點符號),罪名的字數是32個(包括標點符號)。正確的罪名應該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罪’。”*李希慧主編:《刑法各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罪名對罪狀壓縮概括時要準確反映罪狀。“即給犯罪取名的時候,要求構成罪名的詞的內部形式盡可能的把必要的罪狀的內容揭示出來,盡可能的反映出某種犯罪的本質特征,以使受眾能夠通過罪名即能顧名思義知道該犯罪的罪狀的基本內容,了解該犯罪的本質特征。”*吳平:《罪名概念新探》,《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針對一個罪狀,往往會有多種罪名生成方案,諸如針對我國《刑法》第395條第1款就存在眾多罪名方案。“關于本罪的規定,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罪名:(1)非法得利罪、(2)非法所得罪、(3)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4)巨額財產來源非法罪、(5)不能說明巨額財產或者支出合法來源罪、(6)隱瞞巨額財產來源罪、(7)拒不說明巨額財產真實來源罪、(8)擁有不能說明之財產罪、(9)擁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罪。”*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16頁。罪名根植于罪狀,梳理罪名與罪狀的關系,觀察現有468個司法罪名與刑法分則的具體規定,罪名取材與罪狀存在三種樣態。
(一)引用罪名
在簡單罪狀中,無需對罪狀進行大規模裁剪壓縮,直接引用罪狀或者稍微裁剪罪狀就可以作為罪名。簡言之,引用罪名是直接引用罪狀作為罪名。我國《刑法》中存在著大量的引用罪名,例如投敵叛變罪(第108條),間諜罪(第110條),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第127條第1款),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第128條第1款),非法出租、出借槍支罪(第128條第2款、第3款),走私武器、彈藥罪(第151條第1款),偽造貨幣罪(第170條),變造貨幣罪(第173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176條),假冒專利罪(第216條),故意殺人罪(第232條),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45條),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57條),詐騙罪(第266條),聚眾哄搶罪(第268條),故意毀壞財物罪(第275條),傳授犯罪方法罪(第295條),偷越國(邊)境罪(第322條),組織淫穢表演罪(第365條),冒充軍人招搖撞騙罪(第372條),戰時造謠擾亂軍心罪(第378條),私放俘虜罪(第447條),等等。引用罪名不會發生罪名錯誤或者欠缺精準的情形,因為罪名與罪狀等同或者幾乎等同,引用罪名多見于簡單罪狀,很少存在引證罪狀中。
(二)截取罪名
在描述罪狀、引證罪狀和空白罪狀中,其罪狀一般對犯罪特征的描述較為詳細,對這類罪狀生成罪名時需要對其進行概括,概括的方法是摘取罪狀中的關鍵詞生成罪名。以這種方法命名的罪名可以稱為截取罪名。截取罪名是罪名生成中最常用、最需要謹慎對待的罪名生成方法。我國司法罪名中大部分的截取罪名準確反映了罪狀,諸如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第123條),高利轉貸罪(第175條),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第253條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第286條之一),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第314條)等,這些罪名既使用了罪狀中的關鍵詞,又對罪狀進行了準確的概括。
截取罪名既要堅持文本原則,又要對罪狀進行提煉,要做到概括、準確,這并非易事。針對同一規定,截取罪名往往會有各種樣態,需要在概括的基礎上選取最具準確性的罪名。針對我國《刑法》第276條之一擬定何種罪名,眾說紛紜,“學者們根據刑法條文提出了若干個不同的罪名,如‘拒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罪’、‘逃避支付或者不支付勞動者報酬罪’、‘惡意欠薪罪’、‘欠薪罪’、‘欠薪逃匿罪’等”。*莊乾龍:《拒不支付報酬犯罪比較研究》,《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受到質疑的罪名,多是截取罪名,截取罪名出現問題的癥結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截取罪名偏離了文本。有些截取罪名中雖然使用了罪狀中的部分用語,但遺漏了罪狀中的核心用語或者對核心用語進行了替換,沒有堅持采用罪狀用語表述罪名。我國《刑法》第360條第1款(傳播性病罪)規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賣淫、嫖娼的,……”該條中的罪狀表述的是行為犯,只要患有性病賣淫嫖娼就成立犯罪,而司法解釋確定的傳播性病罪給人傳遞的信息是,只有將性病傳播給他人才成立犯罪,這顯然與罪狀傳遞出來的信息不匹配。其原因在于本罪名偏離了刑法條文的文義,本罪應擬定為性病患者賣淫、嫖娼罪。過失損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規定的罪狀是“過失犯前款罪,造成嚴重后果的”,而該條第1款是“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的”,結合該條第1款,第2款的完整表述應當是“過失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的,造成嚴重后果的”。“在漢語通行的習慣用語中,損壞偏于與過失搭配,破壞側重與故意搭配。由此,與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對應的可以是過失損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趙桂民、趙泉河:《〈刑法修正案(五)〉新增軍事犯罪的罪名探析》,《武警學院學報》2007年第7期。先不討論破壞是否必須是故意、損壞才能是過失,該法條原文使用了“過失破壞”,那么罪名就應當擬定為“過失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罪”。
第二,截取罪名沒有抓住實質。采用關鍵詞擬定罪名時,抓住實質性詞匯之后,還要進行一定的概括,像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第291條之一第2款)就合理、準確概括了罪狀。“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第二款罪名沒有明確‘險情’‘疫情’‘災情’‘警情’,但在具體適用法條和罪名時,不能將本罪犯罪對象的外延隨意泛化,應嚴格限定在刑法規定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范圍內。”*宋丹:《〈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六)〉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檢察》2015第22期。罪名不是罪狀本身,罪名只標示犯罪,抓住了構成要件的核心內容就做好了關鍵性的一步。
相反,徇私枉法罪(第399條第1款)概括得過于抽象,沒能體現出該罪的實質。對比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第399條第2款),雖然兩者都遵循了文本原則,該條第1款罪名明顯沒有抓住犯罪的實質(未體現在刑事領域),導致罪名在準確性方面大打折扣。“即單純從罪名上看,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就是徇私枉法罪。因而,從徇私枉法罪概念的內涵分析,徇私枉法罪與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兩罪之間非并列關系,而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包含于徇私枉法罪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邏輯關系。”*武小鳳:《關于詢私枉法罪罪名存在的問題》,《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6年第2期。將我國《刑法》第399條第1款擬定為刑事枉法罪,既抓住了罪名的實質,又能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相區別,很好地滿足了概括性、不偏離文本、協調、準確等四項罪名生成的原則。
(三)借鑒罪名
“在‘兩高’罪名表確定的罪名中,有許多罪名的文字過長,概括性較差,專業性過強,少數罪名甚至帶有經院哲學的繁瑣性,念起來十分繞口,不利于普法宣傳和司法適用。勿可諱言,有些罪名難以表述則是立法本身的缺陷。鑒于這種情況,有學者提出,某些罪名在難以用準確而又簡潔的文字表述時,可以采用約定俗成的辦法解決。”*趙延光:《論犯罪構成與罪名確定》,《法學》1999年第5期。有些罪名已有了民間的或者國外的先行實踐,在與刑法罪狀高度符合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拿來借鑒為罪名使用。借鑒罪名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約定俗成的罪名。有些罪名已在民間或者學界獲得了廣泛認可,具有很好的社會認知度,貪污罪(第382條)是其典型。學理罪名中使用約定俗成罪名并不少見,但基于對法條文義的倚重,司法罪名多未采用。如我國《刑法》第121條規定:“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司法解釋將本條擬定為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張明楷教授認為:“許多論著將本罪的罪名概括為‘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也有學者將本罪的罪名概括為‘以誹謗手段損害商業、商品信譽罪’。實際上,本罪行為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商業誹謗行為,因而概括為商業誹謗罪較為合適。”*同前注,張明楷書,第680頁。如果將本罪認定為商業誹謗罪,就是對約定俗成罪名的使用,未嘗不可,筆者認為最好將本罪擬定為損害商譽罪。針對我國《刑法》第302條規定的“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尸體、尸骨、骨灰的,……”有學者主張將其罪狀擬定為毀尸罪,毀尸罪就是一個典型的約定罪名,“毀尸滅跡”的字眼在新聞中更是常見,但該約定罪名并不準確。“在征求意見過程中,有意見認為,為使罪名更為簡潔、準確,可確定為‘毀尸罪’。經研究認為,‘毀尸’雖然更為簡潔,但不能準確概括罪狀中的‘盜竊’‘侮辱’‘骨灰’等核心要件,故未采納該意見。”*同前注,宋丹文。吸毒罪這個罪名也帶有強烈的約定俗成的痕跡。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第353條第1款)、強迫他人吸毒罪(第353條第2款)、容留他人吸毒罪(第354條)中刑法用語使用的是“吸食、注射毒品”,如果嚴格依據法條文義,則這些罪名都應為“吸食、注射毒品罪”。“吸食、注射毒品”在民間通稱為吸毒,可以說這幾個罪名也都是約定罪名。
第二類是過去的罪名或者外國罪名。刑法借鑒過去(比如民國時期)或者國外刑法制定了某個罪名,在生成罪名時可以直接使用其來源名稱,比如遺棄罪(第261條)。有學者主張對我國《刑法》第133條“交通運輸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罪名化。“將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為予以罪名化,那么,應將之概括為什么樣的罪名呢?有觀點將其確定為‘逃離交通肇事現場罪’或者‘交通肇事逃逸罪’。筆者認為,‘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實質內容在于不履行救助義務,故以‘不救助罪’命名更佳。”*黃河:《論“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罪名化》,《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4期。將本罪擬定為“不救助罪”是采用的借鑒罪名,德國刑法中就有不救助罪(也稱見危不救罪、不進行救助罪),*德國刑法323條c項規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生時,根據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救助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要義務而不進行救助的,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用在這里顯然與罪狀的規定不契合,出現頭大(罪名)身子小(罪狀)的邏輯失衡,不救助罪從罪名上看絕不僅指“交通肇事后不救助”。筆者也主張將逃逸行為罪名化,但不主張使用“不救助罪”的罪名,應使用“交通肇事逃逸罪”。
第三類是國際公約、條約中規定的罪名。隨著全球一體化,犯罪治理也加強了國際合作,我國也加入了一些懲治犯罪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我國不承認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直接使用,條約、公約需要轉化成我國國內法才能適用。那些來源于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罪名,可以直接使用它們在國際上的通用稱謂。諸如洗錢罪(第191條)、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第388條之一)等。“眾所周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規定的罪名予以使用,其具有填補我國受賄罪處罰空隙的功能。”*陳洪兵:《貪污賄賂瀆職罪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頁。
罪狀可以為罪名提供可靠的文本支持,能用罪狀文字表述罪名的就應當優先考慮使用罪狀用語,特別是簡單罪狀中,必須使用引用罪名。截取罪名盡管存在諸多弊端,但也要優先于借鑒罪名,除非有特別的理由(如約定俗成、罪名條款來自外國或者國際法規等),不得輕易使用借鑒罪名。引用罪名優先,截取罪名次之,最后才可以考慮借鑒罪名,這也是罪名生成原則中的文本原則的真意。
四、完備的罪名需要兼顧體系性照應(罪名之間的制約)
罪名之間不是孤立的存在,從罪名用語、罪名結構再到罪名關系都有著內在的呼應和連動,為保證罪名的準確性和概括性,就不能無視罪名的體系性對罪名的制約與矯正。罪名的體系性重在罪名結構、罪名用語、罪名內容的一致與呼應以及在罪名體系之內審視罪名,防止罪名從用語到內容的失范。
(一)罪名的體系性要求
“任何一個法條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看似孤立的、對立的法條實質上存在密切的照應。任何法律規范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任何具體規范都是‘整個法律秩序’(Gesamtrechtsordnung)之一部分,換言之,它在一部法律內部或與其他法律的許多法律規范都存在內部與外部的緊密聯系。”*[德]魏德士:《法理學》,吳越、丁曉春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頁。罪名作為犯罪的名稱,既要與罪狀吻合,也要同其他罪名呼應,這就要協調好前后罪名的關系,兼顧整體罪名群。命名罪名要注重形式一致性的同時重視罪名之間的實質差別,做到格式、用語的相對統一又不失準確。罪名的體系性有著重要的價值,能直觀體現出分布在不同章節的罪名之間的聯系,它有助于對罪名內容的理解,也便利對罪名的模糊檢索。
我國的司法罪名在體系性方面做的不夠好,存在很多不統一或者抵牾的瑕疵,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刑法在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中,規定了數量眾多的‘戰時’犯罪,多數罪名中帶有‘戰時’這一核心要素,但在個別罪名中卻沒有標明罪狀中的‘戰時’。盡管‘兩高’的司法解釋對大多數戰時犯罪均有所標明,但對于少數戰時犯罪仍付闕如,如‘兩高’的《規定》和《意見》對刑法第112條規定的‘資敵罪’、第428條規定的‘違令作戰消極罪’、第429條規定的‘拒不救援友鄰部隊罪’和第444條規定的‘遺棄傷病軍人罪’等罪名,均沒有加上‘戰時犯罪’的識別標志,從而無法判斷其是戰時犯罪還是平時與戰時均可構成的犯罪。”*李永升:《關于“兩高”確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討》,《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我國司法罪名在遺漏相關戰時罪名中的“戰時”的同時,個別罪名中的“戰時”又顯得純屬多余,不符合罪名概括性原則。戰時臨陣脫逃罪(第424條)中“臨陣既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一個空間概念,臨陣已經足以表明時間是在戰時,在罪名中沒有必要再同義反復的出現‘戰時’”。*晉濤:《罪名雜亂和虛化研究》,《廣西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
(二)罪名體系性的保障技術
落實協調性,應著眼于結構的一致、用語的統一、內容的呼應,注意罪名與罪狀的契合關系,關注罪名在類罪名和罪名群中的地位,追求罪名的準確性和協調性。罪名的協調性能標示罪名之間的潛在聯系,有助于刑法的系統性應用。
1.結構的一致
弄清楚罪名結構,有利于對罪名的識記,更為重要的是為以后罪名生成提供一種規范模式,即在保證罪名準確的前提下,罪名結構盡量合理。罪名的結構有文法結構和刑法結構之分,罪名的文法結構是根據漢語語法知識分析罪名構成,罪名的刑法結構是根據刑法的犯罪構成分析罪名。從文法角度和刑法角度可以對罪名結構進行多元檢視,罪名結構具有豐富的內容,其中一項就是在罪名結構中,故意和過失具有特別重要的識別作用,過失犯罪會在罪名中特別標明。“(日本——引者注)刑法38條第1項規定沒有故意的行為不處罰(處罰故意為原則),結果是,過失犯在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作為例外被處罰(38條第1項但書)。那意味著犯罪因故意行為而存在。”*[日]前田雅英:《刑法縂論講義》(第4版),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年版,第202頁。基于處罰故意犯罪為基準、處罰過失犯罪為例外的刑法立法模式,一般都會在過失犯罪罪名中突顯罪過因素,即過失犯罪的刑法結構都會有主觀要素這一特定內容,表明過失的詞匯有“過失”“事故”“失職”“玩忽職守”等,即都會在罪名中體現出過失的性質。我國《刑法》第363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為他人提供書號,出版淫穢書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穢書刊而提供書號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該條第2款(前引省略號之后的規定)作為過失犯罪,沒有在罪名中出現表明過失的字樣,不符合過失犯罪罪名體例,致使犯罪性質極為模糊。該條第2款的司法罪名是為他人提供書號出版淫穢書刊罪,該款是過失犯罪卻沒有使用表明過失的字樣,同時“為”在漢語中有目的性傾向,單純從罪名字面看明顯是故意犯罪。因此該罪名中應添加“過失”,即“過失提供書號出版淫穢書刊罪”或者是“過失提供書號罪”。
2.用語的統一
一類罪名或者相關聯的罪名,若罪狀中對相關行為使用了相同的詞匯,那么罪名應盡量使用相同詞匯。我國《刑法》第131條到第139條規定中,除了危險駕駛罪和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之外,都是規定過失造成重大責任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這一組過失犯罪罪名五花八門,應對罪名進行統一整編,統一擬定為事故罪,如飛行事故罪、鐵路事故罪、交通事故罪等。
我國《刑法》中沒有強制罪的一般規定,但有各種特殊的強制罪,如強迫交易罪(第226條)、強迫勞動罪(第244條)、強迫賣血罪(第333條)、強迫他人吸毒罪(第353條第2款)、強迫賣淫罪(第358條第1款),這些罪名對應的罪狀中都有“強迫他人”的字樣,只有強迫他人吸毒罪罪名中有“他人”字樣。強迫類犯罪的對象只能是他人,這也是這些犯罪中沒有突出他人的原因。因此,強迫他人吸毒罪應為強迫吸毒罪。當然,強制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第120條之五)、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57條)、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第262條之一)等也屬于強迫類犯罪,但不屬于本文在罪名意義上關注的對象。
戰時造謠擾亂軍心罪(第378條)與戰時造謠惑眾罪(第433條)存在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對比它們的罪狀“戰時造謠惑眾,擾亂軍心的”,與“戰時造謠惑眾,動搖軍心的”措辭幾乎一樣,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特殊主體——軍人。司法罪名為了區別二者,將后者擬定為“戰時造謠惑眾罪”,導致兩個罪名極為相似,使得罪名的區分功能喪失,實則應將后者擬定為“軍人戰時造謠動搖軍心罪”。
我國《刑法》第310條規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該條被擬定為窩藏、包庇罪,與之相對應的特殊罪名,即我國《刑法》第294條第4款被擬定為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第349條被擬定為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這其中固然有法條用語的原因,前者使用了“窩藏、包庇”,其他兩個法條中只有“包庇”,根據法條罪狀擬定出這樣的罪名也似乎合情合理。但問題是,立法為何對后兩個條文沒有規定“窩藏”呢?“立法者之所以在窩藏罪罪狀中只列舉了‘提供隱藏處所、財物’的情形,是因為這種情形是常見多發的,屬于不完全列舉。凡是與‘提供隱藏處所、財物’相當的有助于犯罪的人逃匿的行為,都應被評價為符合窩藏罪的客觀要件的行為。”*陳洪兵:《指使交通肇事者逃逸構成遺棄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教唆犯》,《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5期。窩藏是有助于逃跑的行為,但根據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來看,“窩藏”不過是“包庇”的一種,凡是對犯罪人的追訴起到阻止作用的,都可理解為包庇。因此,我國《刑法》第310條就是對包庇罪的規定。
雖然罪名應注意用語的統一性,但不能為了統一性而罔顧準確性。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第339條第1款)與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第339條第2款)就存著為統一性而統一的問題,導致前者罪名產生錯誤。
3.內容的呼應
罪名之間相互呼應能體現出犯罪在內容上的一致、互補或者關聯。內容上的相互關系,取決于刑法的立法規定,也取決于對法條的理解。罪名內容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構建的認知,體現了我們對犯罪的掌握程度。我國《刑法》第271條第1款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可能該條在我國《刑法》第270條(侵占罪)之后的緣故,為了用語的一致性,將本條擬制為職務侵占罪。其實本罪的內容“占為己有”內涵豐富,包括所有將單位財物轉化為個人所有的行為,諸如利用職權的竊取、騙取、侵占等行為。“刑法第271條第1款規定的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也應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可見,刑法第271條規定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公司、企業、單位人員的貪污行為,而不只是侵占行為。認為本條規定了職務侵占罪的理論與司法實踐,都同時認為本罪行為包括侵吞、竊取、騙取等行為。既然如此,將本罪概括為職務侵占罪并不能反映本罪的全貌,不如將本罪概括為公司、企業、單位人員貪污罪。”*同前注⑨,張明楷書,第179頁。
徇私枉法罪(第399條第1款)與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第399條第2款)是并列的兩種犯罪行為,由于徇私枉法罪沒有體現內容上與后者的呼應性,導致兩個罪名之間的關系變得模糊。“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將刑法第399條第2款規定的罪名確定為枉法裁判罪,就不盡科學、準確。因為,枉法裁判既可以是在民事、行政訴訟中枉法裁判,也可以是在刑事訴訟中枉法裁判,枉法裁判罪,顯然不能對此加以區分,因而不妥。”*彭文華、王昭武、吳江:《中國刑法罪刑適用》(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根據刑法分則條文的規定,‘徇私枉法罪’被規定為‘徇私、徇情枉法刑事裁判罪’或者干脆就規定為‘刑事枉法裁判罪’,而399條第二款規定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較為明晰,且符合法條規定的本意。”*李立豐:《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兩個罪名〈規定〉中的罪名設定研究》,《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年2期。
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2條)與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第253條)也是一般與個別的關系,但是兩個罪名沒有體現出內容上的呼應關系,應將后者擬定為郵政工作人員侵犯通信自由罪。
五、結 論
以往,我國司法罪名的生成一直是“跟著感覺走”,罪名生成的方法作為一項“秘而不宣的技能”被各種潛意識支配著,在罪名生成實踐中未能發揮宏觀調控、微觀制約的作用,致使罪名出現雜亂、虛化等問題,罪名生成方法的缺位難辭其咎。隨著罪名法定化契機的到來,更加需要系統探討罪名生成的原則、方法,從而保證罪名的統一、穩定和準確。
罪名生成方法的缺失,一方面源自我們對罪名問題的不重視,使得罪名理論的發展不完備,另一方面是對罪名生成的低要求,認為罪名只是一個簡單的稱謂,用來標示不同法條的內容而已。刑法是精準性法律和嚴密的知識體系,刑法中的任何一個問題和環節都應當經過認真交鋒、嚴肅論證、充分檢視,因為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充滿了“邪惡”,把控不好就會被濫用,背離其目的和功能。罪名生成作為一個重要的刑法問題,應有一套規范的操作標準,讓罪名生成的運作機理和程序完整呈現出來,把罪名生成工作科學化。
法條是罪名的載體,刑法起草者在表述每一個犯罪構成時,出于完整性的需要,通常是一個條文塑造一個罪名(一條一罪名),條文是判斷罪名個數的基本單位。刑法出于明確性和經濟性的考量,不可避免存在一條(款)多罪名、多條(款)一罪名的罪名體例。建立在刑法規定基礎上的犯罪類型對于罪名的個數起到關鍵作用。行為類型是被構建的行為框架,類型的結構取決于立法規定。即便立法設定了行為類型,我們能否準確識別,也是一個問題。識別行為類型存在基本的共識,明顯具有類型邊際和類型識別標志的應視為不同的類型,是不同的罪名。依據行為類型來看,司法罪名中很多違反了立法原意,將立法上的一個行為類型生成為數個罪名或者將立法上數個行為類型生成為一個罪名的并不少見。罪名來源于罪狀,根據罪名是否使用了罪狀用語,存在引用罪名、截取罪名和借鑒罪名三種類型,三者體現罪名與罪狀用語之間從完全等同到徹底分離的關系。截取罪名是多數罪名的生成方法,但也會出現偏離文本、未抓到罪狀實質的缺陷。罪名的體系性,可以保障某一罪名與相關罪名相呼應,增強罪名間的聯系。應在結構的一致、用語的統一、內容的呼應這三個向度上把握好罪名的協調性。
罪名的生成應在科學方法引導下展開,這樣罪名才能達到概括、準確、協調。忽視罪名生成方法,僅僅根據對法條的理解生成罪名,是罪名存在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罪名生成方法的構建和實施,有助于對現行罪名的反思,也有助于未來罪名的準確和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