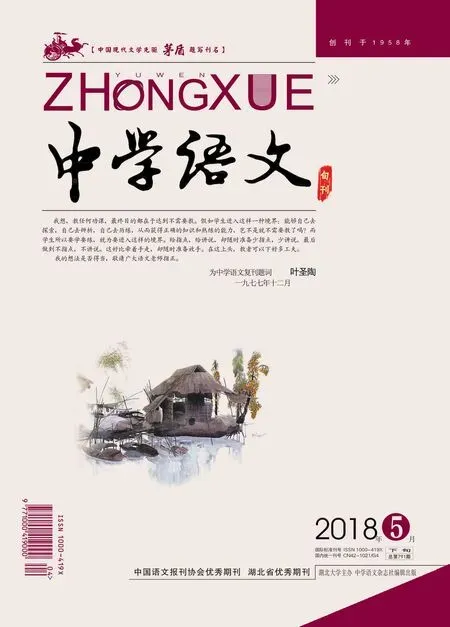談《項鏈》的諷刺藝術
程效恒
莫泊桑的《項鏈》不僅因為人物形象的生動鮮明、語言的典雅規范受到中外讀者的喜愛,而且它更以絕妙的諷刺藝術贏得了世界讀者的喝彩。在這篇小說中,作者成功地運用了欲擒故縱和卒章亮底的藝術手法,對主人公瑪蒂爾德愛慕虛榮和追求享樂的思想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瑪蒂爾德是一個具有極強的虛榮心和濃厚的享樂思想的婦女。她長得花容月貌,然而命運卻好像處處跟她為難,她不幸出生在一個貧寒的家庭,最后又偏偏跟教育部的一個小書記結了婚,過著貧困的生活。她的年輕美貌與其置身的惡劣環境之間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因此她常有一種明珠暗投的悲哀。她身在寒家,可心躺在上流社會的溫床上,在幻想中享受著現實生活中她享受不到的榮華富貴,所以她常常在夢想與現實矛盾對立中,觸物傷懷,終日郁郁寡歡。她是一個深深地打上了資產階級思想烙印的婦女形象,瑪蒂爾德的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極具典型性,又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作為具有較強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作者很有必要對這種思想進行尖銳的批判。在小說開頭作者細膩地描寫了瑪蒂爾德的內心痛苦,工筆式地刻畫了她的性格特征后,便展開了小說的故事情節,這故事情節不僅是瑪蒂爾德思想情感的自我展示,更主要的它是作者通過瑪蒂爾德傳奇經歷的安排,對她虛榮心理和享樂思想進行的辛辣的諷刺。
作者首先運用欲擒故縱的手法對瑪蒂爾德進行了諷刺。為了給不清醒的主人翁深刻的教訓,作者一邊不斷地誘發主人公的欲望,一邊有意不斷地滿足她的欲望,讓她得寸進尺,執迷不悟。在滿足她一個又一個欲望的同時,一邊又暗中設置陷阱,而在她得到極大滿足,處于快樂峰巔而忘乎所以時,作者卻讓災禍降臨,給其致命的打擊。就像瑪蒂爾德要星星,作者想辦法給他摘星星,瑪蒂爾德要月亮,作者就給他登天的梯子,然而就在瑪蒂爾德快要摘上月亮的時候,作者卻抽掉了她腳下的梯子,讓她沉沉地摔在現實的泥潭中。瑪蒂爾德一心夢想著上流社會的生活,但又為沒有機會,“沒有法子讓一個有錢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而懊惱,這時作者投其所好,給她一個機會——教育部舉辦的舞會。這對她無疑是喜從天降,然而她又為沒有漂亮的衣服而犯愁,這時作者又滿足了她,讓她的丈夫傾其所有為她做了一身華衣。有了華衣,她又為沒有耀眼的首飾大發脾氣,這樣作者又讓她在朋友那里借到。瑪蒂爾德的欲望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高明的作者總是讓瑪蒂爾德在山重水復疑無路時,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讓她所有的欲望得到滿足,當這些欲望滿足后,作者將瑪蒂爾德捧上幸福的云端:她在舞會上大出風頭,多年的郁悶在這里得到渲泄,多年的缺憾在這里得到補償。瑪蒂爾德在享受所謂的幸福時卻忘了身邊的荊棘,她沒有想到她那豪華的裝扮與她的生活實際是多么不相稱啊,她沒有想到她陶醉的“幸福”對她來說是根本就是虛無縹緲的云霧。就在瑪蒂爾德處于幸福是云端時,作者卻撇開了雙手,瑪蒂爾德被沉沉地摔在地上——她丟失了項鏈。這真是樂極生悲,從此她走上了一條曲折艱難的道路,一夜的狂歡換來十年的艱辛,這對她是多么沉重的打擊啊!這對她死要面子,不顧實際,打腫臉充胖子的虛榮心和庸俗作風是多么辛辣的諷刺!
然而作者意猶未盡,接著又用卒章亮底的手法對瑪蒂爾德進行更有力的嘲弄。面對飛來橫禍,她堅強地挺直了腰桿。為了賠償一掛項鏈,她在屈辱和艱辛中度過了整整十個春秋。瑪蒂爾德的遭遇夠令人同情了,但是當她還清所有的債務,準備揚眉吐氣,坦坦蕩蕩地生活時,作者卻在故事的結尾安排了瑪蒂爾德和朋友邂逅的場面。朋友告訴她當年她借的那掛項鏈是假的,這對瑪蒂爾德來說簡直是晴大霹靂,斷送了十年的青春竟為了一掛假項鏈,這出人意料的真相無疑將剛剛爬出苦難深淵的瑪蒂爾德再一次推下痛苦的深淵,無論瑪蒂爾德哭也好、罵也好、呼天搶地也好,十年的青春是不會回來的了。蘇聯作家蘇曼諾夫說過:“藝術的打擊力量要放到最后。”作者有意把項鏈的真相在十年之后、故事結束時亮出,這對主人翁來說是殘酷的玩笑、深刻的嘲弄,一個人苦有所值還不算苦,但苦得冤枉才是苦下堪言。
欲擒故縱和卒章亮底的諷刺手法使情節富于戲劇性,然而它并沒有減弱諷刺的力度,相反使諷刺更加辛辣。作者嚴格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嚴格遵循生活邏輯。失項鏈的情節看似偶然但不隨意,它的背后隱藏著生活的必然,結尾的平地波瀾也非作者故作驚人之筆,而是合情合理的結局。瑪帶爾瑪蒂爾德追求的是一種“玩物式”的境遇,她就是不失項鏈,也不會擺脫悲劇命運的。
這兩種諷刺手法在小說中各盡其妙:“欲擒故縱”使諷刺產生了讓主人翁大起大落,爬得越高,摔得越沉的效果,而“卒章亮底”則使主人翁明白十年的艱辛竟是吃了一場啞巴虧,它加深了諷刺的力量。
《項鏈》的諷刺藝術是辛辣的、絕妙的,是耐人尋味啟人深思的。瑪蒂爾德脖子上的那掛項鏈,無疑是一具沉重的精神枷瑣,它沒有將瑪蒂爾德帶進人人間天堂,而是將她引人精神的煉獄。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力量牽著瑪蒂爾德走進一場人生騙局?那么是誰騙了她呢?仔細品味便可發現,作者嘲諷瑪蒂爾德的虛榮心和享樂思想的同時,不是將批判的矛頭也指向了造成主人翁悲劇命運的社會根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