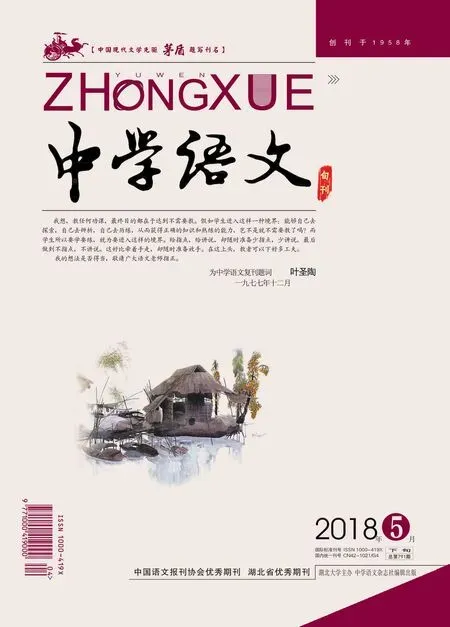淺談“文本細讀”的具體運用
楊昌盛
文本細讀,作為一個文學批評的重要術語,最早是由英美新批評派理論家克林斯·布魯克斯提出的。其實我們古人很早就知道這個道理。比如孔子讀《易》的“韋編三絕”,漢唐的經學家注釋經傳,明清的評點家,在字里行間的濃墨重彩,乃至古代蒙學的背誦抄默,無一不是文本細讀的具體應用。
《新課程標準》對“閱讀與鑒賞”提出了明確要求:“能感受形象,品味語言,領悟作品的豐富內涵,體會其藝術表現力,有自己的情感體驗和思考。”這一課程目標,直接決定了語文課堂閱讀教學的終極目標:引導學生走進文本世界,走進作家的心靈世界,從而建構學生個體的心靈空間。
《林黛玉進賈府》中的“半舊”一詞出現了三次,有著豐富的表現力。開篇黛玉看到賈府門前仆人的“列坐”,不可忽略。“列坐”之“列”,正是仆人秩序井然的表現,更是賈府管理嚴格的有力見證。
再如:“出了垂花門,早有眾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綢車,邢夫人攜了黛玉,坐在上面,眾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眾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攙著黛玉的手,進入院中。”
這一段文字講究很多,也有排場,邢夫人攜了黛玉,坐在上面。其實,這段路并不長,但是,作為賈母的外孫女的林黛玉首次登舅舅之門,坐車是一種氣派,更是一種規矩。作者不厭其煩地一一陳述,如果讀者細心體會,就會體味到一種雍容華貴的生活氣息。
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我今兒才算見了!……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讓他們去歇歇。”
黛玉初到,由眾婆子“扶”下轎;賈母出來,由兩個人“攙著”;王熙鳳出場,由一群媳婦丫鬟“圍擁”而來;迎春三姊妹由下人“簇擁”而來。在文本里,使用“攜”字,只有兩個人,其一是作為長輩的王夫人對黛玉經常用“攜”,其二就是平輩熙鳳對黛玉也是用了“攜”字。我們不妨就這一動詞進行替換,稍作比較。如換上“拉”字,就顯粗魯,沒有教養;換上“搭”字,黛玉年幼,弱不禁風,無關切之意;換上“扶”字,不合輩分,有失身份。唯有“攜”字,既符合身份,又能體現出對黛玉的體恤、憐惜之情。第二次“攜”發生在熙鳳的對賈母的“誤讀”之后,馬上自我檢討,“攜”住黛玉,“攜”字前,再加一個“忙”字,其見風使舵,八面玲瓏,不著痕跡。
《祝福》中虛詞的運用也是令人嘆為觀止。文中“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這句話中的“如此”,如同三個特寫鏡頭,反復出現,意在強調封建迷信與“祝福”活動對人們思想鉗制的程度。“自然”“也”這兩個虛詞,點明了祝福活動的傳承與延續,并為下文敘寫祥林嫂的悲劇預設了環境氛圍。再如文中“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抬到賀家坳,喉嚨已經全啞了……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里,還是罵……”這是敘寫祥林嫂被迫再嫁時的表現。其中四個“也”字,概括列舉“回頭人出嫁”時的種種反抗表現。從“面”的角度揭示封建禮教毒害婦女心靈的普遍性,“全”“還是”等詞語則從范圍或程度上折射祥林嫂“出格”的行為,從“點”的角度凸顯封建禮教迫害祥林嫂心靈的深刻性。
文本中,“我們的阿毛”出現了多次,除了表現母親對兒子的疼愛以及慈母對亡子的深切思念,學生討論后,發現“我們”二字表明祥林嫂心里有老六;“我們的阿毛”讓祥林嫂成了女人,真正的為人妻、為人母,“母親也胖,兒子也胖”,這就是生活幸福的真實寫照,以至多年以后,柳媽跟她談起老六,祥林嫂“笑了”,這是小說唯一直接寫祥林嫂“笑了”,初到魯鎮,只是“笑影”,捐門檻后也只是“高興似的”,唯有這里是“笑了”,可見她和老六有一段幸福的婚姻;“我們的阿毛”讓祥林嫂真正享有了做人的權利,獲得了做人的尊嚴。所有的這些幸福,在“我們的阿毛”一死,祥林嫂又回到無依無靠,人人欺之的境地。狼吃了“我們的阿毛”,更吃掉了祥林嫂一生的希望。
關注量詞。文中“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時……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長桌上,……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一堆”和“一部”這兩處量詞的運用,可見作者高超的遣詞造句能力。從行文上看,“一堆”修飾的是《康熙字典》,“一部”修飾的是《近思錄集注》《四書襯》。如果說“一部”還是寫實的話,那么“一堆”與前面的“脫落”“松松”,后面的“未必完全”幾個詞語相呼應,形象的組成了一副破敗、沒落、陳舊的畫面。眾所周知,《康熙字典》是一部識文斷字的工具書,而《近思錄集注》、《四書襯》則是封建禮教的正統著作。作者正是巧妙地運用了這兩個量詞,并進行形象的對比,寫出了前者的凌亂、殘缺,后者的整潔、完整,從而深刻具體地刻畫了人物那種不學無術、虛偽和正統的封建偽道士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