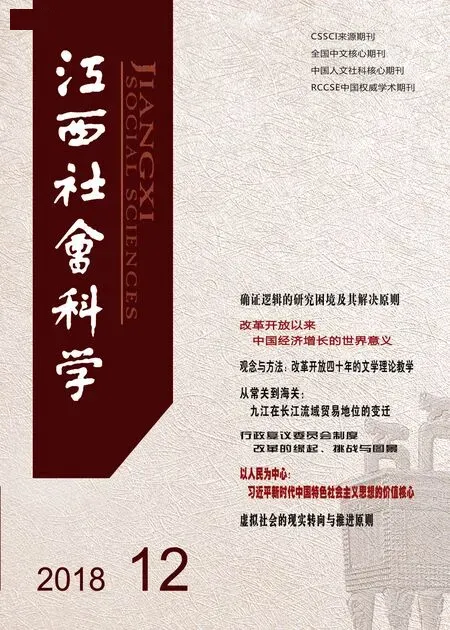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的緣起、挑戰(zhàn)與圖景
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是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改革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也是我國行政復(fù)議法修改的重要論題之一。立足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實(shí)踐,梳理試點(diǎn)工作中的得失成敗,對于堅(jiān)持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改革方向、豐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內(nèi)涵具有重要意義。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不僅要作為行政復(fù)議的審理機(jī)關(guān),而且還要確立為法律上的行政復(fù)議主體。在此基礎(chǔ)上需設(shè)置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必要的正當(dāng)工作程序:建立以聽證為代表的公開審理制度;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委員回避制度;強(qiáng)化行政復(fù)議決定說明理由。
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是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改革實(shí)踐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早在2007年,北京、哈爾濱等地就通過成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方式,提高行政復(fù)議制度的效率和公信力。2008年,國務(wù)院法制辦發(fā)布的 《關(guān)于在部分省、直轄市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 《通知》)決定在北京、黑龍江、江蘇等8省市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2010年,國務(wù)院發(fā)布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再次提出“探索開展相對集中行政復(fù)議審理工作,進(jìn)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10年來,全國各地紛紛設(shè)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處理行政爭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引發(fā)了一些質(zhì)疑和討論。為進(jìn)一步推動該制度發(fā)展和完善,分析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改革的初衷,歸納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實(shí)踐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并在理論上進(jìn)行反思,對于推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改革的深入,促進(jìn)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的緣起
從行政復(fù)議立法來看,在法定的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以外再成立復(fù)議委員會“參與”行政復(fù)議工作,并沒有法律依據(jù)。因此,催生行政復(fù)議委員會這項(xiàng)改革的動因不僅關(guān)系到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構(gòu)成及其職能定位,而且對于推動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的完善,激發(fā)行政復(fù)議制度在我國法治建設(shè)中的作用具有關(guān)鍵性的作用。那么,肇始于行政復(fù)議實(shí)踐中的這種探索出發(fā)點(diǎn)是什么呢,《通知》歸納了三個(gè)方面。①然而,無論是完善體制機(jī)制,還是優(yōu)化行政復(fù)議資源,其核心都是為了提升行政復(fù)議辦案質(zhì)量,提振行政復(fù)議制度的公信力。《通知》對這種內(nèi)在關(guān)系也進(jìn)行了明確的闡述:“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進(jìn)一步完善行政復(fù)議案件審理機(jī)制,可以充分發(fā)揮專家學(xué)者等社會力量的作用,有利于提高行政復(fù)議案件辦理質(zhì)量和效率,也有利于進(jìn)一步消除人民群眾對行政復(fù)議案件審理可能產(chǎn)生的‘官官相護(hù)’的疑慮,進(jìn)一步提高行政復(fù)議制度的社會公信力。”與《行政復(fù)議法》確立的行政復(fù)議體制相比,成立專門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參與行政復(fù)議工作,至少在以下三個(gè)方面能夠有針對性地矯正現(xiàn)行行政復(fù)議制度的局限性。
首先,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行政復(fù)議機(jī)構(gòu)不獨(dú)立所導(dǎo)致的社會公眾對復(fù)議決定公正性的質(zhì)疑。從行政復(fù)議制度的起源及運(yùn)作的實(shí)踐來看,這種“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制度設(shè)計(jì)雖然滿足了解決行政爭議專業(yè)性和效率的要求,但也埋下了公眾不信任的種子。對于復(fù)議制度,西方學(xué)者并不諱言:“復(fù)議程序產(chǎn)生于法院提供的權(quán)利保護(hù)尚不完善的時(shí)代。當(dāng)有人不同意其所受的行政決定時(shí),他有可能在行政內(nèi)部——一般向上級機(jī)關(guān)表示不服。同時(shí)行政機(jī)關(guān)也有機(jī)會自我糾正錯(cuò)誤;法院則免除了這一負(fù)擔(dān)。”[1](P298)“由于復(fù)議是由與作出原決定的官員同屬一個(gè)機(jī)關(guān),其可能的結(jié)果是,它只是成為申請尋求有效救濟(jì)途徑的一個(gè)障礙,造成了拖延和附加的成本,卻得不到一個(gè)真正中立與客觀的復(fù)議。”[2]近年來,國內(nèi)理論界和實(shí)務(wù)部門也將行政復(fù)議公信力不高歸因于復(fù)議機(jī)構(gòu)的獨(dú)立性缺失,“行政復(fù)議機(jī)構(gòu)獨(dú)立性和權(quán)威性的缺乏是造成行政復(fù)議制度失信于民的首要體制性原因”[3](P538),“在揭示行政復(fù)議制度存在的各種問題進(jìn)而探討有效發(fā)揮其功能時(shí),最為集中的莫過于對行政復(fù)議機(jī)構(gòu)獨(dú)立性不夠的批評”[4]。為此,《通知》把“積極探索完善行政復(fù)議組織”作為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明確“探索建立政府主導(dǎo)、社會專家學(xué)者參與的行政復(fù)議工作機(jī)制。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可以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和一般委員組成。主任委員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由本級政府領(lǐng)導(dǎo)擔(dān)任,副主任委員由本級政府法制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人擔(dān)任,—般委員可以由經(jīng)遴選的專職行政復(fù)議人員和專業(yè)人士、專家學(xué)者等外部人員擔(dān)任”,即通過在組織機(jī)構(gòu)、人員組成上與行政復(fù)議機(jī)構(gòu)的分立,保證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組織上的獨(dú)立性,從而為行政復(fù)議的公正展開奠定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其次,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bǔ)行政復(fù)議人手不足并優(yōu)化行政復(fù)議隊(duì)伍的專業(yè)知識結(jié)構(gòu),進(jìn)而提升行政復(fù)議質(zhì)量并緩解社會公眾對行政復(fù)議公信力的質(zhì)疑。根據(jù)《通知》的表述,復(fù)議機(jī)關(guān)人手不足、專業(yè)性欠缺,“成為制約行政復(fù)議制度發(fā)揮應(yīng)有作用的瓶頸”。因此,如何在現(xiàn)有的制度資源背景下,通過體制機(jī)制創(chuàng)新,消除這一“瓶頸”就成了檢驗(yàn)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得失成敗的關(guān)鍵。從實(shí)踐來看,各地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正朝著這一方向進(jìn)行著不懈努力。例如,北京市第一屆行政復(fù)議委員會28名組成人員中,來自高校、研究機(jī)構(gòu)和國家部委的非常任委員有18名之多;2016年成立的江蘇省行政復(fù)議委員會36名委員中,有23名來自有關(guān)高校、律所及省政府以外的其他部門的非常任委員;而哈爾濱市更是明確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個(gè)人委員要以市政府以外的委員為主。[5]可見,設(shè)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能夠很好地借助于“外腦”,彌補(bǔ)復(fù)議機(jī)構(gòu)人手不足的弊端;多元化構(gòu)成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委員在改善行政復(fù)議人員結(jié)構(gòu)、提高行政復(fù)議的辦案質(zhì)量,進(jìn)而提升行政復(fù)議制度的公信力的同時(shí),其本身也獲得了較高的公信力。
最后,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特別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中的議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首長負(fù)責(zé)制的不足,進(jìn)而緩解社會公眾對復(fù)議決定公正性的質(zhì)疑。據(jù)《行政復(fù)議法》的規(guī)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是行政復(fù)議的受理機(jī)關(guān)。一方面,復(fù)議機(jī)關(guān)與行政復(fù)議被申請人是上下級關(guān)系,由于下級行政機(jī)關(guān)在業(yè)務(wù)上接受上級行政機(jī)關(guān)的領(lǐng)導(dǎo)和監(jiān)督,甚至有些行政行為的做出本身就是接受上級機(jī)關(guān)指導(dǎo)的結(jié)果,因而這種行政復(fù)議結(jié)果的公正性客觀上難以保障,公眾對其產(chǎn)生質(zhì)疑合情合理;另一方面,現(xiàn)行的行政復(fù)議程序主要是按照行政命令的模式來設(shè)計(jì)的,確立書面審理的原則,缺乏雙方質(zhì)證、抗辯等程序公正的規(guī)定,無法從程序上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quán)利進(jìn)行保障,雖然彰顯了該制度靈活高效的優(yōu)勢,但為了追求這一優(yōu)勢而以犧牲程序公正為代價(jià),不僅飽受行政復(fù)議“司法化”的詬病,也有些得不償失。從各地區(qū)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工作方式和工作程序來看,普遍確立了案審前材料送達(dá)、參會成員回避、參會成員提問和發(fā)表意見、參會成員對處理意見和其他待議決事項(xiàng)進(jìn)行票決等程序性制度;必要時(shí),案審會還可以中止,通過舉行聽證或者補(bǔ)充調(diào)查等方式取證后,再行恢復(fù)審理。通過這種“準(zhǔn)司法”的程序制度,提高了復(fù)議過程的民主性、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行政復(fù)議決定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面臨的挑戰(zhàn)
官方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表明,實(shí)施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改革以來,試點(diǎn)地區(qū)成效明顯。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試點(diǎn)的各地區(qū),復(fù)議案件數(shù)量明顯回升而信訪量顯著減少,甚至出現(xiàn)了行政復(fù)議受理案件數(shù)量超過行政訴訟的狀況,行政復(fù)議制度作為行政糾紛過濾器的作用開始得到體現(xiàn)。不僅如此,部分未納入試點(diǎn)的省市也積極主動地開展該項(xiàng)工作。數(shù)據(jù)表明,2001年的前10個(gè)月,我國多數(shù)地方行政復(fù)議案件的數(shù)量穩(wěn)步增長,其中12個(gè)行政復(fù)議力量相對較弱的省級政府受理行政復(fù)議案件量同比增長超過10%,寧夏、福建、湖北、江蘇等增長最快,分別達(dá)260%、80%、50%和42%,廣東當(dāng)年辦理行政復(fù)議案件已突破萬件,總體糾錯(cuò)率達(dá)30%。有觀點(diǎn)甚至就此認(rèn)為,我國行政爭議解決方式的“大信訪、中訴訟、小信訪”格局已經(jīng)形成。[6]毋庸諱言,2007年《行政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的頒布施行及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探索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沉睡”的行政復(fù)議制度,促成了行政復(fù)議制度在多元化行政爭議解決機(jī)制中的無限風(fēng)光。然而熱情過后行政復(fù)議制度似又回復(fù)到了先前的“疲軟”狀態(tài),其外在的標(biāo)志就是行政復(fù)議案件數(shù)量的下降和維持決定比重的上升。以2017年為例,貴州省各級行政機(jī)關(guān)共收到行政復(fù)議申請3973件,同比下降12.3%,受理3162件,受理率79.6%,同比下降10%。從審理結(jié)果看,維持1438件,占審結(jié)案件45.95%,同比上升5.9%。②江蘇省常州市政府法制辦共收到行政復(fù)議申請121件,與2016年同期214件相比,收案數(shù)下降43.5%,已審結(jié)的426件復(fù)議案件中,維持204件,占結(jié)案總數(shù)的47.8%。當(dāng)然,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行政管理行為逐步規(guī)范化”“《行政訴訟法》修訂帶來的案件井噴式增長后便有所下降”“行政相對人維權(quán)日趨理性”等,但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在實(shí)踐中面臨的問題亦應(yīng)引起高度重視。概括起來,這些問題和挑戰(zhàn)主要有以下三個(gè)方面。
第一,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與行政復(fù)議法律制度發(fā)展的方向。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jù),這是黨領(lǐng)導(dǎo)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shè)的根本原則。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缺乏《行政復(fù)議法》上的規(guī)范依據(jù)被普遍視為其致命缺陷,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導(dǎo)致人們對該項(xiàng)改革的質(zhì)疑,甚至影響行政復(fù)議在行政爭議解決過程中的公信力。有學(xué)者直言:“至今為止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推行,并沒有嚴(yán)格意義上的法律依據(jù),而只有政策的指導(dǎo)。”[4]顯然,作為行政復(fù)議制度改革初期的一種探索,特別是明確為相關(guān)基本制度改革的“試點(diǎn)”,以政策為指導(dǎo)具有較大程度的正當(dāng)性,但是若一項(xiàng)改革長期處于“試點(diǎn)”狀態(tài)而得不到“正名”,不免讓人懷疑該項(xiàng)改革舉措本身的科學(xué)性。例如,在國務(wù)院法制辦公室發(fā)布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通知》的2年之后,國務(wù)院發(fā)布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意見》再次提出“探索開展相對集中行政復(fù)議審理工作,進(jìn)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的要求,這表明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國家最高行政機(jī)關(guān)的認(rèn)可,并將其作為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一個(gè)重要的“抓手”。同年底召開的全國行政復(fù)議年度工作會議透露,《行政復(fù)議法》的修改工作正在進(jìn)行之中。此后在2013年10月公布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立法規(guī)劃中,《行政復(fù)議法》修改屬于47件“條件比較成熟、任期內(nèi)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之一,而在最新公布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立法規(guī)劃中,《行政復(fù)議法》修改仍然屬于全國人大“第一類立法項(xiàng)目”。為什么已經(jīng)啟動了修法程序并且也列入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guī)劃,但《行政復(fù)議法》的修改卻仍然“猶抱琵琶”?個(gè)中原因一定是復(fù)雜的。但是從改革的實(shí)踐邏輯來看,當(dāng)一項(xiàng)重大改革舉措,尤其是關(guān)乎爭議解決機(jī)制改革和完善的方案長期不能得到立法層面的確認(rèn),必然對其績效產(chǎn)生致命的損害并引發(fā)公眾的質(zhì)疑: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改革是不是背離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向?
第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模式選擇與行政復(fù)議制度功能的定位。通說認(rèn)為,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起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務(wù)院批準(zhǔn)、財(cái)政部公布的《財(cái)政部設(shè)置檢查機(jī)關(guān)辦法》確立“復(fù)核處理”制度。該辦法第6條規(guī)定:“被檢查的部門對檢查機(jī)構(gòu)之措施認(rèn)為不當(dāng)時(shí),得具備理由,向其上級檢查機(jī)構(gòu)申請復(fù)核處理。”延續(xù)這一思路,后來的《行政復(fù)議條例》和《行政復(fù)議法》都將行政復(fù)議制度定位為“行政機(jī)關(guān)內(nèi)部自我糾正錯(cuò)誤的一種監(jiān)督制度”③,直至2007年國務(wù)院制定發(fā)布《行政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時(shí),才將“解決行政爭議”列為行政復(fù)議制度的功能。盡管“內(nèi)部監(jiān)督”和“糾紛解決”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兩者賴以發(fā)力的重點(diǎn)則存在明顯差異,進(jìn)而傳導(dǎo)到行政復(fù)議制度上具體要求也存在不同:“內(nèi)部監(jiān)督”只是要求監(jiān)督者對被監(jiān)督者具有權(quán)威即可,而“糾紛解決”則取決于裁決者能否獲得社會公眾的認(rèn)可和信賴。一般認(rèn)為,我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在實(shí)踐中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咨詢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主要是審議重大疑難復(fù)雜的行政復(fù)議案件,對行政復(fù)議工作和發(fā)展中的重大問題進(jìn)行研究;另一種是以哈爾濱為代表的案件決議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直接審議行政復(fù)議案件并進(jìn)行議決。[5]可見,北京模式實(shí)際上是給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建立了一個(gè)“參謀”機(jī)構(gòu),復(fù)議委員會并不取代復(fù)議機(jī)關(guān)作“議決”,充其量不過是復(fù)議制度中的“審判委會”,從“形式合法”的角度進(jìn)行評價(jià),該模式并未逾越現(xiàn)行法律的約束。而哈爾濱模式是由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取代行政機(jī)關(guān)作為做出行政復(fù)議決定主體,意味著復(fù)議機(jī)關(guān)的“改弦更張”,與“行政復(fù)議司法化”改革思路較為接近。前者之于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震動較小,也基本能夠滿足“層級監(jiān)督”的要求,而后者通過賦予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主體的獨(dú)立性、外部性,從而有助于行政復(fù)議決定的“立威”進(jìn)而取信于民,但需要行政復(fù)議法進(jìn)行根本性的變革。問題是,“解決行政爭議”是《行政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這部行政法規(guī)“增設(shè)”的行政復(fù)議功能,仍然有待全國人大立法層面的首肯和吸納。
第三,行政復(fù)議委員會集中設(shè)置、分散安排與行政復(fù)議公信力的塑造。無論是《通知》還是《意見》,均明確了“相對集中行政復(fù)議審理權(quán)”的改革方向。“相對”集中與“絕對”集中應(yīng)有區(qū)別,問題是,什么樣的集中或者說集中到何種程度為“相對”集中并無明確標(biāo)準(zhǔn),這就造成了實(shí)踐中的各種不同做法。例如,在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過程中出現(xiàn)了將原來分散于政府各部門的行政復(fù)議權(quán)集中到本級政府設(shè)立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來行使,被集中的部門不再保留行政復(fù)議職權(quán)探索,但在具體操作上又形成了同級政府所有部門和部分部門的復(fù)議職能集中到政府設(shè)立的復(fù)議委員會的相對集中和全部集中的不同做法,這是橫向的集中。從縱向上看,這種相對集中與絕對集中在省、市、縣三級又存在著明顯區(qū)別:行政層級越低,集中度可能越高;而在省級層面,由政府的一個(gè)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統(tǒng)一行使行政復(fù)議審理權(quán),往往操作難度較大。當(dāng)然,從試點(diǎn)的角度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模式的多元化是試點(diǎn)的題中之意,它通過不同模式的比較和“試錯(cuò)”,有助于積累經(jīng)驗(yàn)、揚(yáng)長避短,進(jìn)而能夠選擇或提煉出一個(gè)最優(yōu)的模式,并最終形成正式的制度體系。
三、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的改革圖景:堅(jiān)守與方向
全國各地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制度改革探索也有不少做法逾越了現(xiàn)行《行政復(fù)議法》所能“容忍”的紅線,因而需要行政復(fù)議法的修改予以回應(yīng)。在《行政復(fù)議法》修改再次列入全國人大立法規(guī)劃之際,我們認(rèn)為,需要從我國行政爭議解決機(jī)制的發(fā)展趨勢及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改革探索的目的等方面,來全面評價(jià)這場改革的得失取舍,從而為未來的修法提供智力支持和實(shí)踐腳本。
第一,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符合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在爭議解決中的角色定位和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化解行政爭議不僅需要行政復(fù)議制度,而且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行政復(fù)議應(yīng)當(dāng)成為解決行政爭議的主戰(zhàn)場。法治社會并不意味著消除爭議,而是在于提供一整套的規(guī)則體系,預(yù)防爭議的產(chǎn)生,并且在爭議產(chǎn)生后能夠提供有效的制度化爭議解決管道。隨著社會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的形成,司法爭議解決機(jī)制已不堪重負(fù),進(jìn)而形成了多種糾紛解決機(jī)制共存的局面。在風(fēng)險(xiǎn)社會且行政專業(yè)化水平與日俱增的情景下,具有技術(shù)和效率優(yōu)勢的行政審查成為傳統(tǒng)司法審查所不可替代的一種爭議解決方式[7],這一點(diǎn)國外國家法治建設(shè)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也給予充分的證實(shí)。資料顯示,在行政爭議的解決方式中,同一期復(fù)議案件與訴訟案件的比率美國是24比1,日本約為8比1,韓國則為7比1。[8]上述數(shù)據(jù)不僅充分說明行政復(fù)議在行政爭議解決中的主渠道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行政復(fù)議決定能夠?yàn)闋幾h當(dāng)事人所充分認(rèn)可,意味著行政復(fù)議制度具有較高的社會公信力。
在我國,行政復(fù)議和行政訴訟作為我國行政救濟(jì)機(jī)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界與實(shí)務(wù)界有基本一致的認(rèn)識。在行政救濟(jì)機(jī)制在發(fā)揮維護(hù)相對人合法權(quán)益的同時(shí),是否把解決行政爭議作為其肩負(fù)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一開始并不明確。例如,1989年出臺的《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行政訴訟功能為“正確、及時(shí)”審理行政案件、“保護(hù)”相對人合法權(quán)益、“維護(hù)和監(jiān)督”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使職權(quán)④;直到2014年《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才將“解決行政爭議”并列為行政訴訟功能之一。而在我國行政復(fù)議立法中,行政復(fù)議功能同樣是“維護(hù)和監(jiān)督”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政職權(quán)、“防止和糾正”違法或不當(dāng)?shù)男姓袨椤ⅰ氨Wo(hù)”相對人合法權(quán)益⑤;直至國務(wù)院2007年頒布施行新的《行政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才將“解決行政爭議”確立為行政復(fù)議的核心功能,并將其他功能予以“剔除”⑥。雖然糾紛解決同權(quán)利救濟(jì)“可以并行不悖”,但兩者之間有時(shí)難免也會出現(xiàn)背離,甚至造成“案結(jié)事不了”的狀況。這種局面既是對行政糾紛解決機(jī)制權(quán)威的一種侵蝕,同時(shí)也可能損傷社會公眾對糾紛解決機(jī)制的信任。正因?yàn)檎J(rèn)識到“糾紛解決功能的強(qiáng)化既是司法權(quán)的應(yīng)有之義,也是因應(yīng)化解社會矛盾的時(shí)代需要”[9],2015年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將“解決行政爭議”確立為立法目的之一。相比較而言,由于《行政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的法律位階低于《行政復(fù)議法》,因此盡管該條例第1條強(qiáng)調(diào)是“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fù)議法》”制定的,但在形式上難免遭受合法性質(zhì)疑,因此應(yīng)當(dāng)在行政復(fù)議修改時(shí),明確將“解決行政爭議”作為該制度的主要任務(wù)。
實(shí)際上,行政復(fù)議不僅要以“解決行政爭議”為主要目的,而且還要在行政爭議解決過程中發(fā)展“主渠道”的作用。這一點(diǎn),不僅是法治發(fā)達(dá)國家和地區(qū)的“先例”,而且逐漸成為我國行政爭議解決制度建設(shè)的一個(gè)方向。例如,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之所以能夠不顧理論上的爭議,規(guī)定復(fù)議機(jī)關(guān)在作出維持復(fù)議決定時(shí)應(yīng)當(dāng)同原行政機(jī)關(guān)為共同被告的目的⑦,就是要“敦促復(fù)議機(jī)關(guān)積極履行職能,發(fā)揮復(fù)議制度在行政爭議解決中應(yīng)有的作用”,進(jìn)而解決行政復(fù)議這種“具有高效、便民、成本低等優(yōu)勢的解決爭議的方式偏離”其“設(shè)置初衷”的問題。[10](P70-71)顯然,行政復(fù)議制度要在我國行政爭議解決機(jī)制發(fā)揮主要作用,核心在于通過行政復(fù)議裁決主體的改造來消除現(xiàn)行復(fù)議制度給人們造成的“官官相護(hù)”印象。而廣泛吸收外部專家學(xué)者組成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與傳統(tǒng)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相比,既在組織上獨(dú)立又不乏廣泛性、專業(yè)性、代表性,較之于行政系統(tǒng)內(nèi)部基于上下級關(guān)系而產(chǎn)生的復(fù)議機(jī)關(guān)而言,其中立性和公正性更容易獲得相對人和社會公眾的認(rèn)可。
第二,從行政“層級”出發(fā)有差別地實(shí)施相對集中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設(shè)置應(yīng)當(dāng)成為我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改革的方向。如前所述,“相對集中行政復(fù)議審理權(quán)”是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改革的一個(gè)方向,國務(wù)院法制辦副主任郜風(fēng)濤在2011年12月24日召開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座談會上也明確表示,實(shí)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模式,相對集中行政復(fù)議權(quán)限,有利于簡化行政復(fù)議管轄體制,依法有效化解行政爭議,保障行政復(fù)議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提高行政復(fù)議的效率,它可能會成為我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的基本發(fā)展方向。[11]透過各地紛繁復(fù)雜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實(shí)踐,我們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不同行政層級,從縱向和橫向兩個(gè)維度上進(jìn)行有差別的相對集中。
一方面是橫向的集中,即在縣(市)、設(shè)區(qū)的市一級實(shí)行行政復(fù)議審理權(quán)向縣(市)、設(shè)區(qū)的市人民政府行政復(fù)議委員會集中。之所以作出這種設(shè)置安排,原因有三。(1)客觀條件的限制。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優(yōu)勢是要借力“外腦”來解決復(fù)議機(jī)關(guān)人員不足、專業(yè)性不強(qiáng)和獨(dú)立性缺乏等問題,而我國目前較為普遍的一個(gè)現(xiàn)狀是,各種專門人才往往集中在少數(shù)大城市,若以《行政復(fù)議法》規(guī)定的復(fù)議機(jī)關(guān)為依據(jù)普遍建立相對應(yīng)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不僅不能緩解《通知》指出的專門復(fù)議隊(duì)伍人才匱乏問題,而且縣(市)、設(shè)區(qū)的市專業(yè)人才儲備實(shí)際也不能滿足這種需求。由此可能造成這樣的一個(gè)結(jié)果,即少數(shù)專家不得不受聘多個(gè)行政復(fù)議委員會,進(jìn)而造成不同行政機(jī)關(guān)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委員的高度重疊而成為實(shí)質(zhì)上的一個(gè)復(fù)議委員會。這樣一來,不僅可能對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尤其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公信力造成負(fù)面影響,而且也會帶來了公共資源的浪費(fèi)。(2)實(shí)質(zhì)性解決行政爭議的考慮。從我國行政爭議解決實(shí)踐來看,社會公眾一個(gè)普遍的認(rèn)知是,爭議解決主體的層級越高,所受到的法外因素干擾越小,越是能夠公正地處理行政爭議。這一點(diǎn)甚至已經(jīng)對我國行政訴訟管轄制度的改革產(chǎn)生了影響。⑧按照現(xiàn)行行政訴訟管轄的規(guī)定,雖然復(fù)議機(jī)關(guān)作為被告并不能實(shí)質(zhì)性地提高行政訴訟的級別管轄,但客觀上對行政復(fù)議的審理主體和相對人的心理等都會產(chǎn)生積極影響。(3)回應(yīng)行政復(fù)議實(shí)踐的需要。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那樣,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作為行政復(fù)議受理機(jī)關(guān),既造成復(fù)議機(jī)關(guān)的專業(yè)性不夠,難以有效處理行政糾紛;又有可能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fèi),根據(jù)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情況,市、縣兩級政府部門很少辦理行政案件,有的縣一年受理的行政復(fù)議案件只有三、四件甚至更少。因此,取消市、縣政府部門行政復(fù)議的職責(zé),將其統(tǒng)一交給政府行政復(fù)議機(jī)構(gòu)管理,對行政復(fù)議的實(shí)踐影響不大,還能提高復(fù)議效率。[12]哈爾濱市就相對集中行政復(fù)議權(quán)進(jìn)行了有益探索,經(jīng)市政府部門的申請,可以將原本由本部門管轄的行政復(fù)議案件交由市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決定,而2009年修訂的《山東省行政復(fù)議條例》第6條第2款更是明確規(guī)定,經(jīng)省人民政府批準(zhǔn),設(shè)區(qū)的市、縣(市、區(qū))人民政府可以集中行使行政復(fù)議權(quán)。
另一方面是縱向的集中,即實(shí)行省級與縣(市)、設(shè)區(qū)的市級差別化的集中。在省級,政府組成部門可以根據(jù)實(shí)際需要參照省政府的做法,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省級政府部門的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因其獨(dú)立性、專業(yè)性還能吸引對下級政府部門提起的行政復(fù)議申請,從而實(shí)現(xiàn)另一種維度的行政復(fù)議集中。更重要的是,這種形式的集中在保證行政復(fù)議專業(yè)性同時(shí),亦未突破我國行政復(fù)議法確立的上級行政機(jī)關(guān)作為復(fù)議機(jī)關(guān)的體制。
第三,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不僅要作為行政復(fù)議的審理機(jī)關(guān),而且還要通過行政復(fù)議法的修改確立為法律上的行政復(fù)議主體。以北京市和哈爾濱市為代表的兩種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模式,其根本的差異在于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與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的關(guān)系,即復(fù)議委員會的決定對復(fù)議機(jī)關(guān)是否有拘束力。從經(jīng)驗(yàn)邏輯來看,如果復(fù)議委員會的決定對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沒有拘束力,那么復(fù)議委員會制度在實(shí)踐中較大的可能是流于形式,甚至可能衍變成為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復(fù)議決定正當(dāng)性背書的工具。行政聽證制度在我國最初的遭遇即是例證;如果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具有絕對的拘束力,那么在現(xiàn)行體制下仍要由行政機(jī)關(guān)及其負(fù)責(zé)人承擔(dān)復(fù)議決定的后果就有些不大合適,并且也與行政機(jī)關(guān)首長負(fù)責(zé)制的問責(zé)機(jī)制相沖突。[12]實(shí)際上,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將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確立為共同被告,目的雖是為解決長期以來行政復(fù)議維持率居高不下的問題,但也給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帶來了極大的應(yīng)訴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只承擔(dān)訴訟風(fēng)險(xiǎn)卻不享有作出復(fù)議決定的相應(yīng)權(quán)力,復(fù)議委員會制度定會受到現(xiàn)行體制的抑制而難以有效推行。有鑒于此,我們認(rèn)為,在當(dāng)下的制度環(huán)境下,可以吸收多數(shù)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探索的做法,即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作出的決定類似于“專業(yè)咨詢意見”,其對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并不具有絕對的拘束力,最終的復(fù)議決定仍然由復(fù)議機(jī)關(guān)作出。但是,若復(fù)議機(jī)關(guān)不采納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審理意見,必須充分地說明理由。蘇州市從2014年開始,在全市范圍內(nèi)推行說理式行政復(fù)議決定書,要求從講清“法理、事理、情理、文理”四個(gè)角度完善行政復(fù)議決定書的制作;對復(fù)議機(jī)關(guān)與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決定一致的行政復(fù)議事項(xiàng),由復(fù)議委員會提供復(fù)議決定書;復(fù)議機(jī)關(guān)作出與復(fù)議委員會不一致的行政復(fù)議決定時(shí),由復(fù)議機(jī)關(guān)就決定理由進(jìn)行充分說明,并形成書面存檔。⑨
從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改革過程中推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探索的目的來看,我們認(rèn)為,行政復(fù)議委員會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做實(shí)、做強(qiáng)”,直至以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名義直接作出復(fù)議決定,才能真正提升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公信力,使行政復(fù)議成為我國解決行政爭議的主渠道。實(shí)際上,這種做法與我國現(xiàn)行行政復(fù)議體制并不存在沖突:按照我國《行政法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的規(guī)定,行政復(fù)議機(jī)構(gòu)與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離”的,而復(fù)議機(jī)關(guān)對于復(fù)議機(jī)構(gòu)的處理意見基本上也是“照單全收”,而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實(shí)體化實(shí)際上就是這種分離的“審決主體”一體化。當(dāng)然這不僅需要我國行政復(fù)議法修改時(shí)對行政復(fù)議體制作出根本性的變革,并對包括行政訴訟法在內(nèi)的相關(guān)法律規(guī)范作出相應(yīng)調(diào)整,同時(shí)還要強(qiáng)化行政復(fù)議的程序構(gòu)造。
在已有的理論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學(xué)者針對行政復(fù)議制度正當(dāng)程序缺失而帶來對復(fù)議申請人權(quán)益保障的力度較弱的狀況,主張推動行政復(fù)議的司法化,并在制度設(shè)計(jì)方面仿照行政訴訟。對此,我們持保留態(tài)度:一方面,盡管行政復(fù)議具有準(zhǔn)司法性,但從本質(zhì)上講,行政復(fù)議是行政權(quán)的行使,是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與其他行政行為不同的是,其他行政行為是發(fā)生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而行政復(fù)議機(jī)關(guān)居中裁判,是三方行為。也正因?yàn)閺?fù)議機(jī)關(guān)居中裁決且行政復(fù)議需依當(dāng)事人的申請啟動,行政復(fù)議才具有了司法性質(zhì)。如果過于強(qiáng)調(diào)行政復(fù)議的司法性,推動其司法化,則會使行政復(fù)議喪失行政權(quán)的特性,損害行政復(fù)議制度“方便快捷、程序靈活”[12]的優(yōu)勢;另一方面,過于強(qiáng)調(diào)行政復(fù)議的司法化,會使其喪失制度價(jià)值。行政復(fù)議作為與行政訴訟并行的行政糾紛解決制度,其獨(dú)特的制度價(jià)值在于能夠通過行政機(jī)關(guān)的內(nèi)部監(jiān)督更快地解決行政糾紛,減輕法院的壓力。行政復(fù)議不僅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還能通過體制內(nèi)層級監(jiān)督的天然優(yōu)勢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進(jìn)行審查。從這個(gè)層面上說,行政復(fù)議對行政相對人的權(quán)利保障更為全面。例如,美國就很注重發(fā)揮行政復(fù)議和行政訴訟在行政和司法兩方面解決行政爭議的功效,司法審查確立了“窮盡行政救濟(jì)原則”,并側(cè)重法律審查。[13]過于強(qiáng)調(diào)行政復(fù)議的司法化,行政復(fù)議與行政訴訟同質(zhì)化,既忽視了行政復(fù)議獨(dú)特的制度價(jià)值,也會造成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的浪費(fèi)。
在此基礎(chǔ)上,為了保證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獨(dú)立、科學(xué)、公正地作出復(fù)議決定,必須設(shè)置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必要的正當(dāng)工作程序。為此,既要保障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作為一個(gè)行政機(jī)構(gòu)的特性,又要吸收部分司法程序規(guī)定,使得復(fù)議申請人能夠感受到程序公正。(1)建立以聽證為代表的公開審理制度。《行政復(fù)議法》規(guī)定了書面審理的原則,確實(shí)能夠保證行政糾紛解決的效率。但是“書面審原則的貫徹又使得復(fù)議工作人員對事實(shí)問題的查明更多依賴于被申請人提交的證據(jù)材料”[14],在我國行政決定程序不完善、證據(jù)收集和認(rèn)定方面存在問題的情況下確定書面審理原則,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實(shí),會損害案件審理公正性。(2)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委員回避制度。任何人不得作為自己的法官,這是行政程序公正原則最基本的要求。為保證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中立性,委員會成員發(fā)現(xiàn)復(fù)議案件與本人或所在單位有利害關(guān)系時(shí),應(yīng)當(dāng)主動申請回避;復(fù)議申請人因同樣原因申請委員會成員回避的,應(yīng)當(dāng)同意。(3)強(qiáng)化行政復(fù)議決定說明理由。說明理由能夠使行政相對人充分理解行政行為及復(fù)議決定作出的原因,有利于行政糾紛的解決;同時(shí)說明理由也是對復(fù)議機(jī)關(guān)復(fù)議決定的有效監(jiān)督。
四、結(jié) 語
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在行政復(fù)議的實(shí)踐中不斷探索發(fā)展,在保證復(fù)議機(jī)構(gòu)獨(dú)立性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復(fù)議決定的公信力,對完善行政復(fù)議制度、將行政復(fù)議建立成為解決行政爭議的主要渠道具有重要意義。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符合我國行政復(fù)議制度在爭議解決中的角色定位和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但是,由于設(shè)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依據(jù)的文件效力層級較低、缺乏統(tǒng)一的制度性規(guī)定,行政復(fù)議委員會的實(shí)踐存在一些問題。因此,應(yīng)當(dāng)通過《行政復(fù)議法》修改將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確立下來。行政復(fù)議委員會不僅要作為行政復(fù)議的審理機(jī)關(guān),而且還要確立為法律上的行政復(fù)議主體。并在此基礎(chǔ)上設(shè)置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必要的正當(dāng)工作程序,首先,建立以聽證為代表的公開審理制度;其次,確立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委員回避制度;最后,強(qiáng)化行政復(fù)議決定說明理由,以促進(jìn)行政復(fù)議委員會制度的完善,更好地發(fā)揮行政復(fù)議的制度優(yōu)勢。
注釋:
①具體為: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是落實(shí)黨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完善行政復(fù)議體制、創(chuàng)新行政復(fù)議工作機(jī)制要求的重要舉措;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是提高行政復(fù)議辦案質(zhì)量、效率和社會公信力的現(xiàn)實(shí)需要;開展行政復(fù)議委員會試點(diǎn)工作,是優(yōu)化行政復(fù)議資源配置、充分發(fā)揮行政復(fù)議制度功能的重要途徑。
②參見《省政府法制辦圓滿完成2017行政復(fù)議、應(yīng)訴案件統(tǒng)計(jì)工作》,http://www.gzfzb.gov.cn/zwgk/xxgkml/tjsj_39180/201804/t20180417_3238160.html。本文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系查詢各地行政復(fù)議和行政應(yīng)訴統(tǒng)計(jì)報(bào)告,以下不再贅述。通過比對,發(fā)現(xiàn)也有少部分地區(qū)2017年行政復(fù)議案件數(shù)略有上升,如江蘇省無錫市、安徽省銅陵市等。
③參見原國務(wù)院法制辦公室主任楊景宇1988年10月27日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所作的《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fù)議法(草案)的說明》。
④《行政訴訟法》第1條規(guī)定:“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shí)審理行政案件,保護(hù)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quán)益,維護(hù)和監(jiān)督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使行政職權(quán),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
⑤《行政復(fù)議條例》第1條規(guī)定:“為了維護(hù)和監(jiān)督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使職權(quán),防止和糾正違法或者不當(dāng)?shù)木唧w行政行為,保護(hù)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quán)益,根據(jù)憲法和有關(guān)法律,制定本條例。”《行政復(fù)議法》第1條規(guī)定:“為了防止和糾正違法的或者不當(dāng)?shù)木唧w行政行為,保護(hù)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quán)益,保障和監(jiān)督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使職權(quán),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
⑥《行政復(fù)議法實(shí)施條例》第1條規(guī)定:“為了進(jìn)一步發(fā)揮行政復(fù)議制度在解決行政爭議、建設(shè)法治政府、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fù)議法》,制定本條例。”
⑦從相關(guān)司法解釋來看,這里的被告還是必要的共同被告,即哪怕起訴人不起訴復(fù)議機(jī)關(guān),人民法院也要依職權(quán)追加作出維持復(fù)議決定的復(fù)議機(jī)關(guān)為共同被告。
⑧例如,21世紀(jì)初行政訴訟實(shí)踐中出現(xiàn)的“提級”管轄,以及2008年最高院關(guān)于管轄的司法解釋和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等,相對1989年行政訴訟法管轄規(guī)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⑨行政復(fù)議說明理由制度在國外的行政復(fù)議制度中也存在。例如,德國《行政法院法》第73條第3款規(guī)定:“復(fù)議決定中必須說明理由,附具權(quán)利救濟(jì)手段的告知,決定必須送達(d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