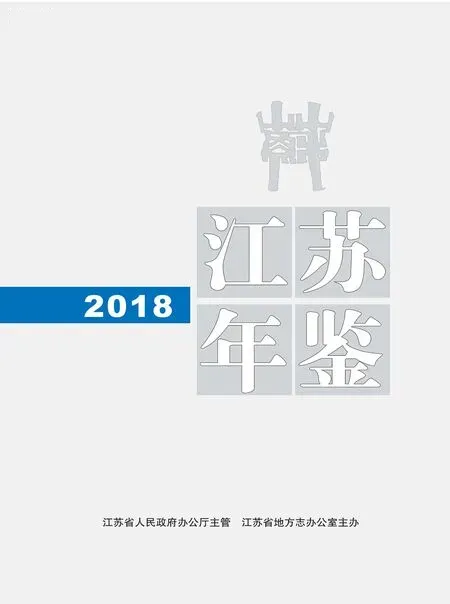經 濟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現江蘇地區就誕生了原始農業、原始畜牧業和原始手工業。但由于境內臨江沿淮瀕海,早期缺乏防洪排澇設施,洪患恣意為害先民,洪水過后土壤又極易鹽堿化,經濟水平很低。在中國現存第一部文獻匯編《尚書·禹貢》中,徐州(包括今蘇北等地)的土壤肥力和田賦貢獻率名列全國中游,揚州(包括今江南等地)排在最后。秦統一全國后,隨著鐵器農具的普及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今江蘇地區與全國一樣,經濟呈總體發展的歷史走向,同時也表現出歷史階段性和區域差異性的自身特點。
西漢惠帝、文帝、景帝時期,是江淮之間和蘇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漢高祖末年,吳王劉濞利用富有銅礦和沿海地緣優勢,采銅鑄錢,煮海為鹽,國庫充裕,遂在全境取消稅賦,民間經濟發展獲得強大的動力,國強民富,富可敵國(漢王朝),《漢書·枚乘傳》稱其“富于天子”。
東吳、東晉及其此后的宋、齊、梁、陳,相繼在今南京建都,境內江淮和江南成為東南政治中心。加之北方陷入長期戰亂,中原精英紛紛渡江南下,大部分定居在今蘇南及其周邊地區。在此期間,六朝政權偏安一隅,江南地區得益于長江“天塹”屏蔽,數百年間沒有發生大的戰事。中原人口的持續遷入,帶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增加也迫使人們開辟荒野,擴大耕地,在原有的土地上精耕細作,南京、鎮江、常州、蘇州成為當時重要的都市。但同時,淮河流域由于處在南北爭奪的交錯地帶,受到戰爭的反復破壞,生產力遭到極大摧殘,經濟發展逐漸落后南方。
隋代南北大運河的開鑿,為江蘇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契機。廣大鄉村借水而興,許多城鎮因河而盛。位于長江和大運河交匯處的揚州,成為南北交通、經濟、文化的樞紐,繁華程度在長江流域與成都并駕齊驅,人們謂之“揚一益二”。到了唐后期,經濟地位已超過長安、洛陽,雄踞全國之首,成為最為繁華的工商業大都市,史稱“天下之盛,揚為首”。安史之亂以后,五代十國紛爭,北方戰無寧日,江淮地區相對安定,北方人口第二次大規模南遷,再次推動江蘇經濟崛起,并逐漸發展為國家的財賦重地。《新唐書·權德輿傳》謂之“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杜枚《崔公行狀》謂之“三吳,國用半在矣”,蘇州刺史白居易謂之“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
宋代范仲淹在今南通、鹽城地區修建捍海堰,使得農田和鹽場免受海潮襲擊,史稱范公堤。太湖地區興治的圩田形成由人力控制的排灌體系,成為當時領先全國的旱澇保收良田。宋金對峙期間,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規模南遷,為江蘇經濟帶來第四次發展高峰,并最終超越中原,成為全國的經濟重鎮。當時流行民諺說“蘇常熟,天下足”,后演變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至此,江蘇經濟通過深厚的歷史積淀,形成一股巨大的慣性力量,持續發展。但在蘇北地區,自公元12世紀末黃河奪淮入海,大片農田被淤埋,村莊被摧毀,水系被破壞,進一步拉大了與蘇南地區的差距。
元代太湖流域成為全國的植棉中心和棉織業中心。明初定都應天(今南京),明代后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進一步推動了江蘇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明后期地域面積只占全國的0.33%、耕地面積只占全國的2.85%的蘇州、松江、常州三府,農業財政貢獻率卻占到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3.96%。其中,蘇州府在洪武二年(1369)向朝廷繳納的糧食竟然占全國總額的11%,超過當年四川、廣東、廣西和云南四省的總和。迄于清代,蘇州、南京和浙江的杭州成為全國三大絲織業中心,揚州成為淮鹽運銷中心,無錫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
清代后期,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生凋敝,江蘇特別是蘇北地區深陷積弱積貧的窘境。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轟開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強迫清王朝簽訂《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先后開放上海、南京、鎮江等口岸,對中國進行殘酷的經濟侵略和掠奪;與此同時也帶來先進的西方工業文明。江蘇得風氣之先,先后創辦蘇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等“洋務”實業,民間也積極興辦近代民族工商業,涌現出以南通張謇、無錫榮氏為代表的近代工商業集團,為發展地方經濟和民族振興做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江蘇經濟取得長足的進步。其間雖然走過一段彎路,但早期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興辦的大量廠礦,卻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江蘇歷經鄉鎮企業崛起、外向型經濟突飛猛進、創新驅動等幾個階段,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以“創業創新創優”為載體,“爭先領先率先”為動力,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到20世紀末,全省基本邁入小康社會,蘇南部分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初步現代化。2017年,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5900.9億元,增長7.2%,全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107189元,增長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