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憶溈及其異類系列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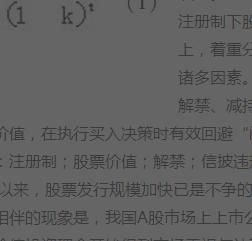

一.堅守異類的小說創作
隱居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山下的薛憶溈,一度其身份曾經使讀者撲朔迷離,他不是深圳的作家嗎?理工男出身的薛憶溈,何以棄理從文?早在北京航空大學(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書時,他就醞釀著自己的文學夢。大學二年級,他在北航圖書館的期刊閱覽室里讀完馬爾克斯的《沒有人給他回信的上校》,感動得“第一次”為文學作品流下眼淚。本科畢業之后他沒有在所學的理工方向深造,而是轉向文學創作,并且攻讀英美文學碩士學和語言學博士學位。薛憶溈認為:促使我走向文學之路的契機應該是中國大陸始于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它的“主旋律”是以存在主義為旗幟的西方哲學思潮。我的基礎教育橫跨整個七十年代。七十年代無疑是我“成長期”中最關鍵的階段。
迄今,薛憶溈已出版有長篇小說《遺棄》、《白求恩的孩子們》、《一個影子的告別》、《空巢》、《希拉里 密和我》、短篇集《首戰告捷——戰爭系列小說》、《出租車司機“深圳人”系列小說》,隨筆集《文學的祖國》,《一個年代的副本》、《與馬可波羅同行》、《獻給孤獨的挽歌》等。我與薛憶溈有過一次深度的學術對談,從中可以窺察到這位作家個體的靈魂世界。我將下面摘取的對話片斷概括為三個關鍵詞:“精神探險”、“永恒主題”與“重寫革命”:
其一.寫作是孤獨的精神探險。
江少川:你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界最獨立特行的人物:從來沒有加入過作家協會,也幾乎沒有參與過官方組織的文學活動。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你的寫作一直是“在野”的寫作。你的文學也一直獨立于“主旋律”,是個人的追求,孤獨的追求,也是最純粹的追求。這種獨特的文學狀態是出于性格還是出于信仰?
薛憶溈:我想兩者的原因都有。我生性就比較孤僻,對任何性質的集體活動都持懷疑和抵觸的態度。在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北京高校的學生有機會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國慶三十五周年的慶典。我們整個年級有近八十個學生,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參與“同樂”。同時,我也堅信文學是個人的事業,是孤獨的事業。與同行真正面對文學的切磋當然非常重要。但是,我很清楚,所有與物質利益掛鉤的大集體和小圈子都很容易將文學變成低級趣味,都非常危險。是的,在文學上,我一直保持著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這種獨特的文學狀態當然讓我受益無窮,但是它也給我帶來過許多的尷尬和困難,比如在五十歲之前,我幾乎沒有得到過文學獎的光顧,無疑是同輩所謂著名作家中在這方面的“翹楚”。
其二.個體生命的困惑是作品的總主題。
江少川:知識界評價《遺棄》是中國少有的探尋個人存在意義的“哲理小說”。何懷宏教授借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稱它是你“尋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旅程”。你完成《遺棄》第一版的時候年僅24歲。你是在一種什么樣的境況中完成這部作品的?在很多人可能都還“不省人事”的年紀,你的作品中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密集的哲理呢?
薛憶溈:《遺棄》是1988年在長沙酷熱的夏天里用急行軍的速度完成的。整部作品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思想者和寫作者對現實、歷史以及生命的深層焦慮的集中宣泄。充滿精神追求的八十年代即將結束了:《遺棄》的主人公像許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同齡人一樣對個人和世界的前景開始出現了深層的焦慮。小說的題記經常被人引用:“世界遺棄了我/我試圖遺棄世界”。它表明《遺棄》是一部探討“我”與“世界”之間關系的作品。“我”與“世界”的關系是文學永恒的主題,
其三.挑戰自我,發動“重寫”革命。
江少川:更多的作家,尤其是在成名之后,總是希望有新作不斷出版,往往會把目標定在“下一部”新作上。而你卻對舊作發動了一場引起廣泛關注的“重寫”的革命。對少量作品進行“重寫”可以理解,而你對2010年之前發表過的所有舊作,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甚至隨筆作品都進行了“重寫”,如此徹底的革命在文學史上確乎少見。開始這樣的“重寫”需要多大的勇氣,完成這樣的“重寫”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很想聽你進一步談談“重寫”的情況。
薛憶溈:我“重寫”舊作的原因是自己對漢語的感覺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使所有那些舊作讀起來都讓我感覺不對了。這種“不對”的感覺對我的身體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折磨。“重寫”是我的必經之路。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它是我對自己的救治。不經過這樣的自我救治,我就不可能再往前走。說實話,我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這場革命會如此持久又如此暴烈。整個的“重寫”從2009年底開始,到今年年初基本結束,持續了五年多的時間。整個的“重寫”幾乎涵蓋了我在2010年(也就是46歲)之前發表的所有作品。①
《首戰告捷——戰爭系列小說》與《出租車司機---“深圳人”系列小說》是體現上述三個特色的中短篇經典之作,以下分別加以評述。
二.戰爭框架下對個體生命的沉思
《首戰告捷——戰爭系列小說》雖稱“戰爭系列”,可是這部作品集中沒有波瀾壯闊的宏大戰爭場面敘事,沒有敵對雙方刀槍廝殺的血腥戰斗,也未為英雄人物樹碑立傳。作家聚焦在歷史變革中的人,寫戰爭框架中普通人物的命運及對個體生命意義的沉思。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歷程》收入中篇小說金庫,與《阿Q正傳》等11種經典并列,是薛憶溈戰爭系列中最有影響的一篇作品,也是他移居加拿大后創作的第一部小說。薛憶溈居住的蒙特利爾是白求恩生前居住時間最長的城市,他在那里生活了八年。薛憶溈說蒙特利爾是白求恩帶進他的生活的。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國家喻戶曉,因為毛澤東寫過一篇《紀念白求恩》的經典短文。薛憶溈在閱讀研究了大量中英文資料以后,重新塑造了這一“專門利人”的懷特大夫的形象,他如何來到中國,在艱苦的抗戰歲月,他如何渡過了20個月的時間,他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歷程》揭示了他豐富的感情經歷與復雜的內心世界,及多少年來不為人所知的真實人生。他來到中國之前,在西班牙馬德里,一度曾陷于生命低谷,在強烈的政治傾向與沖動下,他來到中國,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日子里,企求尋找理想與激情的歸宿。而現實是殘酷的,他面臨戰亂中窮困、荒涼的農村慘狀,目睹女秘書弗蘭西絲空襲中死亡,15歲的孩子戰斗中受傷得不到救治而慘死。他憂傷,孤獨,思念前妻,想念家鄉。這位大夫集革命者與藝術家,激情與失意,獻身與痛苦于一身。作家還原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外國人,他是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者,有激烈的政治傾向和沖動,有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有情愛,也有挫折、失意、迷惘與痛楚。他非常想念前妻,即使離婚以后仍然舊情不忘,甚至有愛情至上傾向。他勤勉工作、而醫療器械、藥物奇缺,得不到補給,在貧困艱苦的中國土地上,他發出了對人生、時間、生命的叩問,對天堂迷茫的思考 。懷特大夫性格復雜,情感豐富而又多才多藝。他是人而不是神,他有七情六欲,他不是圣人更不是符號。他認為自己不過是歷史的一顆棋子。薛憶溈深有感受地說道:“我希望將讀者帶進一個個體生命的深處,希望讓讀者看到個人內心的渴望與痛苦,同時感受文學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在歷史和戰爭的框架下探尋個體生命的意義是我的文學的一個偏好。”②endprint
薛憶溈對戰爭與革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寫的《“專門利人”的孤獨》一文用確鑿詳實的史料,尤其是被保存下來而塵封多年的白求恩的書信,為《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歷程》提供了真實、理想的背景材料,也是這篇小說最好的詮釋與注腳,可以看作是互文或姊妹篇。
《首戰告捷》是小說集中震撼人心的篇章。革命勝利了,將軍決定回老家接父親到北京居住,多年未見老父親,音訊全無,這次連他的居室都安排妥當了。故事發生在途中的回憶過程中。快到老家舊宅了。將軍回憶起他當年參加革命時的一幕幕往事:將軍投身革命,遭到父親的強烈阻攔,父親死活不同意兒子上戰場,他不理解兒子的行為舉動,他擔憂,然而改變不了將軍毅然從戎的決心,無奈之下,父親只好一路跟隨他的部隊走。將軍自然理解父親的拳拳之心,但將軍決意已定。將軍出生入死,血濺沙場,此時,終于回到闊別已久的老家,將軍百感交集,要見到父親了。然而老宅不在了,只有一片廢墟,父親不在了,家人不在了。
父親是怎樣去世的,怎樣走的?是革命的敵對者,還是革命的激進者,抑或其他(小說中只是一筆帶過“一支來歷不明的軍隊洗劫了他們家”)?這些都不重要,無關緊要了,小說的震撼力在于,革命成功了,除親歷戰爭的革命者以外,還有那些普通人,不理解、不贊成或不支持者,他們并不站在敵對方一邊,但他們也作出了犧牲,付出了代價,雖然他們不是死在戰場,父親卻是因為兒子,最終付出了身家性命。兒子選擇革命之路是對的,然而父親當年所做的一切,亦無可厚非,多少父親對待子女不都是如此嗎?老父親走了,為什么令人震撼?令人心疼,那是人性在扣動讀者的心靈。而對將軍,那是因為父愛,是兒子對父親的反思,也有他的自我反省。將軍的父親不就是這樣的普通人嗎?他的兒子為革命奮戰多年,貢獻卓著,而他在革命勝利之后不在了。
小說給人不僅是悲痛,或曰傷痛,而是“痛”之后的追尋與思索。革命者在戰爭年代赴湯蹈火,有的還付出了生命,這當然可歌可泣,要大書特書,而在戰爭的背后,還有許多小人物,也有傷與痛,革命者從革命中走過來了,有的獲得功勛與偉業,這是值得慶幸的。而有的人不理解革命,也非直接參與者,或者旁觀者,他們反對暴力,祈求和平,這是否也是一種信仰呢?他們的父輩,如將軍之父親還為此付出了生命。這就是令革命者以及廣大民眾、讀者心靈震撼之所在。“小人物沒有權力,對歷史沒有影響,但是,他們卻最受歷史的影響。”③
一場重大、激蕩的變革與革命之后,參與革命的普通人及其家族(親人)的境遇與命運,應當獲得怎樣的尊重,關懷與呵護,這是人類應當普遍關注的論題,也是文學的使命,這是對人的終極關懷,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母題,這正是薛憶溈戰爭系列小說的思想深度與沖擊力。薛憶溈說《首戰告捷》是一篇關于父子關系的作品。小說題目中的首戰特指將軍遭受父親阻撓,投身到革命的反叛獲得的首場勝利。作家在談到這篇經過重寫的短篇時 提到對一個細節的改動:將軍最后一役在戰場上走過,表情嚴峻地在一具敵方年輕軍官的尸體邊蹲下。原版本中,將軍感嘆地說:這是一個英俊的人。重寫版中,將軍說:這是一個永遠失去父親的兒子。這一句之改的細節,讓讀者窺察到小說主旨的密碼。這就是他在《首戰告捷》的重寫版自序中開頭的那句話:個人與歷史的沖突是我的文學著力探討的主題,而戰爭為我提供了進入這個主題的特殊通道。
讀這篇小說不禁想起馬爾克斯的《沒有收到回信的上校》,為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上校,革命成功后退伍,為得到退伍金補助,他幾經周折,提供證據8年,名字列入登記表6年,整20年來,老夫妻倆風燭殘年,生活凄苦,在一個小鎮等候那封兌現退伍金補助的回信,等到兒子也死了,那回信還沒有等到。這是馬爾克斯的經典短篇。這篇作品與《首戰告捷》,寫的是發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國度完全不一樣的故事,但同樣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因為這樣的戲劇故事能超越時空與膚色。我以為《首戰告捷》與馬爾克斯的經典之作達到了同等的高度。
三.新都市小人物的心靈史
“以深圳人系列小說”命名的短篇《出租車司機》,早在1997年就發表在“人民文學”上。2002年他移居加拿大,深藏在蒙特利爾。在異域生活三年之后準備回國之時,“深圳人”系列忽地刺激了他的創作沖動。喬伊斯說過:從遠方觀察和描寫故鄉,反而比較客觀。到2012年完成這個小說系列 ,此時薛憶溈移居加拿大正好十年。一部十二萬字的短篇小說集,寫作地點橫跨深圳與蒙特利爾,創作時間前后跨度16年,這種跨域中西的人生經歷、海外留學的潛心研修與生活經驗,雙語文學創作的積淀,開闊豐富了他的文學視野,他在重新回憶、省思、反芻那座城市及城市的人,思考如何寫中國故事,不僅讓國內讀者喜歡欣賞,不同地域、膚色的外國讀者同樣也要能接受、感興趣。她的鄰居白人老太太讀了英譯本后不但自己很喜歡,還買了兩本作為圣誕節禮物送給朋友。他參加加拿大文學活動,出現了排隊購買這部英語版小說的盛況。薛憶溈最近談到《希拉里、密和我》的創作時說,要“搭建在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上,……為讀者打開認識‘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特殊的窗口”。④這就是地球村意識,或曰人類意識,國際視野,這不正是我們的作家所要認真思考與追尋的東西嗎。
“深圳人”系列小說,不是記述一座城市的發展史,也不是寫深圳人的奮斗史,而是寫歷史進程中的人,寫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個體生命的意義,在平凡的生活流、心理流中展現人物的心靈世界。薛憶溈認為:“現代化進程是一種歷史。它當然深刻地影響了小人物的命運。而在作家看來,最值得文學關注也最考驗作家能力的是那些肉眼‘看不見”的影響,是那些與統計局發布的或真或假的數據沒有明顯關系的影響。”④“那些肉眼‘看不見的影響”是什么?濾去城市流光溢彩、繁華喧囂的外表,掠過高樓大廈下行色匆匆的人群,作家在追尋普通百姓個體生命的軌跡,他(她)們是這座最年輕的新興城市的邊緣人:出租車司機、教師、小販、女秘書、打工姐妹、劇作家、同居者、家庭婦女……。這里有悲涼后的徹悟,堅韌中的辛酸,追尋中的沉淪……。一位出租車司機來這座城市打拼了十五年了,他拉了一趟好價錢的長途后得知他心愛的妻子與女兒遭車禍去世。小說寫的只是一位極普通的小人物的“痛失”,并沒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節,那場車禍只是輕輕一筆帶過。小說著意所表現的是司機的自責、內疚、后悔,原來為什么粗心,只是她們存在,存在時平凡不過,一切都是慣常的,一旦失去,才感到她們的珍貴,而那時未珍惜到足夠。她們走了,他頓時反思自己,萬分痛悔。這是大徹悟。而小說的結尾,他突然意識到,來這座城市十多年了,還有兩位親人同樣也“不在意”,那就是漸漸老去的父母親,他不能重復對待妻子與女兒的粗心,大悲之后,他決心回到家鄉陪伴年邁的父母親。如果從美學的概念探究,這位司機的“痛失”,或許不能說成悲劇,但小說同樣產生了悲劇的效果與感染力。而它帶有暖色調的結尾,耐人咀嚼,余味尤為深長。endprint
《小販》從中學生的視角寫一個到城里做小販的遭遇。小販為了養家糊口在學校門前擺攤,一群迷戀美國好萊塢大片與意甲足球聯賽、崇尚格斗而成績差的男生,故意戲弄、欺侮這個賣爆米花的小販,甚至用磚頭砸傷了小販的額頭。如果說這群涉世未深、懵懂無知的少年傷害的是小販的身體,而幾個有權的管理者搶走他用以活命的化纖口袋,并割破它丟到垃圾箱,還狠狠罵道:“你這樣的人就不該活命”。那么這幾位管理者的惡言深深刺傷的是小販的心。小說的末尾,秋季開學的時候,小販又來到學校門口,他要活命,要生存。明知還會遇到那樣的中學生、那樣穿制服的管理者,他又奈何?而小販不經意說的一句話:當年美國鬼子都沒有逃出我的手心。點明他原來是參加抗美援朝的老兵,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而在多少年過去的戰爭之后,他還在為生存而奔波,甚至為活命而受屈辱。
《兩姐妹》中,姐姐這位漂亮的女孩,為了堅守“可靠”這唯一的標準,放棄了另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男子,嫁給了平庸且唯唯諾諾的可靠男人。隨著可愛女兒的出生,姐姐滿足現狀成為家庭婦女,而丈夫步步升遷,移情別戀,變心了。離婚以后,姐姐沒有重新開始新的生活,而是實行所謂“報復”,與丈夫的上司、助手、領導頻頻發生性關系,在失去理智的瘋狂之后 她殘害了自己,患病而死,在迷茫中放縱、沉淪,走向毀滅。她的悲劇在于丈夫變心之后的迷茫與自殘。
系列小說展現給讀者的是小人物個體生命之痛,而作家所傳達出來的是一種悲憫情懷。出租車司機失去妻子與女兒之后,對人生的深刻體悟與洞徹,引起人們深深的反思,如何珍愛普通平凡的人生與家庭。而溫暖的結尾也溫暖著讀者的心。作家寫《小販》,并非只是在譴責那群無知懵懂、不道德的少年,批判那幾個不講人性的有權的管理者。小說的主旨不在于控訴,小販隨口而出的上過戰場那句話,那明知會受辱而再次出現在學校門前的堅守,讀到此處,誰不會產生辛酸、憐憫之情。他還在憑自己的辛勞養活自己。而那位姐姐在迷茫中的自我滅亡,在引起人們悲嘆與哀痛的同時,更激起人們的反省與沉思,那就是她的沉淪之死。悲憫情懷是文學的最高境界,薛憶溈說:“個體生命的意義一直是我的文學最重要的主題。而普通小人物一直是能夠幫助我挖掘這一主題的最佳人選。”⑤作家在系列短篇集中將讀者帶進一個個小人物個體生命的深處,窺探人物內心的渴望與痛楚,感受作者悲天憫人的文學情懷。
薛憶溈讀外國文學經典下功夫極深。喬伊斯是薛憶溈最為崇拜的西方作家之一,他多次說道: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喬伊斯、卡夫卡和博爾赫斯。他曾反復精讀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和《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都柏林人》這部被譽為西方系列短篇的經典之作,對移民作家白先勇的《臺北人》,蘇煒的《遠行人》的創作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從“深圳人”系列小說,可以看到喬伊斯《都柏林人》的傳統與技巧的滲透,而薛憶溈在繼承的基礎上的借鑒與發展也是顯而易見的。薛憶溈自覺運用文學的空間形式構筑地域性的城市印象:將單篇人物個體生命的心靈史,一篇篇整合構筑為空間的整體,構建起新興都市空間中小人物的群像畫廊。
約瑟夫·弗蘭克在《現代文學中的空間形式》對《都柏林人》的空間結構有過精辟的論述;“喬伊斯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必須當作一個順序來讀的數百頁紙中,如何為全部豐富的城市生活創造出同時性的印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強化它。”“深圳人”系列正是用“結構性并置”,“交互參照”、將十二篇沒有情節關聯的短篇合成為一個城市的空間圖景,其“空間形式就像一個桔裝的構造”⑥將各篇中的人物組合拼接成城市整體人物群像圖,展現出都市小人物形形色色的眾生相與生存現狀。系列短篇各自成篇,然而卻有一個總主題,故事發生在同樣獨特的空間,那座最年輕、最開放的城市。表達急劇轉型期中普通人共同承載的生命負荷之沉重。
注 釋
①②③⑤江少川:《在文學的祖國里執著地生根--薛憶溈訪談錄》,《作家》2015年第7期。
④呂紅:《隱藏在皇家山下的文學奇觀》,《紅杉林》2017年第一期。
⑥約瑟夫·弗蘭克:《現代文學中的空間形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頁。endprint

